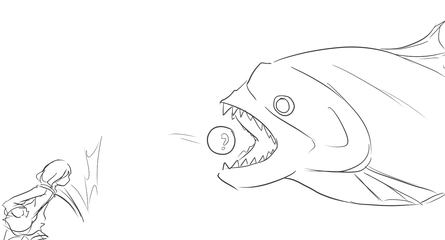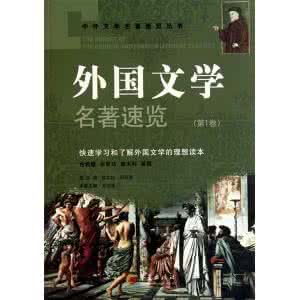
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普罗”一词就是英文Proletarian(意为无产者、无产阶级的)译音“普罗列塔利亚”的缩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中,普罗文学运动作为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端于1928年,结束于1930年,即以大革命失败后太阳社的成立与后期创造社立场的转变为其形成的标志,而以左联的成立和柔石、殷夫等“五烈士”遇害作为其高潮结束的标志。
普罗文学运动的主体是以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作家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与倾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它的理论直接来源于苏俄“拉普”的文艺理论以及日本“福本主义”与“纳普”的文学主张,是在现代化背景下产生的革命文学,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标准,以革命活动为题材,以革命者与无产阶级为描写对象,在否定“五四”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反资本主义的主题,并在白色恐怖和中共党内“左倾”思潮的双重作用下,表现出激进的面目。
“革命的浪漫谛克”是普罗文学重要的审美追求和创作方法,这一名称来自于1932年瞿秋白为《地泉》所做的序言,它囊括了普罗文学的创作特点———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革命加恋爱的题材、标语口号式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而对于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而言,“革命”这个词语本身似乎就蕴涵着暴力,其源出《周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①它所指的是政权的改变,在近代以来则被赋予了民族、民主的要求,并且这一能指在无产阶级运动兴起后延伸为阶级意义上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革命。
从苏俄传播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认为革命是新兴阶级对旧的统治阶级的暴力行动,阶级斗争的理念对于急于在现实困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革命者们有着莫大的诱惑,“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②
因此,普罗作家相信,他们所追求的“战斗的力的美”便是阶级斗争中的革命的暴力,郭沫若(麦克昂)呼喊着“文艺界中应该产生出些暴徒出来了才行了”③,蒋光慈、钱杏邨等人一再将革命和暴动视为一种艺术,宣称“Boudon(暴动)确实是一种艺术,只要Boudon的意义是伟大的。恐怖时代的残杀是值得我们咒诅的,Boudon时代的牺牲流血委实不能否认不是一种Art。”④于是在艺术上,甚至出现了以简单粗暴为美,“我们对于艺术的手法的主张,是Simple and Strong”。⑤
一
对于革命的暴力,汉娜·阿伦特认为,“必然性和暴力结合在一起,暴力因必然性之故而正其名并受到称颂,必然性不再在至高无上的解放事业中遭到抗拒,也不再奴颜婢膝地被人接受。相反,它作为一种高度强制性的伟大力量受到顶礼膜拜”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所谓历史必然性与暴力的结合,使革命的暴力以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面目存在。然而,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传播过程中,“革命”被描绘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然途径,其所具有的善的目的与作为手段的暴力美学之间也就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革命者们选择了用预设正义的方式作为二者的中介,即在阶级话语中贫困成为道德判断的先验标准———穷人在道德上必然是“善”的,反之,富人则具有先天的“恶”,革命也就表现为“善”的阶级(“好人”)消灭“恶”的阶级(“坏人”),革命的暴力因此被想象为符合道义的行动而获得了正义性,这一过程实现的唯一依据就是“贫困即美德”的先在规定。正是由于在道德上优于其他阶级,所以无产阶级也就在理论上进一步巩固了争夺领导权的合理性,“道义优越是穷人成为革命者的动因。一旦穷人觉醒或被唤醒这一道义优越,穷人基于道义优越的权利要求会迅即变成追求美好生活而实施暴力的权利。这种权利将是超越一切法律的、自我绝对化的‘单向正义’。”⑦
基于此,在正面叙述革命斗争的普罗小说中,革命的暴力行动以崇高、正义的形式出现,“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这一原则成为革命者的特权,使对阶级敌人的毁灭和杀戮得到豁免甚至褒奖。
蒋光慈的《最后的微笑》便是叙述了一个复仇的故事:性格懦弱的青年工人阿贵在被工厂开除后受到蚂蚁打架和革命者沈玉芳牺牲等事件的刺激,杀死了特务刘福奎、工头张金魁和工贼李盛才,自己也饮弹自尽。对于自己杀人的事实,阿贵也感到了惶惑,他质疑了杀人的合法性,“若说杀人是应当的事情,那末这样杀将下去,似乎又有点不大妥当。你杀我,我杀你,这样将成了一个什么世界呢?而且人又不是畜生,如何能随便地杀呢?……”但是,阿贵杀人的直接动机是为个人及沈玉芳、李全发复仇,通过沈玉芳对革命正义的解释将杀人的行为上升为道义上的阶级复仇,沈玉芳告诉阿贵:“凡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行动,无论是什么行动都是对的。既然如此,那末一个被压迫者将一个压迫他的人杀死,这事当然也是对的了。压迫人的人都是坏人,被压迫的人都是好人,好人应当把所有的坏人消灭掉”,这一理论将阿贵杀人归结为好人杀坏人,使阿贵相信自己是“为人除害”,是理所应当的行为,从而消除了他对“犯罪”的恐慌,获得了道德上的解脱。于是,阿贵自杀之时,“他的面孔依旧充满着胜利的微笑。……”⑧
这种魔力在于革命的预设正义提供了一套颠覆性的道德话语,并以此覆盖了暴力非法性的一面,从而使受压迫者破除了对原有秩序和法律的内心恐惧,充分放大了他们对现实的抵触和破坏情绪,他们如同被催眠般坚信自己的所为是崇高的,是承担道德责任的结果。
这就使得暴力掩盖了人的自然天性,《菊芬》里的菊芬是一个“又天真,又活泼,又美丽,又纯洁的少女”,发现冤枉了恋人薛映冰收到情书后,“这时在她的脸上荡漾着愉快的微笑的波纹,同时似乎又有点羞意。她走到薛映冰面前,痴痴地望他几眼……”但就是这样一个恋爱中的带着娇痴的少女,却毫不犹豫地对阶级敌人发出了血淋淋的咒诅:“我现在也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总是想杀人,总是想拿起一把尖利的刀来,将世界上一切混帐的东西杀个精光……”“呵,杀,杀,杀尽世界上一切坏东西!……”⑨“纯洁”与“杀戮”这两个性质相反的词语同时存在于她的身上,人性这一抽象的概念或是被当作“革命”的对立物遭到抛弃,或是被纳入“革命”的话语之中,狂热的革命激情在菊芬的身上展示了它的巨大的改造作用,使这样一个天真的少女在“为着全人类”的崇高动机下陷入对暴力的崇拜中。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阶级矛盾的根源,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了不同阶级的冲突,因此无疑摆脱贫困低下的地位是工农大众的必然的革命诉求,“贫困将帮助人们打破压迫的镣铐,因为穷人失去的只有锁链”⑩,而完成这一愿望的途径则是消灭剥削阶级,实现受剥削者的翻身。劳苦大众的翻身过程在普罗小说中被简化为剥夺阶级敌人的肉体,实现自身和阶级的复仇,作者使小说中的人物相信阶级的压迫是他们受苦的根源,想要摆脱贫困和苦难就只有彻底地粉碎剥削阶级,因此在正面叙述工农革命斗争的文本中,其典型的叙述逻辑是贫困源于剥削———杀死剥削者———穷人翻身,暴力在其中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既是贫困之果又是翻身之因。
华汉的《暗夜》{11}叙述了由于地主的剥削造成了罗家生活的窘困,从而引发了罗氏父子的仇恨,在罗大的主张下———“杀!杀!杀!……杀完了恶霸田主我们好分土地”,老罗伯也意识到,只有杀光地主分田地穷人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杀”成为对生存困境的反抗:“啊啊,你!你!你!你不容我们穷人生活下去的田主哟!你你你!你们真该杀杀杀杀呀!……”农民通过杀死钱文泰等土豪劣绅和攻占警察局的暴动,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革命的暴力行动被叙述为贫苦农民获得和捍卫自身解放的唯一手段,即“我们要杀人!我们必须杀人!我们要放火!我们必须放火!”“现在是拿我们的血去换取我们的衣食住的时候了”,“要用鲜红的血流去掩埋粉碎敌人的铁一般坚强的残忍的反扑。”{12}而以上话语又体现出普罗小说在叙述语言上强烈的阶级意识,罗氏父子话语中的“我们”和“你们”,分别指代农民与地主两个对立阶级,老罗伯说话的对象是幻化的田主人———“一个红肿鼻子的矮胖子”,但这一人称“你”最后转换为“你们”即延伸为对整个地主阶级的战斗宣言。“我们”杀死“你们”的潜在涵义是强调“杀”(复仇)是集体性的行为,一方面在话语层面上规避了个人复仇的偏执和功利,通过阶级复仇的形式彰显革命暴力“为工农大众”的崇高目的和正当性,另一方面也营造出集体复仇的声势和煽动效果,因此成为普罗小说中的常见话语。
二
这样的暴力叙事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紧张与矛盾,在人类的普遍认知中,暴力总是被置于社会伦理的负面,尤其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和为贵”的礼法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而革命时代对暴力的正面叙述及揄扬,突破了旧的伦理秩序,建立起以阶级为基础的革命伦理,于是普罗文学的文本中流露出伦理冲突的痕迹。
《咆哮了的土地》叙述了地主家庭出身的李杰回到家乡组织农会,在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中与父亲、家庭决裂,为了取得群众的信任,他不得不作出了同意了李木匠火烧自己家即李家老楼的要求,与此同时,内心也陷入痛苦挣扎:“病在床上的母亲或者会被烧死……痛苦着的惊叫着的小妹妹……这怎么办呢,啊?……李杰在绝望的悲痛的心情之下,两手紧紧地将头抱住,直挺地向床上倒下了。他已一半失去了知觉……”在这一情境下,李杰选择了牺牲自我,使个人情感屈从于阶级的需要,因此一面承受人性被撕裂的痛苦,一面相信这是“革命”对自己的考验:“这一次对于我是最重大的考验,我不能因为情感的原故,就……”,“只要于我们的事业有益,一切的痛苦我都可以忍受……”李杰的阶级出身是他作为革命者的最大障碍,于是他用毁灭自己家庭的行动表达了对于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而这一行为也招致王荣发之类年长者的质疑:“这真奇怪,他居然叫我们打倒他的老子。这未免革命革得太过了头了罢?”{13}
主人公的矛盾在于:母亲、妹妹会被烧死———获得农民(李木匠)的信任,悖离孝道———忠于革命。在李杰的自白中,他说“我没有父亲了”,“世界上还有比‘孝父母’更为重要更为伟大的事业,为着这种事业,我宁愿受着叛逆的恶名。母亲!你没有儿子了”。“没有父亲”意味着“父亲”的缺席,在宗法制的父子关系中,“父”与“子”构成了家族血统的延续,李木匠的怀疑就源于李杰因其出身而造成的相对农民的“异己”地位,既然李杰已经将父亲及其所代表的阶级视为“恶”(“如果我跟着他做恶,孝可是孝了,可是我们这一乡的穷人就有点糟糕!”{14}在革命者看来,欺压穷人自然是“恶”的),那么“没有父亲”即“叛父”在革命的伦理中成为革命者旌表自身正义与公正的行为,“父亲”成为“敌人”,成为暴力的对象,对“父”的暴力是李杰式革命者对自我历史的否定,通过否定,他由剥削者的儿子变成一个“无父”的“纯洁”的无产者,清洗了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因此在革命阶级内部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在阶级斗争的层面上,“叛父”这一在传统伦理中属于“恶”的行为却被叙述成为革命和为贫苦大众的“善”。
而对于“母亲”,李杰则痛苦地说“母亲!你没有儿子了”,其潜在的话语内涵是主人公承认自己的不孝,从而以有罪的身份(“叛逆的恶名”)接受母子关系的断裂,假如我们把父子伦理视为宗法制的基础,而把母子关系当作人的自然天性,那么李杰表明与父母决裂的不同话语正说明了革命-伦理-人性三者在革命者身上的复杂显现。
即使是革命者李杰,“不孝父母”而背负“叛逆的恶名”这种传统孝道的观念也存在于他的意识中,这样,一方面作者通过文本向人们展示了革命的正义和剥削者的“恶”,但另一方面,李杰却承认了自己“叛父”的革命行为是不孝和“恶”的。他所面对的困境是在“孝”与“更为伟大的事业”之间作出选择,这并不在于违反传统伦理所受的舆论的压力,而在于主人公的意识里依然留存着传统伦理的约束,李杰因为舍弃母亲和妹妹而痛苦,阿贵因为杀人而陷入“有罪”、“无罪”的困惑,翠英和鲁正平见到施暴而起了恻隐之心(《短裤党》),革命看上去并没有彻底祛除蕴藏在人性中的伦理法则,造成了革命者对暴力的短暂的迷惘,“蒋光慈曾企望借马克思之手送孔子道统上天堂,革命者李杰“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尽管李杰有‘不忍’之心,但还是走得很远。”{15}
于是,普罗文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革命的正义性基础上想象出革命者的阶级自觉意识,革命的信念总是引导李杰们在亲情和道义之间作出“正确”的决断,而这种信念的存在似乎又被认为是先验的和理所当然的。李杰在作出背叛家庭的决定时,他已经把家庭视作革命的必要牺牲,翠英们对于革命暴力的质疑总是会被轻易地粉碎,往往在一刹那的犹豫之后,阶级觉悟就使他们几乎立刻还原为坚定的革命者。当这种阶级自觉先于文本而置于作者的观念中,普罗小说的人物也就必然出现简单、概念化的缺失,但考虑到革命者的内在矛盾,这一缺失又是不可避免的。
普罗文学用预设正义的方式确定了暴力叙事的合理性,并试图以革命伦理颠覆文本叙述中的传统伦理,这是普罗文学在其政治美学上的实践———以审美的移情作用将主体的个人情感通过想象的方式转化为普遍的情感共鸣,“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6}可以看到,普罗文学的这一叙事特点成为了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政治美学特质之一,并在之后的革命文学发展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继承和延续。
注释:
①《辞源》第四册,第3364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②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47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③麦克昂:《英雄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④钱杏邨:《强盗及尼拨龙琪歌》,转引自《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第217页,林伟民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流沙〉创刊号·前言》,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第2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⑥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99页,译林出版社,2007年。
⑦魏朝勇:《革命、暴力与正义》,《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⑧见《蒋光慈文集》第一卷,第520、54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⑨见《蒋光慈文集》第一卷,第402、41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⑩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54页,译林出版社,2007年。
{11}收入《地泉》时,改名为《深入》。
{12}见《阳翰笙选集》第一卷,第344、356、371、423、42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见《蒋光慈文集》第二卷,第380、381、25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14}见《蒋光慈文集》第二卷,第374、20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15}魏朝勇:《革命、暴力与正义》,《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16}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