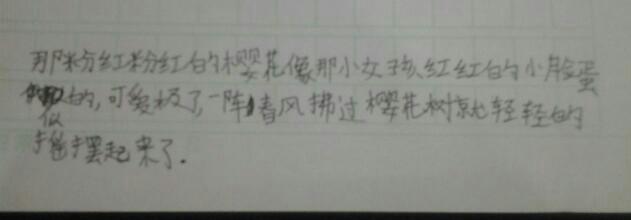《金瓶梅》作者可能是菩萨,所以他要求我们读者,也能成为菩萨。
柔情看过《红楼梦》不知多少遍,那藏匿于纯情之下的男盗女娼,令我觉得真正的污秽和厌倦。以前没有仔细地看过《金瓶梅》,此次才好好地品读《金瓶梅》,感悟出潘金莲有那种本能反映出的原生态淫欲美。
这种慈悲,一心追求纯洁与完美的少男少女是很难理解,或者几乎不可能想象的。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人为地把爱情的定义无限拔高,似乎“坏人“就必定没有爱情,似乎以性生活为主要载体的爱情就必定不是爱情,似乎我们天生就有无限的权力去贬低、干涉甚至镇压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这恐怕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总是把《金瓶梅》定为“淫书“的主要心理依据。
我们还常常会产生另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只要容忍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的存在,我们自己的高尚纯洁浪漫的爱情就必定会遭到威胁与破坏。尤其是,一个自认高尚的人,如果不去贬低那些不符合“高尚“定义的爱情,那她自己似乎就必定不可能拥有任何高尚的爱情,似乎他(她)就必定也是流氓荡妇之辈。这,恐怕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金瓶梅》里的“淫秽描写“的深刻文学意义的根本社会原因。
潘金莲是《金瓶梅》中的第一主角,也是全书写得最成功最灵动的艺术形象。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最成功的人物之一。
潘金莲人物是从《水浒传》中借衍而来,但在《金瓶梅》中,其经历、性格、生活等得到了多方面的重要的充实,从而塑造成一个既聪明伶俐、美丽风流,又是一个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典型。
《金瓶梅》作者写书之时,也许是觉得一个象《水浒传》中潘金莲那样的女人,带着无限的怨毒之力,正宜表达那种开天辟地以来万古常新的人心中之嗔恶。也正因为如此,作者给我们描绘出鲜活的潘金莲原生态的淫欲美。
潘金莲本是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第六,小名六姐。天生一副好姿色,又缠得一双好小脚。但好景不长,潘裁缝染上重病,无钱买药,蹬腿走了,撇下了老婆孩子。寡妇难撑家门面,女儿终是他家人。做娘的度日不过,便把9岁的潘金莲卖在城里王招宣府中,习学弹唱。这潘金莲不仅模样好,人也机灵聪明,学啥会啥,学啥像啥。到15岁时,描鸾绣凤,品竹弹丝,会弹一手好琵琶。这可都是让男人们心魂荡漾的技艺。
不久,王招宣死了。潘姥姥把女儿要了出来,转手卖给了张大户家,身价三十两银子,合当时五十石米。潘金莲在张大户家也是学习弹唱。光阴荏苒,日子易过,眨眼18岁了,潘金莲出落得脸似三月桃花,身如出水芙蓉,杏眼动人心魄,细眉弯弯,把个张大户馋得如同饥饿极了的猫见了鱼。只因为当时主家婆余氏凶狠如虎,张大户才不敢轻易沾腥。但有一日,邻家嫁女,余氏赴席。张大户暗暗把金莲叫到房中,遂心收用了。张大户已是五十开外的老头,得如此娇嫩黄花闺秀,以为大占便宜,美不胜美。接二连三之后,毛病出来了,先是腰疼,后是耳聋,小便不畅如水滴,眼泪鼻涕时常流,白天哈欠连天睡不醒,晚上喷嚏无眠难受。老头中邪了!余氏厉害,见此情此况岂有不知根由的?咒骂丈夫,苦打潘金莲。张大户挨骂已是家常便饭,可就是舍不得小潘金莲。随后想了个好主意,倒赔房屋,把潘金莲嫁给了房客武大郎。武大郎老实忠厚,得此美妇,以为是房东看得起自己。
武大郎原先娶过一妻,生下女儿迎儿之后就命归黄泉了,家中正缺个帮手,以后可以放心地挑着炊饼满街走了。老实人的心眼实,然而倒霉也就倒在这个“实”字上。武大郎前脚出门,张大户就溜进来与小潘金莲抱成一团。有几次,武大郎出门未上正街,想起忘了什么,马上回来拿,结果就碰见自家床上睡着老少鸳鸯。可他老实,从不言语。再挑着担子走出去。张大户胆大了,彼此云雨更多了。那身上的邪病更重,一年不到,呜呼哀哉死了。
张大户还没有入土,主家婆余氏就把武大郎一家赶出了大门。武大郎只好在紫石街西头租了两间房子住下。二十刚出头的潘金莲不比从前,她讨厌武大郎,要不,怎会去同那张大户私通呢?她倒不嫌“三寸丁,谷树皮”的,不嫌武大郎矮、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嫌的是武大郎太老实。她心中暗恨,眼泪常流:“普天之下,男人有得是,为什么将奴嫁与这样一个不争气的?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回家来除了酒就是睡,推他不醒,摸他不动,好像一截死木头。”她憎嫌武大郎,日逐站在门前勾引几个奸诈浮浪子弟,甚至在武松来到之后,竟也使出手段诱引,恨不得与武松成双(第一回)。后虽遭武松斥诫,但她不思改悔,在武松出行东京时,勾搭上了西门庆,药杀了亲夫武大郎,一顶轿子进了西门庆宅中。

潘金莲在西门庆众妻妾中,是个出名“专爱咬群”的主儿,她利嘴巧舌,机变伶俐,说话“似淮洪也一般”,尤其与那恃宠逞娇的丫环庞春梅撺合在一起,日常搬是弄非,人都怕她三分。她惯常手段之一是听篱察壁,安插耳目,即所谓设“影子”。当西门庆与来旺之妻宋惠莲勾搭,在藏春坞弄奸之时,被她潜身在月窗下偷听,听到那婆娘说她不过也是个后婚的人来,“露水夫妻”,便气得“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移脚不动”,恨道:“若教这奴才淫妇在里面,把俺每都吃他撑下去了。”(第二十三回)日后来旺醉谤西门庆之言,被来兴告到她的耳中,她便咬牙切齿道:“我若饶了这奴才,除非是他就下我来!”(第二十五回)并终于说动西门庆陷害来旺,宋蕙莲也无活路,上吊自尽(第二十六回)。
当西门庆与李瓶儿在翡翠轩私语,她又“走在翡翠轩槅子外潜听”,听得西门庆爱李瓶儿“好个白屁股儿”,以及李瓶儿已怀身孕(第二十七回),便刻意把话拿捏他俩,又常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淀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她,以夺其宠”(第二十九回)。至于其他,如安插平安探听西门庆与书童狎事(第三十四回)。拿捏并安插玉箫专一探听吴月娘上房消息(第六十四回)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她又心狠手辣,善于直接置人于死地。最典型的是当李瓶儿生下官哥之后,她眼看西门庆日益专宠李瓶儿,“把汉子调唆的生根也似的”,便数次惊吓小儿,甚至训练了一只“雪狮子”猫,用红绢裹肉令它扑而挝食,终于得隙扑到了官哥的身上,将官哥吓得风搐起来,不久夭亡(第五十九回)。李瓶儿受了这一精神打击,一病不起,潘金莲便乘胜追击,日逐指桑骂槐,气得她病上加病,又不敢和她争执,于是也一命呜呼了(第五十九至六十二回)。
潘金莲在西门庆宅中惯于“咬群”的根本目的,其实在于争宠夺爱,以满足她“欲火难禁一丈高”(第十二回)的肉欲需要。潘金莲平日在家,一味“霸拦汉子”,凭着她生得标致,又会诗词赋曲、琵琶弹唱,“枕边风月,比娼妇尤甚”。这几件都可在西门庆的心上,因此西门庆极宠爱她,尤其此妇肯接溺尿、吊双足、行后庭花,兼最善品箫,故西门庆把她视作性虐泄欲的工具,而每有这方面需要,便入她房来。
但是,潘金莲并不以此为满足,一旦西门庆“旷”了她几日,或是外出远行,她便难熬孤身永夜,就会干出玩小童(第十二回)、私女婿的勾当。为了笼络住西门庆之心,她除了配合西门庆摆弄淫具、制作绫带、按宫中春图行房、施展枕边风月以外,还惯于当“窝主”。她腾地方教西门庆在她眼皮底下奸耍庞春梅;她明知西门庆与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等有奸情,也不管,只要他凡事不瞒她,行一次向她说一次,有一人向她说一人即可。用她自己的话说:“你主子既爱你(如意儿),常言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那好做恶人?”(第七十四回)在性生活上西门庆以她为玩物,她则反将西门庆做泄欲工具,无丝毫夫妻恩爱可言。最终,西门庆在外搞了王六儿回来,她明明见其瘫软无力,却给他灌下过量的淫药,不顾死活地骑在他上面,弄得他“精尽继之以血,血尽出其冷气”,当下昏死过去,不久油尽灯枯,髓竭人亡(第七十九回)。
西门庆一死,潘金莲即与女婿陈经济打得火热,两人在库房中,在花园中私会,甚至大白天隔着窗扇也会云雨弄事(第八十二回)。同时全不顾廉耻,一日被庞春梅撞破,竟不要脸要庞春梅同意与陈经济奸耍(第八十二回)。自此主仆打成一家,与这小伙三人对奸。她弄出了肚子,趁吴月娘去泰山酬愿进香而私行打胎,将已成形的“一个白胖的小厮儿”倒进茅厕里(第八十五回)。然而这一切,终于被受尽折磨的丫环秋菊揭发出来了。吴月娘变脸变色,将她让王婆领去变卖。但是她淫欲成性,“依旧打扮乔眉乔眼,在帘下看人”,晚间反而拿王婆的儿子王潮儿来解渴(第八十六回)。最后,被武松报兄仇,斩首、割胸、剜心,落个尸陈街头的悲惨下场,亡年32岁(第八十七回)。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