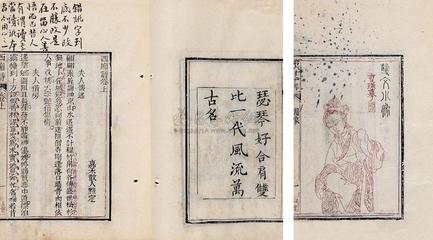作者:蒋成德
《水浒传》是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明代的李贽(1527-1602)与清初的金圣叹(1608-1661)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两位评点者,且影响至大,后人对《水浒传》的认识莫不从其序与评中获得启发。然而李金二人无论在《水浒传》的创作论,还是《水浒传》的主题论、人物论上,都是大相径庭的。今人多以为李贽的“《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的思想为金圣叹所继承,其实是大谬不然的。在主题思想、人物评价方面,金圣叹都是力反李说,而独标异见。那么,究竟孰是孰非,比较一下李贽与金圣叹的批评,探其文学思想,是不难看出其高下的;且对我们正确认识《水浒传》,也不是没有益处的。
一、关于《水浒传》的创作论
李贽在《忠义水浒全传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小说也可发愤的创作论思想。他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可耻孰甚焉?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竟,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剿三寇(又本作灭方腊———引者注)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
“发愤作书说”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可以说是古来有之。最早提出的是诗人屈原,他把发愤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在《九章·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自汉之后,倡此说者代不乏人,除前李贽提到的司马迁外,汉代桓谭在《新论·求辅》中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唐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不平则鸣。”宋代欧阳修在《梅圣俞诗序》中说:诗“穷而后工”等。这些都是对屈原“发愤”说的继承与发挥。然在李贽之前的这些人所讲发愤著书的那些书,是指史传、政论、诗歌、散文,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封建的正统文人所说的正宗文学。李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把“发愤作书说”用之于小说评论,而小说在过去一直都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唐代以后的文人虽日渐重视小说,也只是拿它来消遣游戏。如韩愈在《答张籍书》中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亦间乎!”到了李贽那里小说的地位不仅不再是小道消遣之作,而且可比之于《六经》《语》《孟》;不仅可比之于《六经》《语》《孟》,而且它也可以与正统诗文一样来发抒愤懑。如此来认识小说在前人中是没有的。李贽还在《藏书·司马迁》以及《续焚书》中《封使君》、《伯夷传》、《复焦漪园》等数文中发表了类似的思想。如《杂说》一文中说得就很透彻:“且夫世之真能文者,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焚书》卷三)这比之于司马迁的“发愤作书”,韩愈的“不平则鸣”那种纯是个人遭遇上的不平与愤懑来又要超出一等,李贽所说的“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显系指社会现实之事,而“欲语”则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社会进行愤怒的揭发与批判。正因为李贽对“发愤作书”有自己的认识因而对作家发愤的内容,李贽也有不同于他人的理解,即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夷狄处上,中原处下。而泄愤者则是那些“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水浒传》反映了千百年来“官逼民反”的思想,那些“啸聚水浒之强人”正是为官所压,为官所逼才走上绿林道路的农民,他们以造反、革命的形式向官府向朝廷泄其愤懑。正如李逵所说的“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李贽把农民的起义看作是农民的泄愤,不是要统治者去镇压,而是给予了同情。在李贽的其他著作里也可看到他对农民起义的同情。他把古代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窦建德等列入《世纪》与历代帝王并列;他借武帝的话赞扬赤眉军不离散人家的妻奴;他对黄巢声讨统治阶级的檄文十分赞赏,认为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所以能节节胜利,是由于天下离心,人士多附之。在李贽看来,陈胜、窦建德、黄巢正如《水浒》中的宋江一样,都是以造反、革命的形式泄其对社会对现实乃至对官府对朝廷的愤懑。李贽的这种以小说来泄愤的思想并没有为金圣叹所继承,而真正继承这一思想的则是与金圣叹同时的陈忱及稍后的张竹坡。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李贽继承司马迁以来关于“发愤作书”的思想又加上了他的前人未曾说过的新内容,有许多可贵之处。他讲发愤,不是着重于个人一己的穷通出处,即封建文人那种有才不见用、有志不得酬的怨愤,而是有比较深广的社会内容,有敢于替啸聚水浒的农民起义英雄说话的精神,这种“发愤作书”的内容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不多见的。
金圣叹明明是承袭了李贽的“《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的思想,说施耐庵是“发愤作书”(第6回批),“怨毒著书”(第18回回首总评),却又故反李说,独标新异,说施耐庵“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这就是说施耐庵并非“怨毒著书”,而是“无事作文”了,他是由于“心闲”才去弄弄游戏之笔的。这段话出自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此文放在他所批七十回本《水浒传》的前面,带有指导性意义。那么如何来看金圣叹的“心闲弄笔”或“无事作文”思想呢?
“心闲弄笔”思想实质上就是小说的娱乐观,认为小说是消闲遣闷的玩艺儿。先秦以至汉魏时,小说多出于俳优。俳优的职责就是用诙谐的故事供君主贵族逗乐,故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说俳忧之词“本体不雅,其流易弊”。到了唐代,唐人传奇已颇具规模且有较高的艺术性,然韩愈还说“此吾所以为戏耳”。宋代的皇帝喜听人讲小说以取乐,故郎瑛《七修类稿》记载说:“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日欲进一奇怪事以娱之。”绿天馆主人的《古今小说序》也说南宋高宗做太上皇以后,清暇无事,喜阅话本,“于是内?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衍进御,以怡天颜。”唐宋以后,不仅皇帝,市民乡民也争听俗讲说话,《水浒传》中就有雷横听书、李逵听书的情节,反映着城市勾栏里讲小说的盛况。陆游的“满林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和刘后村的“二女相携看市优”(《田舍即事》)记述了农民对说话的喜爱。而文人墨客对小说也有浓厚的欣赏兴趣。署名汤显祖的《艳异编序》说:“月之夕,花之晨,衔觞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现……亦足以送居诸而破岑寂。”可见,小说是供人茶余饭后所谓“饱暖无事、又值心闲”时消遣把玩的。无论是韩愈还是汤显祖,他们都看到了小说的娱乐功能,也隐约地看到了小说不同于史传的文学特性。金圣叹的思想正是循此而来,因而也并不怎么新鲜。他在批点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如“耐庵才子戏笔”(第4回批),“只将闲笔余墨写得有如儿戏相似也。”(第54回批)既是“戏笔”,那也就无需探究作品的思想内容,只须仔细揣摩《水浒传》的文法就行了,所以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里说自己最恨人家子弟不会读书,只记事迹,而不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于是他就揭出若干文法,什么“草蛇灰线法”、“背面铺粉法”,什么“弄引法”、“獭尾法”等等,一部反映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在金圣叹的总论与批点中,就成了是施耐庵弄弄“草蛇灰线”,弄弄“獭尾”的“戏笔”了。
不过,金圣叹又不能无视《水浒传》中那些草泽英雄们的怨抑不平之声,不时流露出“怨毒著书”的思想。如第六回,在林冲所说“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月赞的气”一句下,金圣叹批道:“发愤作书之故,其号耐庵不虚也。”在第18回回首总评中,金圣叹又写道:“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这里又分明是李贽的“《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的意思了。这与前文的“心闲弄笔”“无事作文”说是正相矛盾的。再细看金圣叹的“怨毒著书”,却又并非完全是李贽“发愤作书”的思想。他认为“骂官吏”“骂秀才”,虽然“其言愤激”而其实则是“殊伤雅道”的,因而“怨毒著书”虽不可责备,但却是不可提倡的。对这一点,金圣叹还有更极其错误的思想。他在《第五才子书序一》中大谈作书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样的人才能作书。他说:“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试听听金圣叹这样一付杀气腾腾的口气,这哪里是谈作书,纯是诛人烧书之论。《序一》乃是金圣叹批点《水浒传》的总纲,因而这一段话不可忽略过去。过去的研究者往往注意到前引的金圣叹的“发愤作书”“怨毒著书”两段话,却并没有把它与金圣叹的“作书”论联系起来,没有从总纲上去理解把握这两段话。孤立地看这两段话,金圣叹是赞成“怨毒著书”的,一结合《序一》来看,就不然了。金圣叹认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作书的,作书是关乎到天下的“道”与“治”的,因而它只能是圣人的事,天子的事。而施耐庵只不过是一个才子,写的又都是一群“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第五才子书序三》)的绿林强盗,所以施耐庵乃是“横议之人”,《水浒传》则是“破道与治”之书,对前者则应诛之,对后者则应烧之,一诛一烧,则“发愤”“怨毒”之声除尽,天下也就归于太平了。这才是金圣叹的真实思想。金圣叹批点《水浒》并非是真要人们随施耐庵去“发愤”去“怨毒”,他是欲借批《水浒》而达到烧书的目的。这在他的总纲性的《序一》里说的明明白白。他说:“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所以腰斩《水浒》,痛骂宋江,把《水浒》原本,条分节解,又东骂强盗西骂贼,使天下人看了他批的《水浒》后,“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而他的功劳也就可以比之于焚书的秦始皇了。因此从金圣叹的总纲《序一》来看,从他批点《水浒》的总体来看,金圣叹其实还是反对李贽的“发愤作书”说的。
二、关于《水浒传》的主题论与人物论
如果说金圣叹对李贽的“发愤作书”说在反对中还有所引用的话,那么对李贽的《水浒》主题论、人物论,金圣叹就完全是反对了。李贽认为《水浒》的主题是“忠义”,梁山人物皆是“大力大贤”。而金圣叹则大反其说,他认为《水浒》的主题乃是灭盗,梁山人物皆是“豺狼虎豹”。如此相对立可以看出金圣叹是实欲压李贽而张己说的。
李贽的《水浒》主题“忠义”说见于他的《忠义水浒全传序》。他说《水浒传》“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于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李贽把“忠义”归之于水浒,以此二字来概括小说的主题,把一部写造反、革命的书说成是宣扬封建的“忠义”观,说明李贽并没有真正把握《水浒》的主题。李贽又认为体现这一“忠义”主题的则是宋江。在《序》中,他说:“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称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这就是说宋江是“忠义”的化身,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最后率全体梁山义军接受招安,又与一些梁山英雄“服毒自缢”,“同死不辞”是“忠义”之举。李贽把对农民革命的背叛,对把农民起义队伍引上投降主义道路的宋江说成是“忠义”之才,这也是错误的。这反映了李贽有很浓厚的封建忠君思想。因而他的《水浒》主题“忠义”观是并不可取的。那么,否定了李贽的“忠义”观,就意味着金圣叹的“灭盗”论是对的吗?显然不能这么说。金圣叹的“灭盗”论也同样是错误的;不仅错误,而且是反动的。他欲与李贽相反对,故意歪曲《水浒》的革命主题,说《水浒传》一书之旨就是除灭群盗,方能太下太平,这显然也不符合《水浒传》的实际思想内容。他的《第五才子书序二》即是专篇针对李贽的“忠义”观而作的。他说“施耐庵传宋江,而题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着重号引者加)接着就发了一通关于“忠义”的腐论。在第70回总评中,他透出了与“忠义”相对的“灭盗”观。他说:“聚一百八人于水泊,而其书以终不可以训矣,忽然幻出卢俊义一梦,意盖引张叔夜收讨之一案以为卒篇也。呜呼!古之君子,未有不小心恭慎而后其书得传者也。吾观《水浒》洋洋数十万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之,其意可以见矣。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哉。”他欲反李贽之说,不惜把《水浒》后五十回写宋江受招安征四寇的内容全部砍掉,结以卢俊义一梦把梁山“强盗”全部除灭,也就把李贽所宣扬的“忠义”削掉,而还《水浒》“灭盗”的本意,也即他自己所说的“削忠义而仍《水浒》”。(《序二》)把后半截的“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削掉,而对“忠义”的化身宋江怎么办呢?金圣叹是不遗余力地痛加诋毁,同时兼及李贽。他视李贽是村学先生,读《水浒》,“每每过许宋江忠义”,是“其人性喜与贼为徒”,(第1回总评)又说:“村学先生团泥作腹,镂炭为眼,读《水浒传》,见宋江口中有许多好语,便邃然以忠义两字过许老贼,甚或弁其书端,定为题目。”“夫宋江之罪,擢发无穷,论其大者则有十条。而村学先生犹鳃鳃以忠义目之,一若惟恐不得当者,斯其心何心也!”宋江“一心报国,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诱人入水泊”的芳饵,“彼村学先生不知乌之黑白,犹鳃鳃以忠义目之,惟恐不得其当,斯其心何心也!”(第57回总评)金圣叹骂宋江把李贽也连带进去,不但蔑起为“村学先生”,而且说他“性喜与贼为徒”。骂宋江为盗,也就是斥李贽许其“忠义”为非。显然,金圣叹“独恶宋江”,是与他认为的《水浒》的主题是“除灭盗贼”有关的。然而,《水浒》的主题既不是李贽说的“忠义”,也不是金圣叹说的“灭盗”。如前所说,《水浒传》是一部宣扬农民起义农民革命的书,而金圣叹则欲“歼厥渠魁”(《读第五才子书法》)宋江,并欲借一梦而收剿梁山全伙,实足以表明金圣叹对《水浒传》主题思想的错误认识,和反对农民革命的地主阶级反动性。
李贽的“忠义水浒”的主题虽不可取,但他对梁山人物的评价应该说是正确的。李贽认为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的人,之所以归于水浒走上造反的道路,是北宋末年的黑暗政治造成的。“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所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原是孟子的思想。《孟子·离娄》里说:“孟子曰,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德,大贤役小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孟子说的是战国时各诸侯国的关系,李贽说的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内不同阶层和不同类型人物的关系。北宋末年,四贼当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许多有才有识、有真本领的豪杰人士屈沉于下,为上层极少数昏庸贪浊的人所支配,所压抑,所打击,正如林冲感叹的那样:“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月赞的气。”这种现象的存在正是北宋社会政治秩序不能稳定的重要根由。李贽批点《水浒》,倡扬“忠义”,其目的正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他曾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对那些“大力大贤”的农民起义领袖表示十分的赞赏。如前面提到的陈胜、窦建德、黄巢。他尤其对当时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的“巨盗”林道乾“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以至“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这样的豪杰之士表示钦佩。在《因记往事》一文中,他分析了“盗贼”横行的原因,认为正是处于黑暗环境的底下,“举世颠倒,使英雄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才使那些英雄好汉“直驱之为盗也”,而这些“盗贼”实质上却是“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的”英雄。李贽甚至向统治者提出方案说:“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绝不敢肆。”(《续焚书》卷四)在李贽看来,林道乾也是一个“大力大贤”的人,若不是举世颠倒,英雄怀戚,逼而为盗,那么他也会是一个忠于朝廷,治海有能的干才。看李贽对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的赞赏,尤其是对林道乾为盗的分析,也就能理解李贽对水浒之众的赞扬了。他反复称说《水浒》是一部张扬“忠义”的书,水浒中的人物不仅“大力大贤”,而且皆是“有忠有义”的人。所以,李贽希望君主、宰相和大臣们皆来读一读《忠义水浒传》,关注了解那些屈沉于下,逼入水浒的众多能为国尽忠的有识之士、有用之才,努力改变他们被压抑的状况,不要把这些人再驱之于梁山,逼之入水浒;他甚至希望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对统治阶级内各个阶层、各个集团和各类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对权力的分配进行调整,以恢复或建立他理想中的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久的统治,使忠义真正能够存在于朝廷,存在于君侧,存在于干城、腹心,而不是存在于水浒之中。李贽实际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痛惜有才能的人没有被统治阶级任用来改善政治状况,巩固封建制度。由于历史的局限,李贽当然还不可能超出那个时代,更不可能超出他所属的那个阶级。李贽毕竟只是一个地主阶级中有政治远见、政治卓识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尽管抨击黑暗,反对权奸,但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天下能去除腐败政治,去除贪墨官吏,希望社会能够稳定。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靠谁呢?就靠那些水浒之众,靠那些大力大贤有忠有义的人。李贽对这些逼入水浒的“盗”表示同情与赞扬,可见其对《水浒》中的人物是肯定的。
金圣叹在这点上与李贽又是大唱反调的。他既不同意以“忠义”许《水浒》,当然也就不能同意以“大力大贤”来许水浒中的人物。他说:宋江等一百八人,“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扑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第五才子书序二》)金圣叹把梁山农民起义的英雄皆看成是“豺狼虎豹”之兽,是“杀人夺货”之徒。他们远在水浒,皆是“凶物”与“恶物”,所以必须天下共击之,天下共弃之,直至剿尽杀绝。在批点中,他还抓住梁山好汉的绰号大加污蔑。如第8回中写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两人出场,金圣叹抓住他们绰号中的“虎”、“蛇”曲解,说这是梁山泊“一百八人之总号”;林冲绰号“豹子头”,金圣叹说:“则知一百八人,皆恶兽也。”(第14回批),李逵绰号“黑旋风”,柴进绰号“小旋风”,金说“旋恶物聚于一处故也。”(第10批)李逵下枯井救柴进,金说:“今两旋风都入高唐枯井之底,殆寓言当时宋江扰乱之恶,至于无处不至也。”(第53回批)“地煞星”朱武在《水浒传》第5回中出现,金圣叹便把它解释成这是因为《水浒传》所写的一百八将都是“逆天而行”的象征之故。尽管金圣叹在批点中也说武松、鲁达、林冲、李逵是上上人物,那也只是从这些人物的个人的品质,从小说塑造性格的角度来说的,不可否认,金圣叹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但是一入政治的轨道,他对梁山人物在总体上是完全否定的。
综上比较可见,金圣叹从创作论、主题论、人物论三方面皆反李说,李说施耐庵“发愤作书”,金说施是“心闲弄笔”;李说《水浒》宣扬“忠义”,金则说是除寇灭盗;李说梁山人物皆“大力大贤”,金说是“豺狼虎豹”。总之,金圣叹在《水浒传》思想内容的重要方面,都欲与李贽分庭抗礼,而力标异说,以显己见之独特。然而,虽独异,但并不正确,且太反动。而李贽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忠义水浒说”虽不可取,但他希望“忠义”能够存在于朝廷,存在于君侧,存在于干城、腹心,其用心是十分良苦的。他认为《水浒传》是发愤之书,梁山人物皆“大力大贤”,如此识见,直至今天,仍有其理论价值和认识价值,是金圣叹所远远不及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