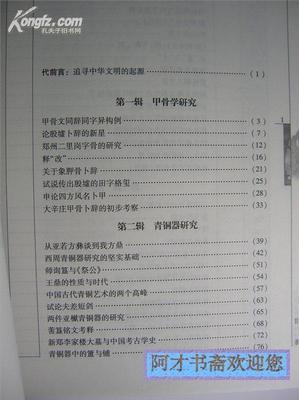韩戍《储安平传》(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后,我感觉需要对二十多年来的储安平及《观察》研究作一个小结。韩戍《储安平传》在这一阶段的储安平及《观察》周刊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收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一阶段中一个成熟的研究成果。学术史上常有“后出转精”的说法,但不是所有的后出成果都能超出前面的研究,这其中除了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评价及相关史料的发现外,还有研究者的心理动力,也就是说一个常见的研究对象是否还需要重新投入自己学术兴趣和精力去完成,这本身也包括了研究者对所选研究对象的判断以及对研究对象复杂性与丰富性的理解,韩戍对此有很清晰的意识,同时也有自信的判断。当我看到眼前这一部《储安平传》的时候,我认为韩戍对自己所选的研究对象的判断是富有想象力和判断的,因为他用自己新发现的史料和对史料的分析,再一次丰富了储安平的人生经历,同时解读了他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学术研究中选题很难,尤其旁人已做过的研究再要出新更难,但韩戍敢下这个决心,确实需要坚定的学术勇气。
储安平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大约是在1989年初,当时戴睛完成了《储安平与“党天下”》,展示了对了历史人物可能引起时代反映的敏感,在储安平及《观察》周刊的研究中,这个传统始终延续下来,即储安平及《观察》研究不纯粹是一个孤立的学术问题,它一定是建立在时代现实的真实感受中,章诒和写储安平的散文,同样也是这个传统的延续。这也是储安平在近二十多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总是在不同阶段可以引起时代回声的原因。到韩戍研究储安平的时候,应当说储安平的历史地位已经凝固了,启蒙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再把他作为个案来研究,需要对历史现象的极端敏感和判断,一般研究者可能回避,但韩戍选择了坚持,最终完成了这部《储安平传》,这个学术自信相当重要。
储安平研究是在启蒙时代开启的,一开始它的学术追求就没有简单停留在一般的报人和作家研究上,而是把重心放在了重新寻找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精神源头上。上世纪八十年末,最早自觉意识到储安平及《观察》周刊自由主义传统的是余英时和汪荣祖,他们分别在重新评价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时,对储安平及《观察》周刊给予高度评价,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储安平及《观察》周刊才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至少我自己是由此才开始试图全面了解储安平其人和《观察》周刊的。多少年后,我才知道1984年就有一位日本学者平野正完成了《储安平的立场与〈观察〉周刊的性格》的长篇论文。2009年夏天,我到厦门后曾开过一个“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在会议论文集中刊出了平野正的论文。当时陈永忠在台湾出版了《储安平评传》,加上我2004年公开出版的《储安平与〈观察〉》,算是这一阶段比较专注于储安平研究的几本书。这期间有大量的学位论文选择储安平及《观察》周刊为研究对象,零散的文章也时有刊出,但多数是冷饭重炒,能静心搜求储安平生平史料和佚文遗事的,我以为非韩戍莫属,我要对他的学术判断和学术耐心表示敬意。他敢于选择储安平为研究对象,内心肯定先就存了一分对先贤的敬意,同时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勇敢,因为储安平研究的风险有时候还不体现在学术史料的搜求难度上,其它方面的顾虑也常常让学者望而却步,而韩戍选择了继续前行。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近年能够进入公共话语的,似乎只有《大公报》和储安平的《观察》周刊。进入公共话语,意味着研究对象成为脱离专业研究的公共常识,也就是说离开专业研究,他们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谈论的热情,不是所有研究对象都有这样的命运,只有那些人生选择和个人命运包含了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人,才可能获得这的历史机遇,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为历史而生的,历史自然不会忘记他们。具体到储安平而言,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人中并不突出,但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每一次选择,却总能体现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对时代的敏感程度远超于他的专业成就,所以他可能是永远会被人谈论的对象,而多数在专业上远胜于他的同代人并没有这样的历史荣耀。1992年我写《〈观察〉研究》时,我就相信这个人以后会不断为人谈起,因为他为历史付出了他的勇气和智慧,今天看到韩戍的《储安平传》,我更感欣慰。
韩戍是许纪霖先生的学生,纪霖先生是我们这一辈人中最早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学者,韩戍能选择为储安平立传,我想他的学术灵感一定与纪霖先生有关,韩戍在学生时代即能完成这样一部传记作品,不要说纪霖先生了,连我这个仅见过韩戍两面的人,也为纪霖先生感到自豪,有这样的学生,我们做教员的人,对以后的学术事业应当更有信心。
韩戍掌握储安平史料是我目前所知最完整的,我后来没有再继续关注这个题目,一是学术兴趣转移,再是感觉储安平史料再发现很难,但韩戍在这方面的判断显然比我高明,他不但发现了相当多的新史料,更发现了相当多的储安平佚文并且整理出版,在这方面韩戍表现出了相当出色的学术素质,同时也展现了相当优秀的学术潜质。
韩戍这本书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我略说两点。
韩戍生活的时代,获取史料的第一手段是网络,网络的第一便捷是发现史源,但要真正得到史料,也还不是一件易事,韩戍在这方面的努力很成功,只要有史源的,他绝大多数得到了,所以这本《储安平传》是我所见史料最丰富的一本,再发现新史料的可能是存在的,但要超出韩戍则有极大难度,因为韩戍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再一点是韩戍扩展史料的能力很强,他能在已知史源的方向上,扩展很多史源方向,比如在储安平的生平史料中,对端木露茜及储安平交游人物史料的发现,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同时韩戍也非常注意域外史料的获得,比如欧洲方面的史料,他在台湾早期情治部门的档案中也发现了储安平史料,这体现了韩戍成熟的史学训练。

2015年5月18日,我参加完储安平衣冠冢揭墓仪式后,在回厦门的高铁上读完韩戍《储安平传》,当时我就想为此书写一篇书评,谈谈自己的感想。我当时的阅读感受是这本书在储安平史料的搜集上花了很大功夫,为进一步提高储安平研究的学术水平加厚了基础,但韩戍对储安平的理解,我以为可能与其师纪霖先生和我这一辈关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人还有区别。这是本书的优点还是缺点?我一时不好下断语,但我感觉在对储安平的理解上,我们这一辈人有比较强烈的时代感受,而韩戍可能更多学术判断,简单说就是,我这一辈人,多看储安平的优点,而韩戍这一代学者可能凡事更愿意用客观和学术观点来来判断。比如对储安平思想倾向的理解上,我们更愿意将储安平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而韩戍则特别愿意评论储安平身上的民族主义特征,就一个人的思想倾向来说,说储安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似无不可,但就其一生事功判断,最后可能是自由主义思想起了根本作用。还有对储安平当年对希特勒的一些赞扬言论,韩戍的评议似乎也稍嫌简单,其实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多以动态和结合世界局势变化来判断,方能更切近事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可能有他们自己成长时代的特殊性,当对国家的感情和自己思想倾向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身上通常表现出浓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这可能也是一个时代印迹,不独储安平,其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何尝不如此?但在思想倾向上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判断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个人以为大体还是不错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曾经中断,所以我这一辈人中,凡在一些历史人物身上发现了自由主义思想倾向,都感觉亲切,有时候愿意夸大他们身上这方面的优点,这是肯定的。我们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当代情感和思想倾向不自觉带进研究对象中,这是难免的,但我至今也还不完全否定这种感情,因为理想的历史研究,很难成为一种纯粹对客观历史知识的追求。我要说,在客观历史知识的追求方面,韩戍这本《储安平传》远胜于我那本《储安平与〈观察〉》的小册子,但在将研究对象与个人历史处境结合的情感交织中,我以为我的情感多,而韩戍的情感少,我忽略储安平身上的缺点(有些是我当时还不知道),但有些是我有意为之,我愿意夸大他身上的某些自由主义思想火花,但因为时代变化的原因,韩戍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了,这可能是一种学术进步,但我们愿意将历史研究和时代处境联结的追求,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可取处。这也许就是所谓一代有一代的学术吧!
2015年7月2日于厦门
(来源:思想者博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