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浑浊,周围充满了寒冷凄凉和空寂,让人产生一种挣扎在悲哀中的感觉,在痛苦中承受着凛冽冰雪残酷的折磨,就在人们混混噩噩的卷缩在这荒原死寂般的蹂躏中困厄潦倒时,孙飞喊了一嗓子:前边有灯光。是的前边确实有灯光,可是灯光跟我们这帮拉车着急回家的人有啥关系?那里距离真正概念的家,还有很远的距离。打头的说:那是造化合作社,谁带钱了?进去买口酒喝吧没人搭茬。孙飞说没问题。打头的说大伙猫腰哇,欢走几步。有酒对小半拉子来讲那太有吸引力了,几个小生牤蛋子,卯足劲,一撒欢就到了。造化合作社晚上九点下班,现在是晚上七点半多了。人们摘下自己的缰绳,吱溜吱溜的像水中的鲫鱼,全都从黑乎乎的毡门帘子底下钻进了合作社,合作社里通长的大屋子,只有一个大火炉,火炉上过火暖道骑着半个大汽油桶,汽油桶被高焦油煤燃得通红通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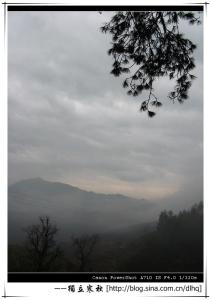
此刻,被十几个大冰坨似的冰人给围上,顿时,有些暗淡。就在大家嘶嘶呵呵的烤火得当,孙飞把两瓶老龙口和几根香肠还有一包猪头肉,摆到了炉子边上的暖火墙上,这时候人们也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了,大家伙轮着嘴对嘴的吹开了喇叭,一大根粗大的香肠,也是你咬一口他咬一口的咬着吃,那些平时装的扭扭捏捏假装干净的女社员女知情们,此刻也不嫌男社员这个的牙黄那个的口臭了。那家伙吃便宜谁不吃呀,造吧,呵呵呵呵,大家吃完喝完一抹拭嘴巴头子,走人了。大车依然在线道上滚动着,然而这回的速度可是快多了。大家肚子饱了心里暖了,走路的步子迈的也大了,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禁了。也就从这件事以后打头的跟孙飞的关系,那是成好了,就是一个字好。其实那天的事,除了打头的,还有我知道,孙飞是乘大伙烤火的功夫转到下杂那边把卖下杂的钱匣子给摸了,又到食品这边买的酒肉,这一切都被大头的给看个清清楚楚,很快左桐铺子的灯光就在远处一眨一眨的欢迎我们了。
这就是我们下乡之后的第一次参加生产劳动的经过,那场寒冷的暴风雪,一直暖暖的保留在我苦难的记忆里,让我终生不忘。
作者:铁工厂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