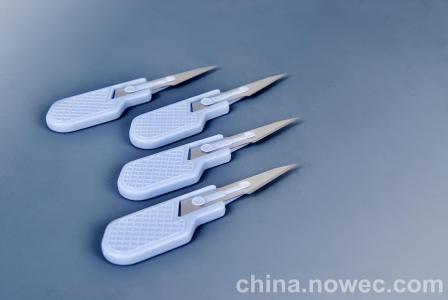《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第31篇。今本《中庸》在传衍过程中被后世者附益,其修改定本当在战国晚期,但其中主要思想观点却源于子思。汉代南朝,不断有人研究《中庸》。唐李翱以后至北宋,诸大家都有独立研究《中庸》的书。二程夫子推尊《中庸》,认为是孔门传授心法,朱子亦大力表彰,作《中庸章句》,使之成为《四书》之一,风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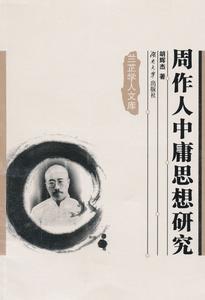
“中庸”的思想,起源于上古时代。《尚书》之《周书》中,有《洪范》与《吕刑》篇,都提倡中道。《洪范》高扬“三德”,以正直为主,有刚有柔,求得刚柔相济的中正平和。《洪范》的“皇极”,即是“无偏无陂(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的政治哲学智慧。所谓“极”,原指房屋的大梁,乃房屋中最高最正最中的重要部分,引申为大中至正的标准。
《中庸》开宗名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说,上天所赋予的叫做“性”,遵循着本性而行即是“道”,使人能依其本性而行,让人之道不断地实现,便叫做教化。《中庸》说的“天”,是使一切存在能成为存在的“天道”。“天道”流行,生生不已,使一切存在发育生成,持续变化。这里的“天”与“天道”是形而上的实体,创造性真几,宇宙生化的本体,一切存在的最高规律,它本身也是不停息地创造活动着的。“天命之谓性”,是说宇宙万有之性,根源于生生不息的天道。一般说人性、物性,是就物的形质、相状或物之经验的所以然而言,但《中庸》以天道为性,即万物以天道为其性。性是天道落在各存在物之存在上说,所以此性字的意义,不是物的形质结构,不是各物的生理自然之性,不是由此类相状概括而成的“本质”,而是使一切物得以生存、存在的创造性的原理。此性是绝对、普遍的。《中庸》是一套形而上的理论,是要对一切存在作一根源性的说明。“率性之谓道”,即一切人物都是自然地循当行之法则而活动,循其性而行,便是道。一切物的存在与活动,都是道的显现。如就人来说,人循天命之性而行,所表现出来的便是道。如面对父母,便表现孝等。这些表现是依循天命性体而不已地实现所开出来的。天道通过人的率性而实现其具体内容。因为气质的障蔽,人不能循道而行,所以须要先明道,才能行道,而使人能明道的,便是教化的作用。一般人要通过修道明善的工夫,才能使本有之性实现出来。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道是一切存在物之存在之理,当然是一切存在物片刻不能离的。虽然道无所不在,但在现实上,人为欲所限,不能循性行道,常会离道、悖道。所以君子常存敬畏之心,作戒惧的工夫,谨慎地要求自己,使自己之心思、行为,在任何场合都合于道。天命之性是超越的大本,至隐至微,所以人必须以戒惧的心情来奉持之。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情感未发之前,心寂然不动,没有过与不及的弊病,这种状态叫“中”。“中”是道之体,是性之德。如果情感抒发合于中道,恰到好处,无所乖戾,自然而然,这就叫做“和”。“和”是道之用,是情之德。“中”是天下事物的大本,“和”则在天下可以通行,谓之“达”。君子省察工夫达到尽善尽美的“中和”之境界,那么,天地安于其所,运行不息,万物各遂其性,生生不已。
《中庸》托孔子之言,指出五伦为五达道,即人人共由之路,普遍之道;智慧、仁爱、勇敢为三达德,即实践五条路的三种方法。“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的“一”是指的“诚”,即落在诚实、至诚上。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里,根本是修身,此是内圣,治人是外王。这与《大学》的主张是一致的。
《五行》论述了“天道”与“人道”的区别与联系,《中庸》也是如此。不过《中庸》是托孔子之言,以“诚”为枢纽来讨论的。“诚”的本意是真实无妄,这是上天的本然的属性,是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本道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天道公而无私,所以是诚。“诚之者”,是使之诚的意思。圣人不待思勉自然地合于中道,是从天性来的。普通人则有气性上的蔽障,不顺遂地尽天命之性,所以要通过后天修养的工夫,使本具的善性呈现出来。这是经由求诚而最后达到诚的境界的过程,求诚的工夫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中庸》认为,由至诚而后明善,是圣人的自然天性;而贤人则通过学习、修养的工夫,由明德而后至诚。由诚而明,由明而诚,目的是一样的,可以互补。“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天下至诚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于是能够兴养立教,极尽众人的本性,进而樽节爱养,极尽万物的本性,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既如此,就可以赞助天地生养万物。这使得人可以与天地鼎足而三了。人的地位由此彰显。这也是首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意思。人体现了天道,即在道德实践中,见到天道性体的真实具体的意义。
《中庸》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里是讲人道,意思是说:诚是自己实现、完成、成就自己,而道是人所当自行之路。诚是使物成其始终的生之道,没有诚也就没有万物了。所以君子把诚当作最宝贵的东西。诚一旦在自己心中呈现,就会要求成就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一切物。当人的本性呈现,仁心呈现时,就从形躯、利欲、计较中超脱出来,要求向外通,推己及物,成就他物他人。仁与智,是人性本有的,扩充出来,成己成物,即是兼物我,合外内。人之本性圆满实现,无所不通,举措无有不宜。
《中庸》还提出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平凡与伟大的统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既保护、珍视、养育、扩充固有的善性仁德,又重视后天的学习、修养;既有远大的目标,又脚踏实地,不脱离凡俗的生活世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追求真善美的合一之境,实现崇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