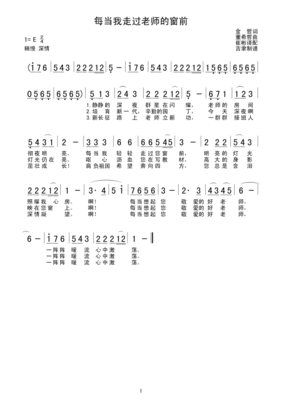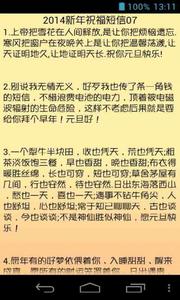佚名
我永远在沙岸上行走,在沙土和泡沫的中间。高潮会抹去我的脚印,风也会把泡沫吹走。但是海洋和沙岸,却将永远存在。
——纪伯伦

岁月的影子,漫洒过那道记忆的篱笆。菊花,开在这个孤单的季节。微风过后,盈袖的暗香,钻进灵魂的罅隙。如酒沉醉,如雾缭绕。
雨季,还没有到来。
阳光,懒懒的,暖暖的,在视线之内弥漫出天空的灰白。沉寂,也不是这个时刻的所有。红尘的喧嚣,远着,近着,激越着,颓废着。是一种真实,也是一种现实。
窗口的风,总是那么的自由。拂面,带着午后的慵懒,带着阳光的温暖,也带着穿堂入室的肆无忌惮。
我,站在风口。仰望,是天空那略带灼目的澄净。俯观,是来往如蚁的车辆行人。凝目,则是高低层立的钢筋水泥。远视,是那隐约连绵的山峦。一切,是身处红尘的真实,一切,是无可置疑的存在。
在这样的世界面前,我经常的呆立;在这样的呆立里,我时常的失语。
或许,我想感悟什么,我想感慨什么,只是,被压抑的灵魂,在瞬间柔软的间隙里,只是扑棱了下,如那天空中掠过的小鸟,转瞬没了踪迹。
下午上班途中,没来由的,我在绕着自己的思维。
你不是我,我不是你,那么,你是谁?我是谁?
你不在这里,我不在那里,那么,你究竟在哪里?我究竟在哪里?
其实,这或许是很简单的问题,也是我经常性的与自己的思维游戏。只是,那么简单的答案,我却始终不想找出来。或许,是我自己内定的答案无法被承认无法被证实后,聊以自愚的一种方式?
其实,知道,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的与完整,我的自由与虚幻是两个不同的真实存在。你的幸福与微笑,我的暗夜与孤单是两个无法重合的独立。但是,为什么在一些时刻,会想起一个泥人。想起遥远的记忆力,有童稚的声音咿呀着:捏一个泥人,一班是我,一半是你。捏一个泥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想着,想着,天突然黑了,夜终于静了。
其实,知道你在那里,在我无法触及的世界,在我无法凝视的远方。也知道,我在这里,在你无法到达的世界,在你无力凝视的远方。只是,为什么还是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想起一些呢喃,想起一些私语。想起一些现在都无法去确定也没有必要确定的对错,想起一些今生都无法实现的美丽。也,想起,那一杯爱尔兰咖啡,那一杯融入了以滴眼泪的爱尔兰咖啡和那一个滴下眼泪的纠葛的故事。
有的时候,是知道一些事情只是由于一些隐藏在骨子里的无法改变的固执而有了那些无法欢欣的忧伤的结局。
有的时候,是知道这颠沛的人生不过是因为思绪钻进了没有前路的死胡同钻进了没有明天的昨日才有的必然因果。
只是,知道又如何?就如知道春夏秋冬是轮转的,生老病死是必然的,爱恨悲欢是必经的,离合聚散是肯定的,知道这些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并不是我们甘心的。又能如何?我们,还是一步一步走在这些愿与不愿想与不想里,满目繁华过后的荒凉,满心希望之后的落魄,满身激情过后的颓废,且,没有退路。
有的时候,真的累了,只想停下来。停下这跋涉的脚步。停下这不由自主的走向黄昏。可是,真实的灵魂告诉我,停下来不是我的本性,停下来不是我所能。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向后走都可以,只是不能停止灵魂的跋涉,不能任由自己停在沉沦里,停在没有路标,没有航向,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黑暗之中。哪怕是走向黄昏,走向落日,走向那未知的荒漠,走向那无垠的流浪,也好过如一潭死水,无波无澜的等待干涸。
或许,这样的境界是一种混沌,这样的思绪是一种混乱。只是,历尽沧桑后,还有什么可以清醒清晰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纪伯伦的《沙与沫》有这样一段话:我对我的房子和道路说,“我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如果我住下来,我的住中就有去;如果我去,我的去中就有住。只有爱和死才能改变一切。”
曾经,对着这段话发呆。不知道算不算沉思的发呆。也曾经,面对着无边的黑暗,在心里反复回味着它。只是,尽管似乎看到了远山之上的点点荧光,尽管看到了夜幕深层隐约的星月,可是,我依然看不穿那黑暗背后的真实,依然看不破这红尘之内的虚幻。只是,从此学会了安静,从此学会了接受,也,从此学会了独行。
记得有一天,小家伙问我是什么性格。我说,内向吧。她说,是。
然后,她又问我属于什么小动物。我说,蜗牛吧。她哈哈笑了,我也淡然一笑。
或许,牛就是牛。无论是西班牙的斗牛还是背着壳的蜗牛,都是真实的,都是存在的。都是一种人生,一种命运。
岁月的影子,漫洒过那道记忆的篱笆。菊花,开在这个孤单的季节。微风过后,盈袖的暗香,钻进灵魂的罅隙。如酒沉醉,如雾缭绕。
淡淡迷路,静静走过。在下一个冬天来临前,终将是一秋的落尽繁华。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