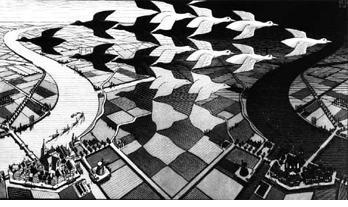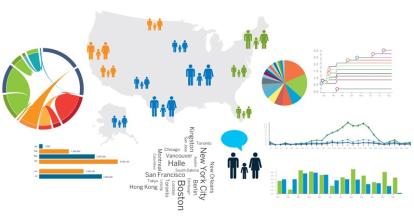鲁迅“恨”与“梦”中的潜意识
——《药》的重新解读
概括地说,《药》象征性地表现了鲁迅两种思想精神,一种是鲁迅对国民性绝望的认识,另一种是鲁迅对绝望的国民性启蒙的殉道精神。对国民性绝望的认识和启蒙思想及殉道精神,是鲁迅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精神。无疑,《药》是这种思想精神最深刻的体现。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药》或者说鲁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精神——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上,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上,也是一种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思想精神?正是这种思想精神的绝无仅有和独一无二,才产生了对鲁迅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高度评价。从思想家到政治家到学者,从文学界专家到最普通的大众读者,都对鲁迅给予最高的肯定。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精神是最深刻的,鲁迅的小说是最有价值的,鲁迅是民族魂,鲁迅的文化方向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方向,等等。问题是,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深刻的思想,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的小说,为什么会成为思想家、革命家式的文学家?这个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周作人在谈到鲁迅的学问和艺术上的成就时,曾说“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特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关于鲁迅》)。但周作人关于鲁迅创作起因的久远,无非是追溯鲁迅童年时代的阅读和后来的人生经验:“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关于鲁迅》)。更多的论者从前期的进化论和后期的阶级论来论述鲁迅的创作,更重视鲁迅后期实行和现实生活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周作人所说的书本知识和后来论者所说的现实生活对鲁迅的创作确实发生着影响并且是重要影响,但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人的童年情结对人却发生着最重要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人在生命最初的时间里,“某些印象已被固定的,并且对外部的反应方式也已建立,反应方式的重要性永远不可能被后来的经验抵消”(《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第467页)。人在童年时期“反应方式”之所以建立,反应方式之所以不能被后来的经验抵消,就是因为“情结“的缘故。情结是由一种严重的心理创伤形成的潜意识心理。情结“主要是描述一组感觉和观念。这些感觉和观念互相关连,由个人情绪经验中的一个重伤害产生出来”;“它是这样产生的:一个人在过去成受某一件事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的伤害,大得使得他潜抑了它,把它埋进潜意识里去。于是它像从地毯下被扫走一般,不再被他意识到,但是仍留在他的心理上”;“这些伤害一旦被潜抑下去,就象一块放射性金属。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害处,其实它却能放出一种能量,影响周围的每件事物,而那最初的情绪伤害就想隐藏在潜意识里的金属一般”(约瑟夫·洛斯奈:《精神分析入门》,郑泰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8、29页)不能得到治愈的严重心理创伤形成了一种潜意识,对人永远具有巨大的支配力量。
鲁迅创作所表现出的“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就与他的童年情结有关,以《药》来说,鲁迅的童年情结与《药》的主题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药》所表现的对国民性的绝望认识和对这种绝望的国民性的殉道性启蒙,是鲁迅童年情结借着生活素材进行艺术虚构时的象征化复现。
鲁迅对国民性的绝望认识,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童年的严重心灵创伤即童年情结。这种童年情结是长在他生命最深处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因而由这情结生成的东西才不是外在于他人格的知识、观念、学问,而是属于他内在的人格的核心内容。鲁迅的童年情结与鲁迅特有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人生方式和斗争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关系,鲁迅的童年情结是鲁迅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底色,是鲁迅对国民性深刻认识,对中国文化深刻认识,甚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深刻认识的最基本思想基础。
鲁迅后来的人生感受和选择都和他这种童年情结有关;比如,在日本的幻灯片事件,正是在他童年的深刻的生命感受——人们的愚昧麻木冷酷基础上,才使那在一般人看来平常的幻灯片在他看来是中国人“看与被看”的一种悲剧;也正是这种绝望的生命感受,才导致鲁迅从他可恨的故乡去异地寻“别样的人生”;才导致他从水师学堂、陆军学堂转到医学学堂,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转到以文学改变国民劣根性的理想;甚至,他绝大多数小说表现出的“看与被看”和“吃与被吃”两种意象、两种模式,即两种象征符号,都是由他童年情结所决定的。
鲁迅的童年经历过一种重大的精神创伤,这种重大精神创伤构成了鲁迅精神的一个重要情结,
鲁迅的童年情结是在鲁迅特殊的童年经历中形成的。鲁迅少年时代经历了中医误
治父亲的病和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变故。鲁迅出身于一个大的家族,他是这个家族的长子长孙,因为家境好,周围的人们把他看得像王子一般,然而,家境突然败落,周围的人们又把他看作叫花子一般。在祖父入狱的变故中,小小的鲁迅不仅深深地感受到了一般人的卑琐和狭隘,更感受到了家族人的自私和无耻;不仅深深地深深地感到了世态炎凉;更深深地透蚀骨髓地感受到了人的恶劣本性。在父亲的治病过程中,鲁迅又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医的害人(后来导致了鲁迅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认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还在追溯这种最初的生命体验:“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和首饰去,在诬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这使鲁迅对中医连同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而家庭的变故又使鲁迅对中国人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岂止鲁迅,鲁迅的祖父和父亲在家庭的变故和父亲的大病中,都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精神变态。祖父从狱中出来,脾气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破口大骂,骂人时还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响;本来温和的父亲,也变得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地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鲁迅除了震惊于外人的卑劣之外,还震惊于自己亲人人性的扭曲畸变。周围的人深深地伤害了对人性抱着美好愿望的纯真少年。鲁迅之所以不能反抗这种深深的伤害,其原因,不仅在于童年的鲁迅不可能象祖父和父亲那样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愤懑和怨怒,不仅在于童年的鲁迅没有力量去改变现实,更在于,这些伤害不是来自哪一个人,而是来自普遍的人性,是像雾一样弥漫在空气中弥漫在所有人身上的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对这种东西鲁迅无从反抗。正因为这样,他就只能把的对人的怨愤、愤怒、仇恨这种精神创伤积淤、压抑自己的内心中,对人的绝望和对绝望的人的改变的愿望就形成了鲁迅被压抑的潜意识情结。鲁迅祖父和父亲的压抑随时都以各种方式宣泄出去了,但童年的鲁迅只能把这种仇怨深深地压抑在潜意识之中。这就形成了鲁迅童年情结的特殊内涵。这期间,鲁迅读过的书中有两部强化了鲁迅的童年情结,一部为《蜀碧》,另一部为《立斋闲录》。前一部是写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情形的,后一部是记述永乐皇帝毫无人性的残暴的。鲁迅家境的变故使鲁迅从现实生活的角度透彻骨髓地感到了人的非人性的本性;而读到的野史又使他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感受到了人的吃人的本质。1927年在广州时,他对青年学生说:“我小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59页)。“从那时起就,我就恨这个社会”,这应该看作是鲁迅对自己童年情结的最好阐释。这“恨”就是压抑的思想情感的表现。这“恨”其实就是压抑,里面就包含着屈辱,包含着绝望,包含着改变的愿望,包含着想改变而无法改变的无可奈何的思想,包含着一种无法释怀、无法排谴、无法宣泄的悲愤和苦闷。
鲁迅的童年是压抑的,其中还包括父亲的压抑,《五猖会》是几十年后还写到的他小时候“笑着跳着”地去看迎神赛会,父亲却偏偏在看迎神赛会的路上要他背书的事——“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精神分析理论曾经深刻地研究出一个规律,一个人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形成的情感虽然被压抑下去了,但不是被终消灭了,而是留在了潜意识中。这种被压抑的潜意识内容在后来的生活中时时寻求表现,以得到心理平衡。鲁迅人生后来的所有重要思想行为几乎都与它的这个被压抑的潜意识情结有关。正是这个情结成了支配鲁迅一生思想和行为的巨大心理动力。鲁迅不只有“恨”,还有“梦”,鲁迅的“恨”和“梦”都是由他的童年情结构成的。鲁迅的人生追寻其实是鲁迅的一个梦,而这个梦的思想动因就是他的童年情结。他到异地求学与这个童年情结有关,他到异国学医,与这个童年情结有关,他由学医而变为弄文学还是与这个童年情结有关。表面看来,他的行为是被他的意识支配的,而实际上,是受他的童年情结驱使的。弗洛伊德说:“一个意识的愿望,只有当它成功地唤醒一个与它具有同样意旨的愿望并从中
获得强化时,方能成为梦的激发因素”(《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689页)。弗洛伊德所说的那个“唤醒”的愿望是指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正是鲁迅童年情结中的“恨”(当然包含改变的愿望)才导致他不断地转换学业,最终把人生的理想追求固定在文学上,那是因为,文学这个“梦”成功地唤起了他童年情结中潜意识。在文学这个梦中,他可以宣泄被压抑的对人的怨怼和绝望、悲愤和苦闷,他可以用它来揭出国民的劣根性,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阐述的他的梦的转变过程,恰好说明了鲁迅童年情结作用的结果:“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但“幻灯片”事件却使鲁迅受到了巨大刺激,上课时看到的一个中国人“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从而做出重大抉择——“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鲁迅之所以看到一个中国人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而认为那“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那是因为,赏鉴示众的幻灯片触动了他的潜意识情结,使他“恨”“看与被看”的“反应方式”重新被激活;而他认为当医生“并非一件紧要事”,而只有文艺才可能改变国民精神,那是因为,他在潜意识中已经感悟到,只有文艺才能表现童年情结中的“恨”,才能表现他所体验到的“看与被看”的意象和模式,才能表现人们的愚昧和麻木,才能宣泄自己的压抑和苦闷。 但鲁迅的绝望的情结又使鲁迅深深地感到救治国民愚昧麻木灵魂的艰难。“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摧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明明知道绝望的灵魂难以救治甚至不可救治,为什么还要去救治呢?这种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当然表现了鲁迅的殉道精神,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仍然与他的童年情结有重要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就是他童年情结所使然,是他童年情结中的梦即潜意识愿望所决定的。鲁迅自己就曾坦诚地说“我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个梦当然是指把文学创作看作那个(改造国民性的)梦,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个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创作的梦其实是来自他童年情结的对国民性绝望的认识和改造这种绝望国民性的愿望的。鲁迅的“苦于不能全忘却”就是这童年情结的内容,“这不能完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呐喊》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鲁迅童年情结的象征化表现。
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其中来自我们童年记忆、童年经验即童年情结的形式,恐怕比来自我们后来的人生经验要重要的多。艺术家就更是如此。艺术家认为是在写现实生活或另外的故事,但艺术家实际上还是在写他的童年。艺术家在写另外的故事的时候,他的童年情结作为一种反应外部世界的模式,就在无形中起着作用。“仁慈的自然赋予艺术家通过他创造的作品来表达其最隐秘的心理冲动的能力,甚至这些冲动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隐藏着的;这些作品强烈地影响着对艺术家完全陌生的人们,这些人自己意识不到情感的来源”(《弗洛伊德文集》第4卷,第482页)。《药》的素材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先驱者秋瑾悲烈牺牲的史实,一个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鲁迅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借鉴别国艺术方式的虚构。但《药》还有另一个“情感的来源”。无论是秋瑾的悲壮牺牲,还是《作粗活的人和不作粗活的人》的内容都不是《药》的艺术意义。《药》的艺术意义在于《药》本身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来源于鲁迅的童年情结,使鲁迅童年情结的象征性投射。决定鲁迅素材选择和想象虚构的是他的童年情结,他的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绝望和希望。创作《药》时的鲁迅已近四十岁,但他所表现的思想精神仍然与他几十年前的童年经历、童年创伤即童年情结有着因果关系。在《呐喊·自序》中鲁迅阐述他创作的缘起时说到的他的童年,这对我们理解它的创作是极其重要的,而鲁迅自己对进行文学创作的解释对理解他的作品就更为重要。在1933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一文中,鲁迅这样写道:“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是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意识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但这是
鲁迅梦的显象和显意,“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仍然来自鲁迅的潜意识情结。 他所表现的仍然受他童年情结支配,仍然是他童年的情感经验,他童年时期的对国民的绝望和希望。因为,鲁迅童年经验太深刻了,而童年经验这种被压抑的潜意识是处处要寻求表达的。“潜意识总是出于警觉状态,随时都在寻找表达的出路,一有机会就和来自意识的冲动结成同盟,并将自己的巨大强度传递给后者。??这些潜意识愿望永远是警觉的,并且可以说是永生不灭的”(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第689页)。“永生不灭”的情感是鲁迅《药》(当然还包括其他作品)的思想渊源。精神分析曾经深刻地揭示出作家情结对作品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新近的一次印象可以使甚至深层潜意识中与即使遥远的过去相联系的诸多因素发生震颤”(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鲁迅创作《药》最明显看到的是秋瑾献身取义的悲壮的史实,但我们看到,秋瑾献身取义仅仅是鲁迅这篇小说的隐线,也就是说,鲁迅的重心,不在于描写秋瑾的献身取义,而在于写出人们对秋瑾献身取义的态度。这就是秋瑾的事件 “刺激”了鲁迅情结的结果。秋瑾事件“刺激”鲁迅的童年情结,因而形成了《药》的特殊结构:表层结构是写人们不理解夏瑜(秋瑾的化身)献身取义,表现人们的愚昧麻木的,而深层结构则是表现自己心灵受严重伤害的童年情结的。那个人血馒头的情节就是由童年“看与被看”的情结意象生发出来的形式。梦的研究告诉我们,梦者的情感是由意象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童年情结也常常是转化为一种意象“记忆”。鲁迅童年严重心灵创伤——、从大家族王子到破落户的子弟的变化所体验到的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对王子的敬仰、恭维、逢迎、巴结,对破落户子弟的冷眼、蔑视、鄙薄、唾弃,从这两种变化中,鲁迅深深地体验到了人性的冷酷和恶劣。鲁迅的这种情感记忆是潜抑的,而鲁迅又慢慢地把这种潜抑的情感记忆即“童年情结”浓缩为“看与被看” 的意象、(还包括“吃与被吃”的意象),而这这种情结意象就成为制约鲁迅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思想模式。这就是为什么鲁迅的小说有一个“看与被看”(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页)、“吃与被吃”重要结构模式的原因。《药》是“看与被看”、“吃与被吃”情结意象规定的情节模式的又一种表现方式。在《药》的情节中隐藏着鲁迅的童年情结。
《药》中的象征,是鲁迅童年情结的一种比拟性的象征。所谓比拟象征,就是一种人物、一种意象、一种结构关系是童年情结的比拟。《药》的人物、意象和结构关系是鲁迅童年情结(包括反应方式)的比拟。“药”具有多重比拟性意义。其一是鲁迅对中国文化认识的象征。吃人血馒头治病的情结,比拟了“吃与被吃”的情结意象;人们对夏瑜牺牲的言论比拟了“看与被看”的情结意象;同时,也把中医的迷信、荒唐和害人比拟了中国文化的非人性,这其中无疑有鲁迅对父亲死于中医的童年深刻记忆;其二是鲁迅对中国人愚昧认识的象征。华老栓们虔诚地相信人血馒头能够救治痨病,把他童年时对人们冥顽不化、愚昧之极的思想表达的淋漓尽致;其三是夏瑜的血并没有唤醒沉睡不醒的人们,比拟了童年情结中,国民麻木冷酷、不可救药的绝望的思想认识。那些看客的形象和意象则是鲁迅童年情结中人性恶劣感受的象征;夏瑜与华老栓们的显在结构关系是启蒙者和不觉醒的民众,实则比拟了鲁迅童年情结中周围人蔑视(看)和自我心灵创伤(被看)关系的潜在结构。
乌鸦的象征更复杂一些,它既象征着夏瑜的这样的启蒙者的殉道精神,又比拟着鲁迅童年情结中被压抑的愿望,砸碎那不是人住的铁屋子,唤醒那些沉睡不醒的人们。这里有鲁迅的冷漠,有鲁迅的恨,对大众的失望甚者绝望,但更有鲁迅的热烈,鲁迅的决绝的殉道精神的投射。那乌鸦的飞去就是这种精神的象征:“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这是鲁迅不可为而为之精神的无意识象征,但这种象征是在鲁迅童年时期就种下了的思想萌芽。
《药》的人物、意象和结构是鲁迅潜意识意念的产物,还表现在《药》是鲁迅童年情结的释放。鲁迅童年情结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精神受伤害,对人性恶的怨毒情感无处宣泄的严重压抑。我们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一步分析鲁迅创作的思想动因。我们可以把鲁迅进行文学创作看作鲁迅的又一个梦,对这个梦即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鲁迅阐释说是意在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我以为,这是他“梦”的明确的创作目的即显意,而在潜意识中,他还有不明确的创作目的,那就是要充分地、强烈地、反复地宣泄童年情结中被侮篾、被歧视、被压抑的情感——描写出他童年时期对人的可恨记忆与经验,勾画出人的
卑琐和丑恶的嘴脸,揭示出人的愚昧和麻木的灵魂,使他们真真切切地、赤赤裸裸地、毫不遮掩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自己被压抑的潜意识得到释放,使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得到“疗救”。这是鲁迅的“梦”的隐意。能够作为这个分析的其他证明的是,鲁迅曾经要办《新生》刊物,但夭折了,后来他就长时间地投入到了沉闷的抄古碑帖的活动中去,这分明是鲁迅受压抑的精神无处宣泄的苦闷象征。
无论我们对鲁迅的《药》和其他作品作怎样的评价,都必须将鲁迅的精神溯源到他的童年情结中去。正是这种童年情结中的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绝望,才使得他是那样地描写了华老栓们无可救药的愚昧麻木,才使得他作品的风格是那样的冷峻、阴郁和凝重;但也正是童年情结中的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希望,才使得他是那样地描写了夏瑜的牺牲,才使得他的作品在冷峻、阴郁和凝重的总体风格中有了不和谐的亮色。说鲁迅的《药》和其他作品是鲁迅童年情结的象征性表现,并不贬损鲁迅作品的伟大。童年情结包含着本真的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受,童年的生命体验虽然是人最初的生命体验,但却是最深刻最敏锐最准确最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作家写作时常常被这种童年情结驱使着,因而才写出了人的最深刻的生命感受,才写出了社会的非人性。曹雪芹就是这样伟大的作家,鲁迅也是这样伟大的作家。
鲁迅作品中的童年梦
———《社戏》、《故乡》中“立人”思想的渗透
鲁迅的《呐喊》小说集里,许多篇章是以故乡生活为题材,且大部分篇章中,故乡是灰暗的、萧瑟的、充满死气,没有一丝朗照。独《故乡》和《社戏》中的童年故乡显得美丽、宁静、祥和、神异,充满了梦幻的色彩。本文试图通过对鲁迅童年诗化故乡的分析,剖析鲁迅暗含在诗化童年生活中的故乡情结和“立人”思想。
一、现实诱发下的诗性故乡
《故乡》和《社戏》两篇小说都写到了童年的故乡,而对童年故乡的回忆都源自现实生活的触发。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生活与他的作品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认为“凭着从幻想中所获得的见解,我们应该期待:一种强烈的现实体验唤起了作家对先前体验的记忆(通常属于童年期),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在作品中获得满足的愿望。作品自身展示为最近的诱发场合和旧时的记忆两种因素。”《故乡》中,“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丝活气。”这既是现实故乡的直接呈现,也是成年人荒凉心境的折射。《社戏》中,“我”所处城市环境的拥挤、促狭、嘈杂、压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都使我觉得“不适于生存”,使我毛骨悚然。两篇小说,一篇是现实乡村触发“我”对童年生活的诗性联想,一篇是现实城市生活触发“我”对童年乡村生活的诗性联想。《故乡》中,荒凉乡村诱发我对记忆中故乡的联想,然而现实乡村人的麻木、迷信、恣睢,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高墙”使我记忆中闪电般出现的诗意故乡跌入现实的无情生活中,所以“我”选择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表现出与现实故乡的决绝。从农村宗法文化的罗网中挣脱出来奔向现代都市的“我”并未找到理想的精神家园,很快就落入现代都市文化的困扰和夹击中。在《社戏》中“我”两次看戏都慨叹“不适于生存”,表现出生存的困惑、焦虑、无奈感。这种现实生活的“被抛状态”使“我”受本性中的恋土、归乡的情结的影响做起了“怀乡”的梦。诚如鲁迅所说:“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再没有青年时代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也应该包含做“怀乡”的梦吧。
二、故乡情结作用下的心灵乐土
鲁迅曾写到:“我有一时,曾经屡次记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思乡的蛊惑”、“旧来的意味”就是缠绕鲁迅的故乡情结。在心理学家看来,情结是一种心灵的结构核心,它具有激动情绪的作用,是一种心理能量,在某种情况下它表现的特别强烈。它属于个人无意识的内心,构成了个人内心生活的私人的、隐秘的部分,但是无论一个人的故乡情结埋藏有多深,一旦他实际的存在处于“被抛状态”,陷入心理的失衡,“乡”作为补偿价值就会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所以当现实生活带给鲁迅精神的困惑、存在的焦虑时,“乡”成了他放飞心灵的乐土。与“乡”紧密相连的童年生活也就具有了诗性的色彩。只有把鲁迅《故乡》、《社戏》中描写的儿童乡村生活理解成鲁迅童年梦想的诗化和诗化的童年的梦,才能理解鲁迅在总结自己创作农民题材小说时所说的话,“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
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鲁迅作品42_鲁迅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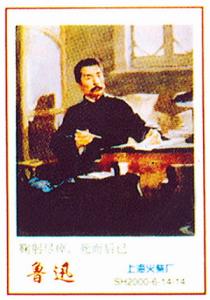
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和他们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亲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的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在鲁迅看来把劳苦大众看的和花鸟一样是一种不顾现实的“瞒和骗”,所以在《故乡》中,那闪电般苏生的童年故乡很快跌入现实的残酷生活里,李希凡认为《故乡》中那在记忆中闪电般苏生过来的美丽的“故乡”,是“一个都市儿童对边海农村的幻想的产物。”如果说《故乡》中的美丽的诗性的“故乡”从儿时的记忆中闪电般出现又陷入现实的灰暗背景里,那么《社戏》中的故乡则是在现实的灰暗背景里,记忆中的故乡被诗化了。
在加斯东·巴什拉看来“童年如同记忆的火种,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复萌”。当鲁迅在现实
中深感生存的不适时,童年的火种在他心中复萌了。“我们多么需要新开始的生命、精神焕发的心灵、开放的心智的教导啊!在生活的巨大灾难中,当人们是孩子的支柱时,他立即有了勇气。”当现实之苦折磨着鲁迅时,为寻找精神的支撑点,作为一个补偿,“乡”便成了心灵栖居之所。鲁迅要把他构筑的儿童乡村生活参与到与城市生活各现实乡村生活的比照中的,所以诗性的色彩浓烈。它是鲁迅童年的梦想和童年梦想的诗化的有机结合。它具有持久性,“童年时期的形象,孩子可能构想的形象,诗人告诉我们某个孩子曾构想的形象,对我们而言都是持久童年的显示。”所以在《故乡》中,当我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时,内心万分凄凉,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眼前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这是因为“我”所记得的故乡是诗化了的童年的梦,所以“故乡”才那么的神异: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英武的少年,景是诗化的景,人是神化的人,这是想象与记忆的复合,“想象与记忆在其原始心理中,呈现为不可分的复合体。若将两者与感知相联系,人们将难于作出分析。再次回忆起的过去并非单纯的曾感知过的过去。既然人在回忆,过去的梦想就已经成为形象价值。想象从一开始即对它乐于再见到的画面进行渲染。为深入记忆的档案库,必须超越事实重新找到价值准则。”超越事实找到价值准则必然美化形象,为回忆加上理想的光环。所以无论是“我”和少年闰土,还是“我”和双喜、阿发等小伙伴的生活都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鲁迅在一篇名《五猖会》的回忆散文中写到过看戏,他写父亲规定他必须背完鉴略才能去看戏,他不得不为这一规定而受煎熬,他借背鉴略抨击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活泼天性的压抑和摧残,现实童年生活的受压抑使他在幻梦中必然出现一个诗性的童年,这一诗性童年留存于他的记忆中,是所有不自由的孩子都可能幻想到的自由生活,所以小说里平桥村的人是不受礼法约束的,“我”也可免念“秩秩斯斯幽幽南山”,打了太公也没人想到“犯上”,可以掘蚯蚓、钓虾、放牛、看戏,偷豆却不被责罚。在加斯尔·巴什拉看来,作家在实际生活中进行的梦想,只有童年的梦想在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真实生活与想象生活之间摆动。回忆与想象的结合才使童年的生活充满光芒,故乡才显得那么明丽而迷人,那豆麦和水草的清香、朦胧的月色、起伏的连山、依稀的赵庄、歌吹和渔火都给入迷离飘忽之感,那回望中飘渺的如
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照着的戏台更显瑰丽,给人以梦幻般的色彩,这是经过沉思的梦想的童年。
三、灌注在诗性童年中的“立人”思想
“经过沉思和梦想的童年,在孤独的梦想深处经过沉思的童年,开始染上哲学诗的色调。”在《故乡》、《社戏》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思想的渗透,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立人”就是追求人格的平等,把人从中国传统人格依附的“三纲”中挣脱出来,从“礼”中挣脱出来。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鲁迅相信青年胜于老年,孩子胜于青年。他把希望寄托于将来的孩子,认为“孩子是可以敬服的”,“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他在《狂人日记》中大声疾呼:“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要寄希望于那些没有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所以他赋予少年闰土能干、青春英气的鲜明个性,并希望水生、洪儿能过“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在《社戏》中,作家同样把希望寄托在像阿发、双喜那样的未受封建文化毒害的孩子身上。这群孩子具有为鲁迅希望的鲜明的个性特色。第一,平等意识,他们无上下尊卑观念。“打了太公”也不会有人用封建等级观念去衡量这一行为,从而想到“犯上”。这与中年闰土和中年的我的关系是多么的不同。中年闰十那一声使我心寒的“老爷”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可悲的厚障壁”。第二,他们待人热情、聪明能干、无私心、有组织性。在人家为船的问题而苦闷时,双喜及时提醒人家八叔的大船回来了。在揣摩到外祖母不放心全是小孩时,聪明的双喜立刻抛出说服外祖母的三条理由:船大,迅哥儿规矩,人家识水性。他们很能干,驾起船来“飞一般”,“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窜”。他们表现的有组织性,行船时双喜拨前篙,阿发拨后篙,年幼的陪我坐在船中,
较大的陪我坐在船尾。第三,他们心细、率真、无私心又不乏狡黠。这在“偷豆”、煮豆、收拾残局的过程中表现出来。鲁迅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群鲜活亮丽率真的生命,或许鲁迅在这群天真、淳朴、聪明、能干的孩子身上看见了并寄托了全部的希望。所以作家说:“诚然!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
或许,鲁迅创作的意图正在于这群“弄潮的好手”,希望也正在于这群“弄潮的好手”。他把自己对故乡的情感和他的“立人”思想灌注于笔下的诗性故乡中,从诗性的童年故乡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对抗生存的痛苦感,焦虑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