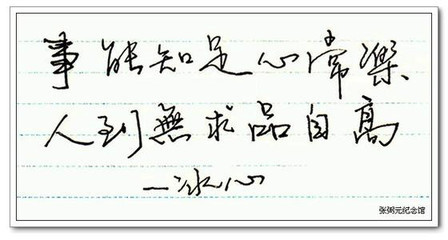对于诗歌创作,大家公认的看法,是葫芦头养家雀——一辈不如一辈了。近现代人中,还有作得不错的,比如苏曼殊、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等。
我记得郁达夫的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戏剧家洪深也有名句曰:大胆文章拼命酒,坎坷生活断肠诗。这都是可以放到“唐诗集”里的句子。清人写诗有所起色,流风所余,民国前二三十年还有些囤货。再往后,旧诗也就基本消停了。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名篇,然而后来妄图模仿毛诗的老干部体,把路走偏了,因为没有毛泽东的视野与襟怀,腹中又没有多少诗书,写出让人不忍卒读的打油诗,倒也不算奇怪。
所谓“老干体”是个新词,顾名思义,这类诗词如同曾经一些老干部的做人和讲话风格一样,观点陈腐、套话连篇,张口闭口尽是举国举世的宏大场面。其创作队伍却不限于某些老干部,许多年轻的诗词爱好者也钟情此类,俨然成为当今诗词创作的一大流派。去年有首馒头诗很是出了风头,还获了国家级大奖。其中两句曰: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其作者周啸天竟是位大学教授。
历史上乱写诗并且影响巨大的有两位,一位是打油诗的始作俑者张生;另一位就是《红楼梦》里的薛蟠。
大画家齐白石以诗自鸣,书斋号曰借山吟馆。他的老师、大学问家王闿运讥讽他为薛蟠体,令他大为愧馁,好像以后的斋号就去掉了吟字。
薛蟠的诗,其实生动得很。比如: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乌龟谐意老公窝囊;马猴极言男人之丑——女儿的悲愁,刻画得入木三分,又令人忍俊不禁。
薛蟠的另一个“大徒弟”是民国军阀张宗昌。鲁迅说他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银子,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他自嘲说:要问女人有几何,俺也不知多少个。昨天一孩喊俺爹,不知她娘是哪个。他向前清进士王寿彭学诗,老王掂了掂他的斤两,命他专攻薛蟠一路。
不曾想,他倒匠心独运,把诗写得风生水起,看得读者跌了一地的眼镜。他描绘自己的军旅生涯:“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他是这样笑话刘邦的:“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下雪很美,在他看来那就是筛石灰:“什么东西飞上天,东一堆来西一堆。莫非玉皇盖金殿,筛石灰呀筛石灰。”
作为一位军人,上述诗词其实写得很生动传神。虽然不够文雅,但景中有情,既可娱人,又可娱己,不失为野诗中的一种套路。我甚至认为他的《大明湖》是一首好诗:“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诗中的蛤蟆,写得活灵活现,充满动感。
宋人杨万里乃大诗人,他就曾描绘八哥“仔细看来还有须”。这和“一戳一蹦跶”甚有异曲同工之妙。
杨万里是文官,张将军是武官,禀赋和修养,天壤之别,但有一点相通:童心。今人写不出好诗,恐怕是童心丢失了的缘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