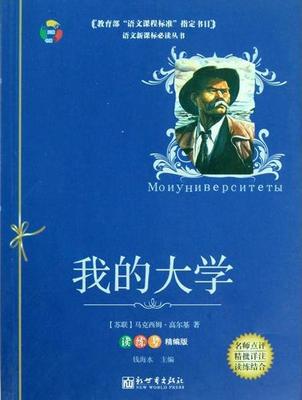上一个世纪的初期,现代大学在中国发轫开端,但是同时几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达到了一个灿烂的顶颠,人才辈出,大师涌现,以至于整个世纪当中的人文建树如果不客气地总结的话,多半就是在那段时间形成的。
但凡是事物在新生阶段,气象最新,气势也最为宏大,创始人物的高山仰止也尤其显得不可逾越,这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的一个通病。中国的大学当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据京师要地,是思潮传播中心,尤为瞩目。而奠定这两所大学的气量和风格的,在北京大学是蔡元培,在清华大学,则就是《中国的大学》的作者梅贻琦。
蔡元培是一位博学君子,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使北京大学成为国家学问之渊薮,思想潮流的源泉,以至于运动的发起者。但是梅贻琦却不同,和蔡元培的“博学、审问”相比,梅贻琦则是“笃行”的代表。笃行做事,声名不闻,但是日渐月累,最终使得清华大学并肩于其他的世界学术名校。如果要比较蔡元培和梅贻琦的更大不同,则在于举世皆知道蔡元培的办学思想,但是却没有能列举他的治校措施,至于梅贻琦,则至今有人能列举他的治校措施,却不能明确说出他的办学思想,盖已经将办校思想化用到治校措施当中了。
要办好一所学校,放眼于学校的建设和学术的成果,而不是将学校作为自己在学界的晋升和声名的升降机,是没有沉稳的耐心不行的,没有长久的坚持不行的,同样没有基于以上两点的基础被学校所信任也是不行的。梅贻琦很好地秉承了以上的原则。他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要论为清华大学服务,则更早在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的教职——到1949年前往台湾,再到1962年在台湾去世,几乎终其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
这足以能够说明梅贻琦的耐心笃行。除此之外,他的耐心笃行还表现在其他的若干方面。学生着急于救国兴亡,梅贻琦解释说:即使救国吧,也第一要有健康的体魄,第二要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因为救国并不只在战场上面,也不完全需要一群莽夫。他的儿子要去参加军事翻译,梅贻琦并不支持,说道:你现在才是大一的学生,也许到了大二才可以去。当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完全遵守父训。国民党的军警捜査大学校园,被激怒的学生围攻教务长潘光旦,梅贻琦又出来解围说:这也许并不好,如果事情闹得更大,学校可能会停课,这从长久上考虑,是不利于学校的发展的,但是可以搪塞,自己就是把往年的学生名单交给军警了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守旧和对于时事的回避,因为很容易愤怒的学生常常会驱赶他们的校长,在梅贻琦之前就发生了两三回,但是梅贻琦在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七年间,清华学生的口号是“拥护校长”。对此梅贻琦的解释是:驱赶校长就是“倒某人”,看来没有人愿意“倒霉(倒梅)”。梅贻琦的回答往往是狡猾而儒雅,也同样有耐心。
以上的很多次事并不只发生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其中有一些事发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经历尤其是梅贻琦的耐心笃行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校务委员会当中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因为要到重庆国民政府任职,在校的时间是很短的,西南联大的校务几乎就由梅贻琦一人主持。但是就是这样,在战事的昆明一隅,在低矮的铁皮房子当中,在几乎是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下,但是偏偏就是这个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一流学者和3名诺贝奖获得者,比起世界上任何的著名学府也不遑多让,甚至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学府就在中国。
这些事如果没有被记载,那么这些事下面的治学治校的思想则都被记载在梅贻琦的《中国的大学》一书当中。其实梅贻琦的著述极少,要想在今天看到梅贻琦的做事的方法和治校的方针,则只有《中国的大学》这一本书。而且即使在这一本书当中,他的叙述方法也极其简单,共分为“大学之精神”“清华之为清华”“西南联大的精神家园”和“工业化的前途和青年的使命”四编。
但是尽管如此,全书四编当中分别提出的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之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这传统就是北京大学的‘自由’,清华大学的‘民主’、和南开大学的‘活泼’”以及 “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都极有指导意义。
但是并不仅此,除这些鞭辟入里的指导思想之外,梅贻琦的这部著作当中,又非常着重地强调着对于大学生德育、体育、美育,以及对于清华大学在若干时期的学校机构的演变和发展,这种事必躬亲和应对的方法,却是一座真正学府的进步和学生的成长的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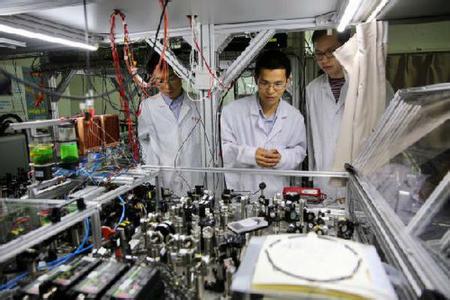
但是梅贻琦却毫不居功。在他所倡导的治校思想当中,首先将使命责任的概念推还给了“蔡孑民先生”,而至于治校的具体办法,则发展了教授治校的一个民主制度,正如朱自清在《代序》中所写的那样:“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和清华关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爱护清华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难得的是他知道怎样爱护清华;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当然更多的梅贻琦的治校和治学还是要从他的著作当中阅读才知道的,既然没有这样的幸运能够在他做校长的清华大学读书或者任事。之所以说他的著作是需要所有的大学学生和教授阅读的,就在于从他的著作当中,无论是学生或者教授,都能认知作为学生或者教授的责任,而不是急功近利。
其实和梅贻琦的耐心、专注、笃行相比较,在今天,急功近利是损害中国大学精神的最大坏处。且不说教授的急功和学生的近利,早在八九十年前梅贻琦就有“大师”和“大厦”之辩,但是八九十年后,中国的大学当中还是只见大厦不见大师,急功近利之故也。正如中国过去的君主,只兴土木,不修德政。大厦是期日之功,而大师则是需要期年之力。如果能够去浮躁,多耐心,想必也能有所矫正。
不过大厦已成,大师的培养和出现为之未远,也未可知。以史为鉴,在怀疑和危机过后,中国的大学必定从榛莽和荒芜当中重新崛起,这就是《中国的大学》的出版价值和意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