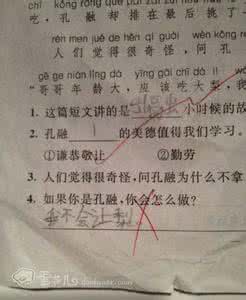长期以来,几乎所有教科书、辞典、百科全书中都讲:孔子打破官学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之风。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化人士,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一定要说是因为有了孔子才打破官学垄断、才有了私人教育,这恐怕不是历史事实。
我国自古就有极为重视教育的传统,在孔子之前,教育之普及、文化水平之
高恐怕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礼记?学记》中讲:“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孟子也讲:“设为库序以教民,库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滕文公上》)我们都熟悉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子产比孔子约长三十岁,是同一时期人,可见孔子时代“乡校”是很普及的。“乡”的规模,有解释为一万二千五百家,有解释为三千六百家。如果连“乡”都普遍有“校”的话,那就很难说是“官学垄断”了。
陈来教授在《古今原儒说及其研究之反省》一文中,对“儒”的源流及孔子之前的教育状况论之甚详,文中也讲:“总合所有上述职官的功能所构成的西周行政教化传统就是儒家思想的来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就是孔子以前就有的‘儒教’的一部分。‘师德’既然是致仕贤者教授乡里子弟的人,则这种职业教化就亦不待王官失守而已有之。”
孔子自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论语?为政》),又自称“吾少也贱”(《论语?子罕》)。既然“少也贱”的孔子都可以受到良好教育,那就很难说“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是自孔子始。
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又讲:“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是乐于、善于向别人学习的。《庄子》、《礼记》、《史记》中均载孔子问礼于老子;《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中讲“孔子学於老聃、孟苏、夔靖叔”。那么,老子等人属于官学呢还是私学呢?
孔子拥有众多弟子,这的确是很突出的。但任何现象都不会是突然出现、孤立存在的。如果说少正卯聚徒讲学、与孔子争夺弟子事属虚妄的话,那郑国的邓析实有其人,只比孔子年轻几岁,自编“竹刑”,还帮人打官司。据《吕氏春秋》:“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弟子比孔子可能还要多些。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孔子时代乃至孔子之前,“官学”与“私学”的界限很可能就并不明显。我们甚至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对“国人”来说,也许原本就没有官学与私学的区别,因为在理论上每个“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当然,这一假设能否成立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下面就孔子教育思想的优缺点谈一些个人看法。
孔子教育思想的缺点:
1、忽视科学
忽视科学这点是中外不少人对孔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孔子那个时代,中国自然科学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和积累,主要有:
在天文学方面,如李约瑟先生所讲:“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而且中国天文学自始就使用赤道坐标系,不同于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和阿拉伯的地平系统,而现代天文学采用的是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纪录是《尚书?胤征》中的记载,发生在公元前1970年或前2019年。世界上第一次新星爆发纪录也是中国殷商甲骨卜辞中的“新大星并火”,约为公元前1300年。
在数学方面,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有:“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东汉郑玄在注疏引郑众所言:“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这同后来的《九章算术》差不多少。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西周时即有“九数”的教学内容是合乎情理的,当然也许不会有《九章算术》中的内容那样高深。但只要有这些概念和最粗浅的运算技巧,在当时世界上也明显居领先地位。
《墨子》一书中述及的数学、几何、力学、声学、光学、机械制造等方面的知识,显然至少不次于晚墨子近两个世纪的古希腊阿基米德。墨子虽然比孔子晚了近一个世纪,而且《墨子》一书中很多内容也为墨子的弟子们所写,但同样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孔子时代及以前,数学和物理知识就应该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了。
《周礼?冬官考工记》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产生于春秋末与战国初,与墨子活动时间大体相当。其中所记录的丰富手工业技术与《墨子》相互印证,反映了那一时期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同样从任何知识所需要的积累、发展的时间过程判断,孔子时代及以前,工艺技术水平会是相当高的。
但在《论语》和其它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无论是数学物理还是机械工艺,均无丝毫反映。如果考虑到西周教学中本来有重数的传统,我们只能说孔子未能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他之前的文化知识。
有人曾为孔子辩护说:《周礼》中讲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是“小学”,是青少年们的学习内容;而孔子教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是“大学”,是成年人学的。但墨子等研究数理工艺的人士就不是成年人了吗?
也有人会为孔子辩护说,在诸子作品中除了《墨子》和《管子》,其他不也都没涉及科学吗?还有人会为孔子辩护:古希腊与孔子地位相当的苏格拉底不也只谈社会伦理、不谈科学宇宙吗?
的确,依照“无求备于一夫”的古训,孔子忽视科学最多只能说缺憾、而不能说是过错。如果将孔子视为与其他诸子和古希腊哲人一样的杰出文化人士的话,孔子对知识有个人偏好是正常、无害的。但后来孔子被君主们尊为“至圣先师”,他的话被认为句句是真理、是社会思想的准则,这样,他的忽视科学这一个人偏好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很不利、甚至可以说是危害了。
2、 缺乏尚武精神
如果说忽视科学是先秦多数士人之通病的话,那缺乏尚武精神恐怕只有孔孟、杨朱等少数学派了。以军事见长的孙子等人就不用说了,主张耕战强国的商韩吴起等人也不必说了,就是《墨子》、《管子》中也有相当篇幅、很高明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连主张虚静无为的《老子》中,虽然多有反战言论,但也讲独特的用兵之道,如:“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六十八章》)等。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句著名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有国家以来,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战争。一个国家民族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战争中获胜,因此古代优秀的政治家往往也是出色的军事家,贵族以勇武善战为荣,百姓也普遍强健能战。
孔子和鲁儒们依自己的爱好和愿望,只把周公说成是制礼作乐的先驱,从不提周公也是位军事家,不仅参与了武王伐纣,而且后来还亲率大军东征,讨平叛乱。
孔子无疑是位礼仪方面的专家,但对军事没有兴趣。《论语?卫灵公》中讲: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问孔子有关打仗的事,孔子答道:“礼仪方面的事我学过,打仗的事我没学过。”并且第二天就离开卫国了。(“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有人曾为孔子辩护说:孔子是不满卫灵公内政不修,因此不同他讨论军事。但在有关孔子比较可靠的言行记录中,也未见他同任何人讨论过军事。
我们都知道,上古时代的“五礼”中是有军礼的,但现存《仪礼》中只有四礼,没有军礼。章太炎在《经学略说》一文中这样讲:“五礼著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
《逸周书》普遍被认为是孔子选了一百篇古代文献集成《尚书》后剩下的周代文献。《逸周书》中有多篇军事文献,如《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武顺》、《武穆》、《武纪》等。但在经孔子选编的《尚书》中,迄今还未发现有军事文献。
前述《周礼》中所讲周代青少年学的“六艺”中有“五射”。汉代郑玄注引郑众曰:“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后来唐代贾公彦作了进一步注疏:白矢,即箭不仅射中、而且要射穿靶子,因此才见到白色箭头,表明发矢准确有力;参连,即连续放箭,有如连珠;剡注,疏曰:“剡注者,谓羽头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疏曰:“襄尺者,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君一尺而退”,襄,让也;井仪,连发四矢皆中靶,并成井字状。显然,这“五射”中除“襄尺”外都是要求很高的实战技术。
孔子也讲“射”:“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又讲:“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这里的“皮”是指箭靶子。孔子讲射箭不一定要射穿靶子,因为人的力气大小不同;而且射箭时“无所争”,要“揖让”,射完了再饮杯酒。显然,孔子所讲的“射”并不是实战技术,而是一种礼仪,类于《仪礼》中的“乡射礼”或“大射仪”,是上不得阵的。
也许有人会替孔子争辩说,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学生厓有(冉求)说他的军事才能“学之于孔子”。但这很可能是做学生的为了能使孔子回到鲁国而讲的谦辞,因为在有关孔子的言行记录中,我们实在看不出孔子对军事有兴趣、有研究。即使退一步讲,孔子在私下里说不定对军事也许确有研究,但流传下来的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孔学思想仍然是缺乏尚武精神。
以前讲过,我们中国的道德观念本来一直是以“德”为中心的,而孔子将以“德”为中心转变为以“仁”为中心。这种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带来了至少两个相当负面的作用:一是注重尊尊亲亲,使法制不彰;二是弱化了尚武精神,使人变得温顺柔弱。
客观地讲,孔子倒也还并不是完全回避、反对战争,而是强调“仁”和“义”、不讲战争自身规律艺术。(见《论语》的《述而》、《子路》、《卫灵公》、《季氏》等篇中有关内容和《左传》的“哀公十一年”、“哀公十四年”及《史记?孔子世家》等。)孟子进一步发展或者说进一步扭曲了孔子这一思想:“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孟子?尽心下》)然而把“善为战”与“仁”对立起来、不讲战争自身规律艺术、只讲“好仁”,果能无敌于天下吗?韩非在《五蠹》中曾举过徐偃王的例子:“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后来曹操在注《孙子兵法》序言中也举了徐偃王的例子,并总结道:“恃武者灭,恃文者亡。”
古代汉族人的体质是非常强健的。荀子在《议兵》篇中曾举例道:“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同古希腊武士轻装跑马拉松而累死的例子可做对照(当然这位希腊武士也有可能原本心脏就不大好)。《汉书》中载西汉名将陈汤对汉成帝讲:“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因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可见即使除去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后,汉兵的体能也至少决不次于游牧民族。
毛泽东年轻时曾写过《体育之研究》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讲:“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这篇文章写于1917年,上距清室覆亡不远。反映出经长期孔孟程朱思想的熏陶后,原本可以“以一当五”的强健民族已是武风不振、体质日趋轻细,并且还被送了个外号:“东亚病夫”。
顺便提及:任一时代的审美观念都必然是当时居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反映。汉代女子以颀长为美,唐代女子以丰满为美,明清女子则以纤弱小脚为美。明清时代这种审美观念肯定反映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孔孟四书、程朱理学中有相当程度的衰弱、病态、压抑、扭曲色彩。
3、缺乏务实精神
如上文所讲,孔子不讲科学、不讲军事;以前也曾述及,孔子不讲经济、不讲法制。那么孔子讲什么呢?只讲两类内容:一类是《诗》、《书》、《春秋》等“文”类;一类是礼仪、道德、伦理等“礼”类。因为孔子认为有这两类东西来维护君主统治、防止犯上作乱就已经够了,这就是他的那句名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这句话在《雍也》和《颜渊》中重复出现,可见这是孔子本人所注重的观念。
孔子还有另一句名言:“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器”是器具,孔子这句话是说:理想的君子是不像器具那样,具有某方面用途。
那么,孔子是不是说“君子”应该有多方面用途、有多方面能力呢?不是。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坐而论道、不做任何具体事。孔子并不欣赏有多方面实际才能的人。
孔子诸弟子中最有才能的要说是子贡了:政治上“常相鲁、卫”,外交上出使一次使“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学术上被孔子称为“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并且经商能力突出,是位商业巨子,因此当时有“子贡贤于仲尼”(《论语?子张》)的说法。而且子贡对孔子的贡献也可以说最大,孔子厄于陈蔡时,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史记?孔子世家》);由于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因此“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
但孔子并不很欣赏子贡。他曾当面对子贡说:“汝器也”(《论语?公冶长》),联系他所讲的“君子不器”,“汝器也”并不是一句好话。(不过当子贡进一步问“何器也?”他答曰:“琏瑚也。”还是肯定子贡是庙堂之器。)另一次他还故意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子贡自然回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进一步肯定:“你的确不如颜回。我和你都不如他。”(“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同上》)
孔子最看重、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颜回的确聪明好学,上文中讲子贡曾称赞颜回“闻一也知十”;颜回去世后,孔子甚至认为再没有好学的人了:“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他的心地也很善良,孔子称赞他:“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他的性格比较温顺,孔子曾讲:“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甚至认为他过于温顺了:“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论语?先进》)他的修养也很好,孔子说他:“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上》)但颜回做过什么具体事情吗?什么也没做过,连谋生也是个问题。(“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
孔子自己只注重“文”和“礼”,不喜欢实用学问,因此也最欣赏颜回这种没表现过实际能力,但好学、在为人上温顺谦恭的人。
孔子和颜回如果只是做人文和伦理方面的学者或朝廷供养的博士,那会是很出色的。但一个国家如果只讲人文和伦理,不讲科学、不讲军事、不讲经济、不讲法制、不注重实际做事的人,那能好的了吗?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将孔学立为思想正统后,直到清末,除乱世外,二千年间中国的科学、军事、经济、法制等各方面的进步似乎与孔学受尊崇程度成反比例起伏,一些方面比起先秦来甚至可以说退化了。科举制度自然有其平等的一面,经科举选拔出的人中也有一些有才干的人;但由于科考内容的局限和在不同时期的侧重,也选拔出了不少只空谈道义而缺乏实际能力的人。
明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中国的某些弊病要看得更清楚:“中国所熟习的惟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利玛窦中国札记》)
4、二分法思维,缺乏包容度
二分法思维是指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我即敌、否认或忽视中间状态存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缺乏包容度。
孔子二分法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的“君子”、“小人”之辨。《论语》中提及“君子”的有一百零几处,提及“小人”的有24处,其中将“小人”和“君子”作鲜明对照的据我数为19次。也就是说,孔子在提到“小人”时,几乎都是用来与“君子”作对照的。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等等。
那么,除了“君子”和“小人”外,还有没有第三类人、第四类人呢?在孔子的言论中没有发现。
上个世纪前半期的著名剧作家、导演洪深曾编译、导演了名剧《少奶奶的扇子》,其中有这样一段台词:“我想世界上的人,也不能就分做两群:说这群是好,那群是坏;这群君子,那群小人。”洪深(或原作者英国王尔德)的这一见解应该说比孔子要更正确一些。
在前一篇有关我国古代法制的文章中曾述及,我国上古传统中一直是主张“既要德政也要法治”、“德政和法治相辅相成”;而孔子则把命题转换为“德政好还是法治好”、“要德政还是要法治”。孔子的这一命题转换也反映了他二分法思维的特点,缺乏兼容并包的观念和胸怀。
孔子是很爱好音乐、很懂音乐的。他曾在齐国听到“韶”乐,之后三个月仍沉浸在该乐曲中,以至吃肉都觉不出滋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他也曾修正了“雅”乐和“颂”乐中的不正确之处(“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但他讨厌郑国音乐,主张排斥、禁绝郑国音乐(“放郑声”),因为“郑声淫”(《卫灵公》)。“淫”是过分、过度的意思。人们解释说郑国的音乐节奏比较强烈,容易激动人心,不符合孔子中正平和的音乐标准。
孔子喜欢韶乐和雅颂,这无可非议,但主张“放郑声”就缺乏包容度了。这就如同不能因为喜欢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古典音乐就主张排斥、禁绝爵士乐和摇滚乐一样。
在另一处,孔子又重复了讨厌、憎恨“郑声”,并加进了新的内容:“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阳货》)据载古时有些人认为朱色即大红色是本色、正色,而紫色是由红色参杂其它颜色而成,是杂色。孔子看来是认为紫色不纯并夺走了一些人对红色的喜好,因此讨厌、憎恨紫色。其实红色固然好看,紫色也很漂亮,五彩缤纷不是更好吗?
如果说对颜色、音乐的好恶还无关宏旨的话,那么“恶利口之覆家邦者”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了。什么是“利口”、怎样算“覆家邦”,这都是很难在法律上作出定义的,这就为“因言治罪”开启了方便之门。《荀子》、《淮南子》、《史记?孔子世家》等古籍中载孔子诛少正卯,所举的五项罪状:“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均为想当然的揣度和以言治罪,与“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自朱熹起,多人质疑、否定孔子诛少正卯的真实性。但将“恶利口之覆家邦者”与他所讲的“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联系在一起看,孔子执政搞“以言治罪”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无论如何,孔子的这些观念言论与周公的对百姓抱怨指责“不敢含怒”、要“永念厥辟”“宽绰厥心”、《国语》中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子产的“不毁乡校”相较,胸襟气度之高下立判。(《荀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也载子产诛邓析,非是。子产前522年去世,而邓析前501年被诛。当以《左传?定公九年》中记载为准:“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驷歂是继子产和太叔之后的郑国执政者。)
有人会为孔子辩护说:孔子不是也肯定子产的不毁乡校吗?还有人会举例说:孔子不是也曾对鲁定公讲“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会“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吗?这里用得上《尚书?秦誓》中的一句话:“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从孔子的“君子”“小人”之辨和他恶紫色、恶郑声、恶利口来看,要让他自己执政而“不毁乡校”恐怕不容易。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思想文化繁荣融合,也有过几次思想文化专制禁锢。
西周时代出现了一次思想文化繁荣融合,从《尚书》、《逸周书》、《诗经》中看,不仅包容了自古以来和当时各地的思想文化,连敌国殷商的优秀思想文化也兼收并蓄。
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文化极大繁荣时期,战国末期以《管子》、《吕氏春秋》为代表出现了兼采百家之长的融合潮流。(这一兼采百家之长的融合潮流后来被一些儒生贬称为“杂家”。)从《管子》中可以明显看出《逸周书》的影响;从《吕氏春秋》以节气时令为结构的风格中,可以明显看出《逸周书》、《周礼》等古籍的影响。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战国末期出现的百家融合潮流是在西周思想文化框架中形成的。但这一百家融合潮流被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思想文化专制禁锢所打断。
西汉初期以道家形上学为框架,又接续了战国末期兼采百家之长的融合潮流,这从司马迁父子的论述和《淮南子》中可以明显看出。但被汉武帝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思想文化专制禁锢再次打断。
唐宋时代今古文经学并尊,政治社会风气相对宽容,经济和思想文化也随之相对繁荣。但明初清代被四书八股、程朱理学的思想文化又一次专制禁锢起来。
人们会说,思想文化专制禁锢是统治者搞的,不能把账算在思想家身上。但为什么不是其他思想而是商韩思想和孔学思想成为了统治者专制禁锢的思想工具呢?
5、缺乏平民情怀
孔子是很好学、很有学问的人。但有些知识精英高傲、冷漠、轻蔑普通百姓,孔子也有这个毛病。以前曾讨论过,孔子之前的上古传统中有明确的“忠于民”的思想,孔子之后的《管子》《荀子》中也能见到“忠于民”的言论。孔子从未有“忠于民”的言论或思想,而是冷漠、轻蔑地讲:“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人们都熟知这个故事:孔子的弟子樊迟(樊须)向孔子请教怎样种庄稼,孔子答道:“吾不如老农。”又向孔子请教怎样种菜,孔子答:“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因为孔子认为读书人应该学习怎样管理百姓,而不用学习种地种菜这些“小人”们干的事。(《论语?子路》)孔子这番话倒也不是全无道理,但语气中的轻蔑感可以说对后来中国人的行为影响是很大的。
孔子对平民百姓的蔑视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有关“小人”的观念上。“小人”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尚书?大禹谟》中:“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这个“小人”是为人低劣的意思,但《大禹谟》为古文尚书,这句话是否可靠还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当可靠的“小人”一词最早出处是《商书?盘庚上》中的“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这里的“小人”明显是“小民”“百姓”的意思。周公的言论中有九个“小人”,全都是“小民”“百姓”的含义,如“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康诰》)、“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小人怨汝詈汝”(《无逸》)等等,均无丝毫轻蔑的意思。
到了春秋时代,从《左传》中看,“小人”普遍用于自称的谦辞,如《隐公元年》(孔子出生前约170年)有“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再如《昭公三年》(孔子13岁时)中,晏婴就在齐景公面前多次自称“小人”。春秋时代,“君子”“小人”也用来分指贵族和平民,并不带什么贬义,如《宣公十二年》(孔子出生前约50年)有“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昭公六年》(孔子16岁时)有“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但那时“小人”也在具贬义的含义上使用,如《昭公八年》(孔子18岁时)有“小人之言,僣而无征,故怨咎及之。”再如《哀公十一年》(孔子68岁时)有“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
《论语》一书中计有24个“小人”,据笔者分析,其中有三个侧重指“小民”、“平民”,没有太大的贬义,这三句话是:“言必信,行必果,胫胫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其余21句都带有明显贬义,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等等。有人会为孔子辩护说:孔子这里只是讲“卑劣之人”而没有指“小民”,就是说,孔子并不是把“小民”和“卑劣”混为一谈。但在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等句子中,如果“小人”不是指“小民”,就会成为同义反复、没有意义;或者我们再退一步说:至少在一部分言论中,孔子是把“小民”和“卑劣”视为一回事。
周公虽然出身于王室、贵族,但颇具平民情怀。他曾对成王讲:“要先知道百姓耕作收获的艰难,这样在身处安逸时,也会知道百姓的苦衷。”(“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又讲:“一些王孙贵族生于安逸,不知耕作收获的艰难,不知百姓的劳苦,只知道享乐。”(“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无逸》)他还有一些名言,如:“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无逸》)等等。
我国上古时代一直有关心平民疾苦、同情弱势群体的传统。《虞书?大禹谟》中即有“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夏书?五子之歌》中有“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意思是:大禹先祖讲,他视天下普通男女同他自己一样)。《商书?汤诰》中有“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商书?太甲下》中有“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周初除周公外,召公也讲:“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周书?召诰》)。《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瘼)”,等等。
孔子的确有“惠民”思想(见下文),但在孔子的言论中,找不到这类同情弱势群体、具平民情怀的例子。
孔子在权贵面前一直是很谦恭甚至谦卑的。《论语?子罕》中讲: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穿官服的人和盲人时,虽然他们年轻,也一定会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定会快步走过。(“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见到穿丧服的人站起来,是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对盲人尊重可能是古代人们相信盲人有特异能力,如《国语》中有“吾非瞽史,安知天道?”;但见到穿官服的人,虽然年轻也一定站起来,是否有点过?
孔子对人说话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等级分明的。《论语?乡党》中讲:孔子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理直气壮、能言善辩,与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温良谦恭(“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唁唁如也。”)
孔子在国君面前就更谦卑了。据《论语?乡党》,如果国君在场,孔子总是恭敬而心中不安的样子,谨慎小心(“君在,椒错如也,与与如也”)。进入朝廷之门,总是弓腰曲背,好像没有容身之地的样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在国君面前,说话总象中气不足的样子(“其言似不足者”),连大气也不敢喘(“屏气似不息者”)。
对孔子的这些举止,当时肯定也有人看不惯,因为孔子曾为自己辩护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
但孔子对非权贵者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有句名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其中的“如”与“不如”显然以是否能成为权贵为标准:年轻人前途远大,怎么会知道他不能成大人物呢?但到了四五十岁还功不成名不就,也就没什么指望了。这倒也是实话,但讲“畏”与“不足畏”却让人觉得有点没必要:无论是“畏大人”还是“民斯为下”都无助于形成健全的心理和思维。
《论语?宪问》中有这样一段:“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这个人均解释为孔子故旧;夷,踞坐,伸开两条腿坐,表示傲慢;俟,待也。这段话意思是说:原壤见孔子来了,还是傲慢地伸开两条腿坐着。孔子就骂他:你年轻时就不知恭顺友爱,长大了也没什么出息,现在老了还不快点儿死,真是个祸害。并用手杖敲他的小腿。
有人解释说这是孔子恨他傲慢无礼,也有人解释说这是孔子跟旧人开玩笑。但这同见了穿官服的人即使年轻也要站起来、“与上大夫言,唁唁如也”、在国君面前“屏气似不息者”,反差是否大了点儿?周公多次讲“不敢侮鳏寡”(《康诰》、《无逸》),《诗经?大雅?荡之什?烝民》中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孔子熟读《尚书》《诗经》,对这些话可能不感兴趣。
有些尊孔者曾质问说:基督教在中世纪也禁锢封闭,经过改造不也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吗?为什么对孔学就这么苛刻?但孔学与基督教在相当关键、本质的一点上不可比,那就是原初的基督教有相当浓厚的注重平等的平民色彩,而孔子思想中没有。
耶稣时的基督教基本上是平民运动、甚至可以说是草根运动,教徒不分种族和社会阶层,连奴隶受洗后也可以即时被接纳为弟兄。虽然中世纪基督教会官方化,但其原初的平等色彩无法根本清除。经过宗教改革运动后,很快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他们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罪人”,无论是总统、富翁还是蓝领工人、失业者,在教堂里都只能互称兄弟姐妹。
伊斯兰教也是这样,他们也有一个说法:“进了清真寺,都是穆斯林”,无论国王贵族还是平头百姓,在清真寺内的待遇完全一样。见报道,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国王或政府首脑向民众讲话时,为了加强说服力,往往说:我不是以国王(或首脑)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穆斯林的身份对你们讲。
释迦牟尼时代的佛教是极为平等的团体,不仅出身穷富贵贱在团体内完全平等,就连出身不同种姓的人在团体内也完全平等,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对所有人的态度都一样:见了乞丐合掌致意,见了国王也是合掌致意。后来有些僧人和庙宇也沾染了一些等级、势利等世俗习气,但至少在理论上是主张“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的。
这种宗教内的平等感对参与者来说是一种双向调节:对富贵权势者来说,这种平等感可以去除虚骄之气;对穷苦贫贱者来说,这种平等感可以增强自尊自信。所以这些宗教在仍然不平等的世俗社会中,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孔学则不仅没有这种平等思想,反而是在原本相对平等的民本思想中加进了或强化了尊君抑民、尊卑等级、贵贱不愆等观念,加进了或强化了对权势者谦卑、对普通百姓轻蔑的礼数。因此,虽然从整体上讲,孔学应该说还是要优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但他礼教这部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没法继承,也无法改造,只能扬弃。
近代康有为等人在建立孔教时,看来也意识到了孔学在现代社会的这一致命缺陷,因此不顾二千余年以来的一贯解释,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重新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使孔子变成具民主思想的宗师。如果孔子原本尊卑等级观念不是那样强烈、明显,或如果再有一些哪怕模棱两可的话可以曲解,或再有几句可以这样重新标点的话来凑数,说不定还真能把孔子变成民主的形象。但可惜没有了。所以康的这一新解即使宽容地讲,也只能说是“孤证难立”。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中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具平民情怀、同情弱势群体的思想,大量存在于《尚书》、《诗经》等上古典籍中。我国传统中能够提供平等感的信仰,是历史最悠久、为各思想流派所共同遵奉的“敬天祭祖”活动:在上天面前,无论穷富贵贱,每个人都是上天的子民;在祖宗面前,无论穷富贵贱,每个人都是祖宗的子孙。有关“敬天祭祖”这一信仰,我们另文再讨论。
孔子教育思想的优点:
1. 严谨的治学态度
孔子无疑是位终身好学不倦的学者。《论语》全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他主张时常“温故而知新”(《为政》),强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并且在好学求知中获得极大满足:“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他毕生追求理想中的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人》)他也不仅是单纯记忆型的博学者,而且是思索型的思想家:“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他也有着坦诚、实事求是的学者素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
他也是很虚心的人:“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并自谦地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正因为他的好学和天资,使他成为了解释“六艺”的权威。尽管他的很多解释并不符合原本的西周时代思想,而是从礼教观念出发进行了相当一些取舍和修正,但还是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如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讲:“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至于后来被圣化、被作为束缚禁锢人们的思想工具,那责任倒也不全在孔子本人。
但孔子的治学方法也不能说是没有缺陷或局限。如人们熟知的,他的治学准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就是说,他致力于叙述传承已有的知识文化、而不创造什么新的,(当然在传承中不会没有自己的取舍和见解,)相信并爱好古代的事物。他的这一治学准则对研究与“史”有关的科目来说是比较适合的,但不适于研究现实问题,更不利于发明创新。他的这一治学准则作为个人偏好来说,是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后来被奉为“万世师表”,他的这一偏好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很不利了。
2. 启发式教学方法
孔子也是很喜欢教学的。如上面所引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虽然他自谦地说“何有于我哉”,但正说明“教”与“学”都是他内心的愿望。
《论语》中直接有关教学方法的论述并不多,但很有价值。
他最经典的一段教学名言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意思是:学生不到百般思索、发愤非想弄清楚的时候,不要启发他;不到心里有些明白、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不要开导他。如果告诉他房间的一个角,他不能推论出其余三个角来,就不要再告诉他了(要让他自己去思考)。这种结合并注重发挥学生本人主动性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很高明的。
但另一件事值得我们讨论讨论:孔子同乡有个少年,有天来给孔子捎个信。有人就问孔子:这孩子挺求上进的,是不是?孔子答道:我曾看见他坐在成年人的位子上,又曾看见他与先生并肩走。我看他不是求上进的孩子,而是个急于求成的人。(“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
春秋时的鲁国以好礼、多礼而著称,孔子又是鲁文化土壤产出的礼学大师。孔子看人主要不是看他是否聪明好学,更讨厌活泼勇敢,而是格外注重他一举一动是否符合尊卑有序的礼数。这对青少年的成长有好处还是没好处?
鲁迅曾写过一篇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其中写道:“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
人们都知道,“洋”孩子最没礼数,小小年纪就和家长老师讨论、争论问题,一点儿没大没小。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发明创造、新思想新观念还是“洋”人们做出来的。而越是讲礼数、讲“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孔学居统治地位时,中国人就越守旧停滞、缺乏创新创造力。“五四”时期反礼教究竟是反错了还是反得不彻底?
3. 丰富了伦理行为准则
以前曾讨论过,孔子偏离扭曲了相当一些上古基本伦理传统,例如:只讲“子孝”而从不提“父慈”,只讲“事君以忠”而从不讲“忠于民”,将以“德”为中心改变为以“仁”为中心,将“以义制事”扭曲为“小人喻于利”,将“礼繁则乱”的主张转换为繁文缛礼,等等。但他也的确提出了一些以往典籍中(尚)未见到的带普适意义的有关伦理行为的准则,这应该说是对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贡献。
孔子这方面的言论有不少,如“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过犹不及。”(《先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子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等等。
孔子之所以能被尊为圣人,多位有才能的学生之所以能够服他,这是需要有一定资本的。我们反对的是圣化崇拜、句句是真理,反对的是礼教这部分思想;但对其思想言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予肯定。
4. 宣扬了德政惠民思想
孔子虽然将西周时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民本思想改变为“君君,臣臣”的君本思想、加进了或强化了尊卑有序的礼数,但他也的确宣扬了上古传统中的德政惠民思想。
《论语》开篇不久的一段话可以说代表了他的政治准则:“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他讲“爱人”在不少情况下也很可能是真心的,比如这件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
他曾称赞子产说:“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他也主张“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
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今年歉收,我用度不够,怎么办?有若答道:为什么不只收一成税呢?哀公说:我收二成税还不够,收一成哪行呢?有若回答:百姓够了,君主怎么会不够?百姓不够,君主又怎么会够?(“哀公问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合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
有若与哀公的这段对话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常常成为后世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理论根据。尽管这番话是孔子弟子讲的,但也可以算孔子一半功劳。(有人也曾指出,过分强调藏富于民、国家财政空虚,这对国家百姓不一定是好事,特别是在有急难时。这一看法也值得考虑。)
5. 继承了注重教化的传统
我们民族自有记载的尧舜禹时代起,就有重视教化的传统。如《舜典》中即有:“帝(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大禹谟》中有“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夏书?胤征》中有“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意思是说:每年开春,有官员在大道上摇着木铃宣讲法令政令,并收集意见。《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有:“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可见《胤征》中所载是实。)
周公也非常注重教化,他曾对即将赴任担任卫国国君的康叔讲:百姓只有受到教化才会从善、安定。我们要时常用他们殷商先王、哲人的美德为准则,来安定、治理殷民。现今百姓不教化,就不知所归;不教化,就谈不上国家治理。(“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康诰》)
如本文开头所述及的,孔子时代以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和体系一直是非常发达的。
孔子也继承了上古以来重视教化的传统,主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
在少有的谈及军事的言论时,孔子也是更注重“教”:“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这些属于“教化”范围的“教”自然应予肯定,但另一种“教”就值得商榷了:一次,孔子去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这里人口挺多啊!冉有问:人口多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让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富起来后又怎样呢?孔子回答:“教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需要讨论的是,孔子这里说的“教之”是教什么?如果是教文化知识、宣讲法令法规、教必要的礼仪规范,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如果是后来所讲的“兴礼教”,即推广体现尊卑有序、繁琐复杂的“礼”的规矩和程式,那就应该否定了。
在《论语?先进》中,当孔子的几个弟子各言其志时,还是这位冉有讲:“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孔子对他的话也未持异议。可见在孔子师徒的心目中,“富之”后的“教之”主要还是指“礼乐”。
孔子还讲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鲁比齐更讲“礼”,而鲁离完善的“礼”也还有差距;所以齐应向鲁转变、鲁应再向“礼”完善。那么远为更富强繁荣的齐变为衰弱封闭的鲁是否有价值、是否合情理,这不在孔子的考虑范围内,孔子关注的标准只是“礼”。
孔学这种“兴礼教”受到后世很多儒生的追捧,但推广体现尊卑有序、繁琐复杂的“礼”的规矩和程式对国家繁荣富强是否有利,这也不在这些儒生们的考虑范围内。对这种“兴礼教”应给与正面评价吗?
汉武帝和隋炀帝都曾“大兴礼教”,以此作为他们是“有为君主”的象征之一,结果是衰亡或濒于衰亡;明初和清代是孔学礼教最居统治地位时期,结果都程度不等地步先秦鲁国守旧封闭停滞落后之后尘。但由于孔学礼教的尊君抑民特性为所有君主所拥护、提倡,因此已渗透到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只能遗憾地说:五四时代反礼教还不彻底,也未能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真正优秀的成分立起来,因此直到现在还能感受到礼教传统的负面影响,近几年随着注重发扬民族传统的时机又有蠢蠢复活之势。如果不是有一些人士抵制,而是放任礼教思想的重现和蔓延,我们有可能会再次步入守旧封闭停滞落后。
至于对孔子本人我们倒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孔子思想和言论中的确有一些应该肯定、值得肯定的内容。而且其他诸子及作品,如《老子》、《墨子》等,也都有各自的弱点和缺陷;如果对他们搞圣化崇拜、句句是真理,也会造成很严重的负面作用。(《尚书》、《诗经》、《管子》等因为是多人文集性质,因此偏颇要相对少一些,当然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在古希腊诸位哲学家中,中世纪对亚里士多德有些圣化和句句是真理,近代对亚的批评也就相对多些。对孔学系统中的礼教这部分思想,我们需要彻底扬弃;但对孔子本人,似乎“去圣”就可以了。作为先秦重要诸子之一,孔子这一历史地位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