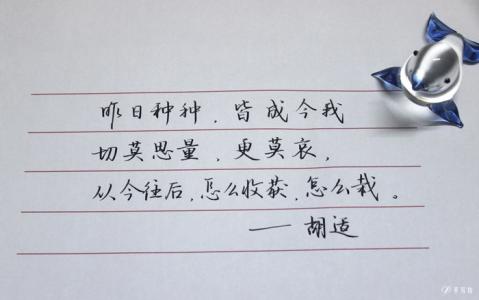0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能把刘斯箴这美丽的名字,与样貌普通的她本人对上号。那时,我们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大学同班同学。
那是一个很小众的讲座,一位来自英国的法学教授来到我们学校,松垮着一张散漫的脸,说着有口音的英文,面带怠倦地讲着关于英国新闻法的内容。整个讲座枯燥无味,清汤寡水,我都怀疑那个白人老头在盘算着,回到朴茨茅茨的寓所之后要喝几杯红酒。本来就稀稀拉拉的同学,走的走,打哈欠的打哈欠。最要命的是翻译—我校外语系的一位英文教师,在讲台右侧同声传译。他杵在台上,捏紧几张皱巴巴的A4纸,结结巴巴地说着慢半拍的汉语,那些字踉踉跄跄地从他嘴巴里跌了出来,郁闷得我呲牙裂嘴口歪眼斜。偏偏他还声音洪亮,佯装出外交部发言人的自信,每翻完一句,就要僵硬又装逼地笑一下。
“这学校太差劲了。”两年来的日日夜夜,这句话都要在我脑海中循环几十遍,事到如今,也只好认命。
正当我甩起书包打算逃出这间教室之时,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老师,刚才那句,您翻错了,前一句,也翻错了,再前几句,统统翻错了。”
教室突然静了。
我停下手中的活计,与剩下为数不多的学生一样,看着第一排那位姑娘的背影。英语老师的脸涨成了猪肝,强笑着说,那么这位同学,你说怎么翻才对?
她的脸转向白人教授,优雅而流利的英文从她的口中淌出,清清澈澈,延绵不绝。教授的眼睛越来越亮,连连点头说着Yesyouareright,yesyou’vegot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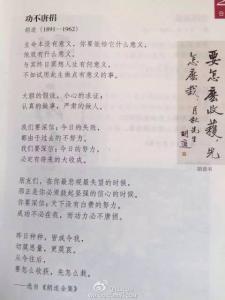
整场讲座成为了他们俩的学术研讨,到了最后,教授站起身来,走到台下,与她握手,握了好长时间手,大体在说,没指望你们能听懂,我研究了一辈子新闻法,做了无数场谁也觉得没劲的讲座,没想到,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姑娘你最懂我的心。
空旷的教室安静了一会儿,突然炸响雷鸣般的掌声。
我站在后排,呆愕当场,忘记了鼓掌。
怎么可能?
这不是和我一个班的,刘……刘什么来着?
1
刘斯箴是那种毫无特点的女孩儿。就像你在路边看到所有人的脸一样,没有被记住的价值。
安安静静的,话很少。若用两个字来形容,只能用“文静”。这个词很奇妙,通常用来形容貌不出众、语不惊人,有些内向,话有些少的姑娘。这两个字还可以替换为“普通”、“没特点”“差不多”等等等等。
身高中等,姿色中等,体形中等,气质中等。看吃穿用度,家世也是不好不坏。匀称中有些偏瘦,连穿着打扮都有些中性。
记得大一军训时,班里几乎每个姑娘都有些绯闻,有的是和学长,有的是与同班同学。经历了青春期上半阙荷尔蒙的淤积,在大学的时候骤然炸裂。但刘斯箴没有,像一滩深水,平静无波。军训就在太阳底下晒,也晒不黑,总是白白净净的。穿着绿色的军训服,帽檐儿有些低。见到熟悉的同学,就点点头算打过招呼,遇见不熟悉的,就略一低头避开目光。
那时,天气仍然炎热。女孩儿们都乘上夏天的末班车,裙子、吊带衫、热裤、凉鞋,慷慨地展示着青春的肉体。记忆中刘斯箴总是穿着长裤,有时是卡其休闲裤的,有时是灰色运动裤,有时是蓝色牛仔裤。脚下不是运动鞋就是帆布休闲鞋。头发不染不烫,指甲干净整洁,不化妆,不纹身,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
不谈恋爱,很少说话。
其实男生也没兴趣和这种女孩儿谈恋爱。
每天按时上课,上课认真听讲,一笔一划地记笔记。下了课慢吞吞地收拾书包,有时自己一人前往食堂,有时与舍友们一起。每当她与舍友们走在一起时,她仿佛一团空气,默默无闻,无味亦无声。
评奖学金时,她不用评定。年级第一,国奖。
当院长邀请她,在全校师生面前做事迹报告时,她谢绝了院长。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她轻飘飘地留下这么一句,院长半天没说出话来。
标准心无旁骛女学霸。大抵可以如此定义。
2
可是,我的室友吴老呆是个只会学习的呆子,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每天点灯熬油地学习到深夜。他对自己的成绩有着苛刻的要求,可每次总是考第二。像他和刘斯箴这种奇怪的人,总会崇拜学习比自己好的异性。在经历了两次第二之后,老呆对状元刘斯箴产生了深切的迷恋。
“她的背影好好看。”
“她学习那么好,却总是不主动回答问题,多么低调的姑娘。”
“她走路时,多么端庄稳重。”
“像她这种专心治学的姑娘,已经太少太少了。”
“我对她不是喜欢,是倾慕,倾慕你们懂吗?”
室友们纷纷表示,追女学霸一定会落得不动然泼的结局。
老呆果然呆,他坚持要追,并且是用最俗的方法。
提前布置了计划,再串通了她的室友。在她在宿舍的夜晚,表白!
那一晚,在惠欣公寓楼下,我们宿舍全员出动,用蜡烛摆出一圈温暖的红心,老呆站在火焰之心正中央,攥着一大把玫瑰,声嘶力竭地吼着“刘—斯—箴,我—喜—欢—你—”
围观的人们纷纷跺脚起哄,在一起!在一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