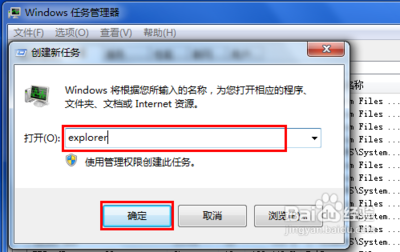小张的脸平静得可怕:“老板,死一个民工算大事吗?以前在我们工地上经常砸死砸伤人,谁关心过?”
小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据说,目前北京已经有85万外来农民工,那么,北京便有85万个“小张”。
【一】
那天,我和男友紧紧捏着一把锃亮的钥匙。钥匙刚从房地产商手中取来,被我们的掌心焐得温热,轻盈得如同一片幸福的羽毛,又沉重得好似泰山压顶。
5年了,我们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尽管几十万贷款山一样压在肩上,但这个城市,对于我们来说,终于不再陌生。我们幸福地依偎着,站在楼下等小张。小张是朋友介绍的,一个装修队的小头目。
……
他太瘦弱、太单薄、太轻飘,以至于走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的存在。如同一根伶仃的竹竿,他面色枯黄,乱蓬蓬的头发沾满石灰与木屑,一件薄薄的粗劣西服被他紧紧拉裹着。下身是一条溅满石灰浆点的劣质裤子,空荡荡地套在腿上,风一吹,像两个袋子。
“对不起,我迟到了。”男人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努力挤出笑脸,用力咳嗽。
“你就是小张?”我惊讶地说,看着他拼命扯住破西服瑟瑟发抖,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不冷吗?”
“还好。”小张谦卑地笑,“我走路过来,走热了,就不冷了。”
哦,怪不得,他从十几里以外的牡丹园走路过来,而且顶着这么大的西北风,不迟到才怪。
只是,他为什么要走路?不是有公共汽车和地铁吗?我不好意思问。小张垂着脑袋,安静地跟随我们进了楼。站在亮晶晶的电梯间里,小张捂住嘴巴,蜡黄的脸被一阵阵干咳憋得通红。
“你病了吗?”男友问。
“没,没有——”小张急忙摇头,拼命压抑着咳嗽,“被灰呛的。职业病,呵呵,做我们这行,好多这样。”
我笑了。只是听着他一声接一声地干咳,不禁暗暗担忧。但我什么也不能说,说多了,害怕他多心。我们很快便谈妥了装修事宜。小张开出的价钱低得令人吃惊,面对我们的重重顾虑,他只是腼腆地笑,轻轻地、肯定地说:“把活交给我,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二】
第二天,小张率领其他三个男孩把“家当”搬来,几乎顷刻间,我们空荡荡的毛坯房便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工地。白天,他们挥汗如雨地工作在浓烈呛人的粉尘中,纷飞迸溅的木屑里以及刺耳轰鸣的电钻声中;夜晚,他们便在地上随便铺几块硬纸板,裹着一条薄硬如铁板的破棉被入睡。事实上,毛坯房是根本无法住人的,没有暖气,没有煤气,没有卫生设备,苛刻的物业还经常断水断电。但是,小张他们,好比都市中的蟑螂,以惊人的生存能力,适应一切阴暗与贫瘠。

有时,我问他们夜里冷不冷?他们竟然乐呵呵地说,他们已经算幸福了。最难过的是盖楼的建筑工人,夜晚睡在没有封顶的大楼里,四处透风。下雪时,雪花能积满满一脖梗。他们还说,虽然是农村孩子,但一样是被父母疼养长大的,只是既然进城打工,就必须锻炼出一副刀枪不入的身子骨,麻木所有的感觉。
然而,小张没有做到。他的咳嗽还没有好,听力也不太好,估计与天天生活在刺耳凄厉的电钻声中有关。看他一边剧烈咳嗽,一边在“硝烟弥漫”的水泥旁劳作,我一阵心慌。
曾经多次劝小张,休息几天,看看病。但是,他总是紧张地说:“职业病,没关系。”然后,拼命压抑咳嗽。我知道,装修行业竞争激烈,他害怕因生病被雇主炒了鱿鱼。于是便再不劝他,只是偶尔为他买来一些止咳药,送去一些口罩以及几件冬衣。
对于我的小恩小惠,小张表现得非常淡漠,甚至连“谢谢”都不多说。但是,背地里,他却和朋友们说,我们是他在北京遇见的最好的老板。
我不喜欢“老板”这个字眼,让他喊“姐”,他坚决不肯,他的原则很简单:“‘老板’就是‘老板’。”
和许多装修工人一样,小张总是衣衫不整,身上永远散发著刺鼻的味道,脸上永远干枯,如同风干的水果,可怜甚至可笑。这令都市中的人们,拥有太多轻视他们的理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