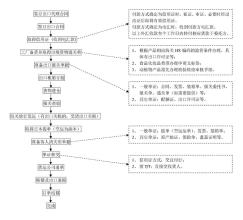不同于乌鲁木齐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漫步阿勒泰市街头会让人找到一种回归自然平静的感觉。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落叶飘零在小路上,颇有宁静诗意之美。山风一吹,随风洒落的“簌簌”声又有其动态之美,如聆听自然的音符。阿尔泰山成就了阿勒泰地区一方奇山异水,千余平方公里的境内散落着许多美景,不禁让人沉溺其中。出了阿勒泰市沿额尔齐斯河到周边的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富蕴县、青河县,一路秋景无限。
来自北方的树
秋天季节来到阿勒泰,我总爱选择下午落日时分去白桦林中散步,享受它给我的抚慰。踩在落满金黄叶子的草地上,身心是那样充盈和满足。树干上的斑斑疤痕就像它明亮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瞅着你,向你诉说着它们心灵的创伤。头顶上的枝头,有黄、有绿也有红,记录着它们生命的轨迹,让你无限想象,思绪万千。
白桦树属于北方的圣洁树。这种树耐寒不喜热,学名为疣枝桦,又叫疣桦、垂序桦、疣皮桦,是欧亚大陆温带古老的小叶型阔叶树种,也是新疆北部山区的落叶阔叶乔木树种。按照海拔高度,它们适应在1000米至2500米左右的地区生活。阿勒泰地区是新疆的白桦树集中分布最多的地区。
秋天来阿勒泰,我都与她相随相伴,它让人爱怜,又浮想联翩。如同俄罗斯人把它比作国树一样,它在我心里已经成为阿勒泰的象征。它富有朝气,充满浪漫。春暖花开时节,它从沉睡中醒来,吐露的嫩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清新秀丽;明媚的夏日,它比肩接踵,用它繁枝茂叶装扮起满目灰褐色的大山和涓涓碧水;晴朗的秋日,阵阵风起,它在萧瑟中呈现出一片金黄;冬日来临,自然万物失去了往日光彩,枯草在寒风中摇曳,凋残的树木已改变了原本的颜色,唯有它,依旧白白的树干,紫红色的枝条。它像一首诗,一首歌,让我着迷,让我爱恋。
白桦树沿着额尔齐斯河一直延伸向前,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它们的种子在这里的山谷中随风飘散,落到哪里就把根扎到哪里。河谷两岸只要有水,就有它们的踪影,尽管没有一棵树干洁白无瑕,但那是因为它们从落地生根到成长壮大,经历了太多风袭雷击和寒霜雨雪的缘故。在新疆,能够形成大面积的除了松树和胡杨,排在第三位的树种算是白桦了。阿勒泰市、哈巴河县、布尔津县、清河县城周边都生长着以白桦树为主的大片次生林,当地政府已经把这些林子建成了公园,成为游客来此的必去之地。
在喀纳斯湖景区和白哈巴村之间,有一片不很大的白桦林,是区间车的必经之路,本来不是景点,可每到金秋时节车经过林子都会被游客叫停,人们簇拥着纷纷下车,在林子里拍照留念。那些专业创作者,更是流连忘返。这片白桦林不知留住了多少人们的心。只要去过禾木的人,都会对禾木河桥旁的那片白桦林记忆深刻,它太招人喜爱了,谁看到眼里都会把它们永久定格在心里,这是一个魂牵梦萦的地方,亲人们在这里寄托祝福,情人们在这里海誓山盟。
斜阳下的白桦树,虽然没有杨树挺拔、榆树粗壮,没有柳树娇柔,松树苍劲,但是在万千树丛中,却彰显着自己不屈的生命力。我崇敬白桦树,是因为它历经风雨不改英姿,它活着树皮是白色的,死后树皮仍然是白色的;尽管它不是栋梁之材,也不是稀有珍贵树种,经济价值也不高,但是最先成林的是白桦树,只有当白桦成了林,松树这些不太喜光的树木才能在白桦林里暗暗生长,而当松树长大了,白桦树就让位了,会纷纷枯死,这就是它的不平凡之处,它的奉献精神。
白桦树沙沙地响着,纷纷落入水中的黄叶随波逐流,无声无息;树干的倒影躺在绿绿的水湾中,给人丝丝宁静。更远处,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像一条银色的缎带,横亘着,泛着亮光,在渐渐沉落的夜幕里,我的思绪也飞向远方。
印象中的白哈巴
被称为“西北第一村”的白哈巴,坐落在阿勒泰西北部的边境线上。这里最美的季节应该是秋季。每年的九月,山村被红、黄、绿、褐等多种颜色所包围,她被阿尔泰山皑皑雪峰衬映得如同一块调色板,吸引着四面八方前来的游人。她地处中国版图最西北角哈巴河县铁热克乡境内,距县城区117公里,东距喀纳斯湖31公里,北距那仁草原33公里,南距铁热克提乡38公里。
白哈巴村分蒙古族支系图瓦人居住区,哈萨克族居住区和边防站三部分,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图瓦人最集中的一个村子,也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图瓦人居住的村落,具有浓郁的图瓦风情。村子坐落在一个沟谷之中,四周被高山环绕,一条路从西到东把村子一分为二,村民们住着风格古朴的尖顶木头房子,这些木头房子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沟谷底部,金黄色的桦林、杨树点缀其间,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环村流过。山村的西北遥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国界河。
我不止一次的来过白哈巴,但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觉,而且有一种去了想再去的欲望。究其原因,是因为它实在不同于其他的村庄,它的纯净、饱和感的美丽,所处的地理位置,它的人文因素,使它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它还是一片净土,没有被人为地破坏过,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使人更加向往,那是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的处女地。
当天边泛起彩色的朝霞,村庄从睡梦中醒来,淡淡的炊烟飘浮在沟谷中。家家户户把牛群从栅里放出来,不用人赶,也没有人跟着,各家的牛只沿着路朝西边走,没有一头是朝其他方向走的,似乎它们知道西面是草地而东边是森林,一群过去了又是一群,一个紧跟一个,牛群中有的不时地回头张望留恋经过的草坡,嘴里�不停地叫着,好像在等待它的伙伴或朋友,它们走出村子,一直走向远处的草甸。
村子里鸡犬的叫声此起彼伏,草地上散发出的清沁混杂着炊烟的熏香是城市人感受不到的,这里的蓝天、白云,温暖的阳光也是城里人体会不到的。白天你可以静静地坐在小溪边看孩子们在木房边和草垛上捉迷藏,晚上你可以躺在草甸上数天上的星星。只有在这里,看到的星星是无以计数的银河,人马座和天琴座被清楚地分辨了出来,这里的繁星分季候出现,是观星绝佳的地点。 有一次,也是在九月,我在村子里遇见一群从广东来的游客,因为不知道这里的天气情况,来时穿得很单薄,又没有多带衣物,村子里的小杂货店也没有,搞得这群人很狼狈。为了能看到这里的日出,他们裹着被子来到半山腰等待最美时刻的到来,因为穿着单鞋,虽然身上暖和了,脚仍然冷得受不了。于是,他们就在地上跺着脚或在原地跳来跳去,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太阳出来就下了山,只有两个人坚持留了下来。他们说在广东没有见过雪山,更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村庄。他们是在一本画册上看到的,就慕名而来了,没有想到看见的比画册上的更美更生动。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一束光线打到村落的时候,他们兴奋地欢呼雀跃。一会儿的工夫,村子都亮了,树木、草地、木房、草垛一时被太阳照得暖烘烘的,大地顿时焕发出勃勃生机。
每到秋天的季节,除了游客之外,摄影人给这个小小的村庄增添了人气。上世纪80年代,这里还不为人所知,因为没有公路;90年代,有了简易公路,来的人渐渐地多了,但是喀纳斯的名气是因为有了深水湖怪的怪谈和摄影人美丽的作品,而白哈巴村则是这美丽景色中的佼佼者。它让无数的摄影人在这里驻足,让无数的发烧友不止一次地来到这里。到了21世纪以后的这几年,每当九月的清晨,村子四周的山坡上都站满了手拿相机的人,“枪筒”有长有短,人有老的少的,他们不为别的,就是想把这美丽的景色带回去让没有来过这里的人一同分享。
岩石上的花

每次进山,我都会刻意寻找岩石。山里当然是有岩石的,但若是多了草木,岩石反而少见,因为它们早已被久远的时间风化腐蚀,成为碎砂土壤,又生长着植物,这时候,岩石往往只在山脊或者悬崖峭壁间。可那也不能阻挡我的脚步,一般的�f岩峭壁只是看起来危险,无需太矫健的身手,实在不行就停下脚步,仰望欣赏头顶之上的岩石风景。我对岩石有着一份难言的热爱,固然因为岩石本身即是天成的静物风景,更因为上面生长了薄薄的地衣,从此刚柔并济,阴阳调和,令人销魂蚀骨。
我愿意这般涉险耗力,就是为看地衣的美貌,这被人走过路过却常常忽略的景致。
山当然是令人喜欢的,山中花草树木都充满着灵气。可是,要说古朴斑斓,没有能比得上地衣的。地衣如画,可以是一幅工笔小品,也可以是宏幅巨著的印象派油画。山中看石看花看树都是风物,可更吸引我的是涂鸦般的地衣,如青草碧波一般的戈壁微孢衣,那永远如同春天般的颜色,无论什么时候都很惹眼。淡淡的蓝紫色如同点雾的白泡鳞衣,总是在小巧精致里衍生出烟雨江南或者傍晚毡房上袅袅炊烟的味道。
在北疆,最常见也最为斑斓壮观的,算是石黄衣和准噶尔橙衣,在岩石山参差的壁墙上大块大块挥洒着色彩,有灰绿色的墙茶渍地衣、黄绿色的地图衣、灰白色的粉盘裂衣,以及许多我认不出来的各种纹理和颜色都不同的地衣,它们有的单独入画,有的挤成一团一团如繁花盛开。像我这样的准专业植物爱好者,每每进山,很多时候不得不减掉花在探访奇花异草的时间,而在岩石峭壁间流连忘返,观察地衣的扩展纹路,看着它们从四周慢慢辐射般生长。有时候我盯着只有半公分左右的地衣,想它们已经生长了多久,还要经过多少年,才能集结成一大片,绘出它们自己的图画。
地衣之美,犹如它的名字,大地的衣裳。仿佛开天辟地,鸿蒙之初,地球睁开了迷蒙的蓝眼睛,它顿了一会儿,懵懂之间却灵智初开,忽然说,我要一件衣服,于是就有了地衣。地衣出现在裸露的岩石上、土壤上,乃至于林木上,地衣出现在大地的身体上。从几个彩色的小点开始扩张,经过千百万年,如同点石成金的金手指,终将这大地画出斑斓绣锦,浮光跃金。从植物分类上,地衣是一种很低端的植物,更确切说,它是真菌和藻类的共生体。地衣酸水滴穿石般打开坚硬岩石的缝隙,制造土壤,为其他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是大地最早的开拓者。为此,地衣常常和瓦松、瓦莲、景天这些喜欢在岩石缝隙间生长又萌态百生的植物混在一起,组成惊人的美的画面。
岩石上的地衣往往是壳状地衣。此外还有叶状地衣和枝状地衣,更容易见到它们在土壤上和枯树上。有的地衣还可以进嘴,著名的地皮炒�u蛋里的地皮菜,即是一种叶状地衣;还有一种叫做藏地雪茶的,即是一种白色枝状地衣――雪地衣,被用来泡茶喝。其实,咱们新疆也有雪地衣,只是没人关注,更欠人欣赏它在天山雪线上纤细纯净的美丽,还有无数山林中、松树上垂挂的长长的软软的松萝,别有梦幻的感觉。
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端天气,对物种要求很高,既要超级耐热又要非常耐寒,冬夏温差高的超过八十度。然而,上天仁慈,赐予我们多种多样的地衣。地衣用它沉静的顽强的生命力,在岩石、大地上画出妙韵天成的图卷,有着掠夺般的气质和美貌。岩石上的地衣,仿佛从内心伸出手,细细抚摸岩石上的纹理和宛转线条,千回百转中,体会生命与永恒的对立统一。我见到最美的地衣,是冬天的戈壁微孢衣。群山枯寂,然而在白雪覆盖的岩石侧面,碧色地衣犹如春草初生,在呼吸之间荡漾着春天的气息,鲜明生动。当然还有更美的,塔城的尹锡梦老师跟我讲述他年轻时看到的岩花――零下十度左右的天气,半结冰的流水绕过岩石,而岩石上地衣有红橙黄绿黑五色,雪、冰、岩花、流水共同构成的绝美画卷。四十多年后,他仍念念不忘,向我夸耀和怀念岩花的美丽。
心向往之,我要去寻找,以后冬天我也要进山,去看最美的岩花。我曾经孜孜以求妄图知晓人生可能达到的境界,返身归来,能看到此生最美的风景,其实已经很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