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谭维维搭档华阴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在中国之星的舞台上震撼全场,也刷爆了朋友圈。
先来看一段纪录片视频,感受下黄土地上古老的原生态摇滚。
电影《活着》、《盲山》、《桃花满天红》,话剧和电影《白鹿原》里,都有老腔唱段。(下为电影《白鹿原》片段)
郑钧的《长安长安》里也有老腔采样。
陕西省华阴县双泉村,华山脚下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里,代代相传一个老腔皮影戏班,是该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只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他们登台了
摄影/陈团结
他们登台了。带着自制的月琴、板胡以及梆子等乐器,还有一条长凳。有的挽着裤腿,有的敞着怀,这与他们在村子生活时的形象没有什么两样。在台上,他们有的径直蹲下来,嘴里叼着烟袋——那是他们的日常姿态;有的席地而坐——那是劳累过后最惬意的姿势。对于他们,任何修饰或者化妆都是奢侈的。他们要展示最本真的自己。
“女娲娘娘补了天,剩块石头成华山,鸟儿背着太阳飞,东边飞到西那边,天黑了又亮了,人醒了又睡了;太上老君犁了地,豁出条沟成黄河,风儿吹月亮转,东岸转到西岸边,麦青了又黄了,人兴了又张了……”
唱到尽兴之处,他们仰天齐声长吼,用力跺地,群情激昂。把内心尽情地宣泄出来,声音苍凉雄浑。一位老人突然站起来高举木块,和着曲调,狠狠地击打一条长凳。此种景象,被形象地描述为“众人帮腔满台吼,惊木一击泣鬼神”。
他们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代表。与其他农民不同的是,他们是陕西华阴老腔的传承人。他们的名字曾随着文化遗产申报材料进入专家官员的视野。通过老腔,他们传递出了中国农民对于活着的感受。他们最大的已经近80岁,最小的也已50多岁。他们是一个不到20个人的群体。
一个不经意的发现
摄影/歌者
那是一个不经意的发现。2000年的一天,华阴老腔保护中心主任党安华正在看皮影戏,悄悄掀起白幕“亮子”想看看后面的情景。他顿时被老腔艺人所迸发的激情惊得目瞪口呆。“后面的东西真是太精彩了!单是靠看皮影戏的时候听他们的演奏,感受不到那种激情和冲击。”学导演出身的党安华意识到,与其把皮影戏呈现给观众,不如把人性的东西呈现给观众。
老腔的说唱形式与皮影戏融合后,成了互为载体的封闭式演出,老腔艺人们处在被包得严严实实的环境中。对于他们,观众“不见其人只闻其声”。但由于遭受现代社会光电传媒的冲击,皮影戏这种传统的民间娱乐形式正在被百姓疏远。
艺人们外出表演时,面对的常常是同样上了年纪的观众。与其说那些观众是在看皮影戏,不如说他们在打发无聊的时间。无论艺人在幕后怎样卖力说唱,年迈的观众已经很难被他们感染。
从幕后走向前台
摄影/陈团结
党安华决定尝试一下。他把华阴县境内的3个老腔皮影班社的骨干力量集中到一起,动员他们走出白幕亮子,直接面向观众表演。老腔艺人习惯了幕后的说唱,如今却要走向前台面对观众,该如何表演?
老腔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本色演出。党安华对他们并未提出更多要求,只是让他们把台词的内容弄清楚,把最真实的感受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
至今,党安华还会为当时的尝试庆幸。2001年,老腔的传承人张喜民、王振中、张新民等12位老腔艺人组建了老腔班社。自此,他们正式走上前台。
这种尝试挽救了老腔艺术。曾经,老腔皮影戏艺人们更多地是在村民有婚丧嫁娶之时演出。经过变革后的老腔,开始引发外界关注。
老腔传人张军民(中) 摄影/陈团结
艺人们曾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也曾到上海音乐厅与西班牙艺人同台竞技。他们还曾到香港、台湾等地演出。他们展现出一个真实的黄土高原上的中国,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和老腔艺人一起走过10年风雨的党安华认为,老腔之所以打动人,因为它是原生态的东西,把农民的憨厚朴实、艰辛豁达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尽管和皮影戏剥离开来,但它的风格一直没有被破坏,揭示人性的东西没有改变,“它最大的魅力就是真实,不矫揉造作。”
当他们开口吼唱的时候
摄影/歌者
在老腔中,几乎没有欢快的花音,因为他们需要把生活的悲苦在顷刻间发泄出来。它是一种生命的挣扎与呐喊。
老腔的起源地位于黄河、洛河、渭河交界地附近的双泉村。水路的便捷,让这里成为汉代京都长安粮仓的所在地。这造就了附近百姓依赖码头为生、从事船工的生活。逆水拉船的征途中,他们齐声呐喊,以释放力量和情绪。久而久之,便演化出老腔这种艺术形式。
老腔艺人用心灵传递出的情感,会让你的内心不由自主地受到触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沉默的群体,沉默地活着,又沉默地衰老。只有当他们开口吼唱时,才会释放沉寂已久的内心世界。声音沙哑,荡气回肠,充满了力量。那是一种执著而又倔强地忍受着的力量,忍受现实世界给他们带来的悲辛和幸福、无聊和乐趣。
陕西作家陈忠实曾经多次观看老腔。每次看老腔,他都会禁不住眼眶湿润。经过他的推荐,老腔参与了话剧《白鹿原》的演出。整出戏以老腔开场,又以老腔结尾。在导演林兆华的眼中,没有老腔艺人,话剧《白鹿原》就做不出史诗感。
如今能唱老腔的不过十余人
摄影/陈团结
像很多文化遗产一样,如今的老腔也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在民国时老腔皮影的鼎盛时期,几百口人的双泉村有十几个戏班。如今能演唱老腔的也不过十余人。
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老腔皮影一贯是家族传承的方式。诸多清规戒律让它仅限于华阴张姓家族中留传。除非至亲,一般人不准入班。既已入班,不准再搭其他班社。剧本绝不外传。这无疑大大限制了它的传播范围。所以时至今日,它依旧仅保留在华阴境内。
现在的老腔班底平均年龄是66岁。年龄最大的77岁,最小的也年过55岁。他们平时耕作,农闲时会聚在一起演奏一番。尽管他们也到很多现代都市演出,但那不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为了挽救老腔,老腔艺人抛弃了门户之见。老腔的传人“白毛”王振中曾称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愿意教。在当地人眼中,王振中身上有很多传奇。他曾为电影《活着》配唱,也曾为电影《桃花满天红》配唱。但到现在也只有两个人愿跟他学习。
年轻人的缺位
老腔传人张喜民保存着老腔自乾隆年间
传下来的百余个戏本。 摄影/陈团结
华阴市也开办起老腔培训班。2008年,培训班招了第一批学员,有二十五六个人。“但年龄都偏大。”党安华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学习,但实际情况显然让他失望。
它不是在培训班上就可以学到的艺术。“三年两年学不出来。”党安华尽管和老腔艺人长时间待在一起,但他还是没法开口唱。他总结的原因是:“那种积累不是星星点点的学习就可以积累出来的。这与老腔艺人的性格、生存方式有关系。他们是通过老腔来表达他们的灵魂。没有那种生存体验,你很难达到那种境界。”
老艺人的名字,尘封在泛黄的戏本上。 摄影/陈团结
为了保护老腔,华阴文化局每年都会安排老腔艺人体检,给他们发放补助。当地文化部门也在搜集整理老腔曲谱和剧本。为了让老腔不被遗忘,文化部门不断组织老腔艺人演出。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强老腔的生命力。
这并不能激发起年轻人对于老腔的向往。出于现实的考虑,双泉村更多的年轻人已在城市中打工。在他们眼中,时髦的都市生活比已成古董的老腔更具有吸引力。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陕西华山脚下我听到了华阴老腔这样一个戏种。艺人们沙哑苍凉的音色迅速引发我的共鸣,让我刹那间热泪盈眶。特别是当他们仰天长吼一起唱“拉坡”调时,让人感到无比震撼。
尽管我自小在农村长大,自认为对农民有深刻的理解。但在听完老腔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理解是那么浅薄。所以,在听完老腔后,我迟迟写不出一个字。真正理解它,需要用心去倾听。它将会带你走进历史深处的世界,让你感受一个底层群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尽管更多时间是沉默的,但一旦爆发,将会势不可挡。
摄影:陈团结、歌者
封面图:陈团结
编辑:风物君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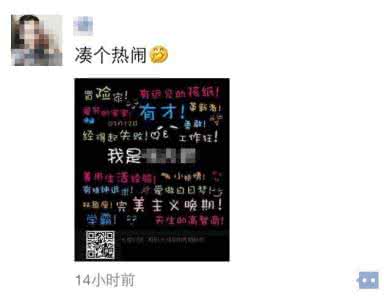
END
本文由地道风物(didaofengwu)编辑,欢迎转发分享,转载至其他平台请于微信后台留言,勿擅自转载。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