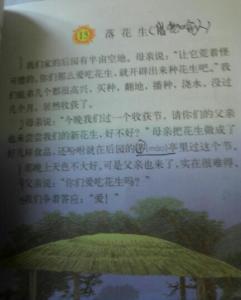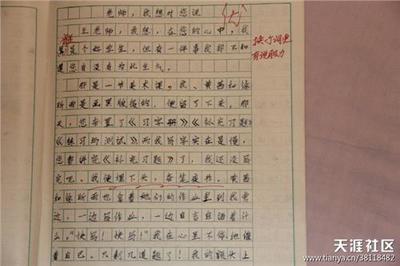上午下课后,我们驱车上路。南京变化真大,已步现代化大都市的行列,道路交通状况大为改观,从会议中心到警官学院仅用了十分钟。
江苏警官学院坐落在南京中华门外安德门,前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江苏省公安学校、八十年代的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她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两次就学,读了中专和大专。
1979年9月9日早上7点10分,我一人持录取通知书,挑着担子(一头是箱子,另一头是放有被子、脸盆、水瓶的网袋)上了从姜堰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这是我长到18岁第一次走出姜堰,当经过江都万福闸时,心潮澎湃,嘴里差点喊出:“啊,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午11时进入仪征汽车站,人们下车到饭店吃饭,每人是四角五分钱一客的饭,是韭菜炒肉丝、半斤米饭。我舍不得花钱,拿出母亲当天早上煮的粽子,吃了两个。下午二点,汽车到了中央门汽车站,我在出口处找到写“江苏省公安学校新生接待站”的牌子,一个职工在等候我们新生。我之后是宝应的王泽洪(现宝应县公安局副局长)、靖江的秦雨花(现江都市公安局长),秦雨花因只十六岁,是父亲送他来的。大约半小时后,一辆客车开来,是公安学校的车子,从火车站接了十几个新生,经过汽车站带我们。我对着刚用五分钱买来的地图,知道汽车是向南开,但不知怎的总感到是向北开--第一次到大城市晕头转向了!
到学校报了到、买了饭菜票,按照安排住到一号楼201室。到食堂吃了晚饭,才发觉从家带来的毛竹扁担没有了,原来从车下来没带上。这下子急得挨个宿舍找,因这是家里唯一的竹扁担,少掉了如何向家人交待?最后在秦雨花宿舍找到,秦雨花父亲说他最后下车,发现有人把扁担遗忘在车上,怕被车子带走,就拿了下来。我连说了好几个“感谢!”,取回了扁担。
晚上,新生集中,班部大个子潘老师吹着哨子,喊着“立正”“稍息”等口令,把我们带到五楼大教室,讲了纪律、注意事项、近几天的安排,就散会。大家没有立即就回宿舍,站在大阳台上向东北方向看南京城里万家灯火,向正北方向寻找那闻名全国的南京长江大桥依稀灯光。
入校的第一个夜晚,辗转反侧,想着重病中父亲、辛劳中的母亲、轰鸣中的车间、操作中的师傅。
第二天,进行分班,我分到一班,宿舍也做了调整,一班在一楼,我其他七位同学住103室。老师也明确了:董文江老师、毕良珍老师、武舞老师分别任一、二、三班班主任,我们大家简称他们“董必(毕)武”。
第三天上午是开学典礼,省厅常务厅长褚玉祥、政治部陈主任和学校几位副校长出席了开学典礼,褚厅长做了讲话。当时,校长是省委常委、副省长、公安厅长洪沛霖兼任,主持工作的是顾校长,后来顾校长调动工作后是武舞老师的爱人孙校长主持工作。
公安学校管理是很严的,每天早上要出操,当时是创业阶段,只一个蓝球场,连操场都没有。早上,上操跑步是沿着学校门前的南京至马鞍山的公路向西跑,一般跑到小行或西善桥。晚上要集中上晚自习,班主任还要到班上检查。由于是恢复高考不久,学生中还有一些老三届的,七八级中有人已结婚生了孩子,也有的在老家已谈了恋爱。记得七八级有个同学把家里恋爱对象吹了,人家母女找到学校,学校就把这同学给辞退了。老师对我们说:“公校(公安学校简称)是培养人民公安战士的地方,这里的学生要对党绝对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严守纪律、团结战斗!”
学校没操场,就发动我们把学生宿舍楼三号楼北边空地斜山坡挖平。我们每天下午去挖泥挑担,南京的丘陵土硬并有石块,无法用锹挖,就用镐刨。后来,学校也用扒土机来扒,这样,人工加机器终于把运动场弄出个模样来,用碳渣做跑道。这样,可以在场子上晚上看电影,早上上操,白天搞倒功、擒拿格斗了。不仅是操场,学校大路两侧的树,各宿舍楼前后的花木,也是学生们栽的。
任课老师有学校的,有从南大、南师等高校请的,也有是省厅、南京市公安局业务处室的负责人兼职的。留苏回来的梅老师教消防课、朱武老师教现代文学、南京教师进修学院李廉老教授讲古代汉语、杨良成老师讲授宪法和国家与法的理论、徐信老师教刑法和刑诉法、陈尉成老师教情报课、毕老师的爱人王强生教刑侦、王曹贵乾老师教日语、姬仰曾校长亲自教政治......业务课大多是省厅和南京市局的领导来上的。
在开学后一个多月,学校决定扩招,从苏、锡、常、南通招了100名新生,编为四班、五班。毕老师负责管理这二个班。当时,老师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每天晚上,董老师、武老师都到我们一、二、三班看望大家上晚自习。晚上熄灯后,有时还到学生宿舍检查,看看被子有没有盖好。当有学生生病,武老师从家中把病号饭烧好送到学生床头。
学校对过是坐小山,名叫菊花台。古时盛产菊花,故名“菊花台”。相传,清代乾隆下江南,到了安德门外,其时正值金风送爽,雏菊盛开,满山浮金点玉,溢光流彩,竟醉心忘返。此后,这里便以菊花台命名了。我们上学时一开始,一条小土路弯弯曲曲地上山,两边全是草,里面有许多四脚蛇,山上有许多毛竹、小竹子,有稀世珍品方竹,有携带一段美丽神话传说“嫁”过来的湘妃竹,还有各具特色的女儿竹、佛肚竹、菲白竹、孝顺竹等近百个品种。有许多高大的松树和龙柏、桂花树,还有南京地区罕见的金陵雀梅王、白皮松以及好些不知名的树。山上有两座水泥混凝土的碉堡,据说是当年日本鬼子修的,进去看看,小日本的工程质量是真高,绝不是豆腐渣工程。这山上还埋葬着九位爱国志士。1941年,日本制造了“珍珠港事件”。1942年4月17日,日军占领了菲律宾。日本侵略者对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人员进行诱降、逼降;要他们“改弦易辙”为伪政权出力,效忠“日本天皇”,受到了领事馆外交人员的坚决抵制。他们在敌人刺刀面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而被野蛮杀害。这九位烈士是驻马尼拉总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性,领事莫介恩、朱介屏,主事卢秉枢。萧东明,驻山打根领事馆领事卓还来,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衔领事杨庆寿,随习领事姚竹修,甲种学习员王恭炜。
后来这山上浇成了水泥路,烈士墓也维修一新。砌了六角亭、双竹亭、桂花亭、六角竹亭、雀梅王、天隆寺、塔林、玉乳泉等景观。当然,这是后话。
每天早晨,天不亮,许多同学特别是文科班、理科班和外语班的,就到教室走廊、路灯下,借着灯光读书。天一亮,大家就到菊花台上去读书,树林里、竹林里、山坡上、碉堡顶山尽是公安学校的学生。6时,大家又去准时出操。
下午下课后,晚饭后,大家到菊花台山上散步,阵阵凉风吹来,竹海沙沙作响,松涛呼呼鸾鸣,如处蓬莱仙境。入校时恰好八月,桂花飘香,沁人心脾,三十年后的今天仍余香留鼻!
我和文科班的周咸杰、我们班的孙瑞林,有时也和同宿舍同学在菊花台散步,大家谈课程、案例、社会、改革开放、人生,憧憬美好的未来!也有时看到通往石子岗的上山陡坡公路上拉板车的工人步履艰难,上去把他们的车子一一帮助推上去,也算尽点儿微薄之力。
在菊花台东侧约有一刻钟的路程,是将军墓。西侧平坦的山包上是南京军区在战争中牺牲的和和平时逝世的将军和校官墓,这里军衔最高的是1931年参加红军、曾任八路军第31军分区副政委、解放军60军军长、志愿军三兵团军长、南京军区参谋长的张祖谅中将。这位戎马一生、战功卓著的将军,老胃病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身体难以承受高强度的指挥作战,1952年7月当听到志愿军遇到入朝后最大的一次损失后,主动向陈赓和王近山请战要求入朝参加战斗,就连《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打仗素以“疯子”著称的兵团代司令王近山也忍不住上前紧紧握住张祖谅的手,激动地说道:“希望你能来,我马上向上级请求!”在他的指挥下,几千人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了,出其不意,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创造人类战争奇迹、书写了自己作战指挥生涯中闪亮的一笔,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当他率部从朝鲜回国,特地叫车在鸭绿江边停了下来,面对朝鲜国土三鞠躬后深情地说道:“不能忘了朝鲜人民的支援,更不能忘记永远长眠在朝鲜国土上的英雄烈士们!”由于长期积劳成疾,1961年5月13日张祖谅中将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如今我们每到将军墓时都向他和其他英烈们三鞠躬!
这坐小山包的东侧有一同样平坦的小山包,坐北朝南,有三座用石块和水泥砌成的坟包穹形墓,这就是著名的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墓。中为项英墓,右为袁国平墓,左为周子昆墓。这里十分幽静,前面的墓道宽广、松柏成排,环境特好。我们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带上书、报纸、干粮,来到这里铺上报纸,躺在地上看书。
菊花台、将军墓成了公安学校学生的花园。烈士们的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也成为了公安学校学生的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谐而奋斗的精神!
两年的学习很快就结束,离开学校的上一天晚下,我们宿舍的同学一起喝了在校时的唯一的一次酒。第二天早上,当离开学校时,我看看那座教学楼,流下了眼泪:母校,何时再回到您怀抱!?
毕业后下乡破案,有人问我:“你是从哪儿到公安局的?”我就骄傲地告诉他:“我是公(安学)校来的。”
1981年5月20日中午部分扬州籍同学毕业合影留念。后排从左向右为:金传铮(现高邮公安局副局长)、陈锦平(在扬州市工作)、王泽洪(现宝应公安局副局长)、夷文明(现扬州刑警支队大队长)、王日兵(现扬州市公安局油田分局副局长)。前排左起为:秦雨花(现江都公安局长)、宗长友(现泰州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我、基国平(现扬州市维扬区委常委、公安分局长)。由于当时通知仓促,缺少孙瑞林、邰为民、邵永江、王靖江。
1984年12月20日,我正在苏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跟班学习,接到县局通知:参加省厅在公安专科学校组织的成人高考复习班,准备参加1985年成人高考。啊,毕业三年多啦,现在第一次回母校!当时,学校没有地方提供全省一百多个公安干警复习时的食宿,把我们安排在安德门招待所上课、食宿。经过半年多的复习,我以第一名考上,100分的卷子其中数学99分、地理96分、历史98分。1985年9月9月日,我正式到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干修科学习。
再次脱产来上学,与第一次的感受大大不同。这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升华。同时,课程设置以及师资结构优化得多,教学也成熟得多。
曹贵乾老师从省厅预审处长的位上调到学校做教授,从原来教日语到现在教“法学基础理论”,这课程比过“国家与法的理论”要丰富得多;叶荣桂老师、张月亭老师也分别从省厅三处处长和南京市局刑警大队教导员的位上调来做教授,他们教的刑侦课已从六年前的案例的叠加,到现在的真正意义上的“刑事侦查学”,而且由于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讲刑侦理论课把人听得如醉如痴,似乎好象从今后什么案子都难不倒咱刑警;徐信教授还教刑法、刑诉法,不过教材已不是我们1979年初学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两法时讲义“白皮书”了,而是高铭宣教授主编的《刑法学》和统编教材《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深度和高度不可同日而语;朱武老也由过去教“现代文学”改教“逻辑学”,还成为“侦查逻辑”的专家;董文江老师已任学校党委办公室主任,他爱人孙晓东老师也调到学校任管理系主任,教授“公安管理学”;王强生老师成为侦查系政委。法律课增加了“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经济法”等,但与现在法学本科比,还少行政法学、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商法、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等课程。
几位老教授的课给人印象很深。钱老先生的“社会学”、陆老师的“中共党史”、宋老师的“哲学”、胡老师的“政治学”等等。
年轻的老师讲课引人入胜,带来了许多新知识。赵远老师的“政治经济学”,深入浅出,并把现代经济理论引入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得到大家一致好评;陈德祥老师、徐乃龙老师的“犯罪心理学”,使我们掌握了一个新的武器,为以后对付刑事犯罪打下基础;沈文祖老师的演讲,使我们知道“尤理卡”计划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张霞老师讲授“交通管理”,我们第一次知道“冲突点”、高速公路管理,十多年后当苏中大地建起宁通、宁靖盐高速路和姜堰高速互通时,我才感到这堂课是没有白听;何光沪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除了讲述“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外,还为我们介绍了从原始宗教,到现代宗教,从儒释道、各民族宗教到世界三大宗教的知识,我们一下子认识到:如果把宗教史剔除在外,人类历史就有相当一部分是空白,人类思想史可能无法下笔书写。这位清瘦、具有典型学者气质的老师,为我们阅好考试卷后,便到北京做了任继愈老先生的博士生。
许多老师是从外面请来的,这是时任校长的姬仰曾校长的主导意见。姬校长认为:应当从各个大学、科研机构请一些知名学者来讲课或开讲座,以拓宽干部专修科学员的视野。于是,请费孝通教授来给我们大家开讲座、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来讲课,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等等。长时间上课的有:南京农业大学陈教授来讲了一学期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上海复旦大学王松、王邦佐等教授来讲“政治学”。特别是王邦佐教授从政治学基本理论、我国政治、比较政治、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一直讲到国际政治与国家关系,其中关于英国文官制度的介绍,使我们看到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
与第一次来上学相比,幸福多了。带薪、老师学问很深、有教材。说起教材,我第一次上学时,公安教育才起步,没有什么教材。业务课除了发了一本公安部三局《刑事侦察学》外没有什么教材。上课要认真听讲,这个“认真”非同小可,因为没教材,上课记笔记要句句不能漏,下课核对笔记要字字不能错,否则考试就有问题了。所以,那时上课几乎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更没有一个睡觉的。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什么参考书,就到图书馆借书抄,《法医学》、《急性中毒》、《机械性窒息死亡》等书,全被我用晚自习结束后的时间各花了一个多月抄写好,当年的用十六开的纸抄了一尺厚。也正是抄书,使我对这些书的内容至今都大致记得清楚。第二次来时,不用抄书,但在这里基本功得到锻炼:比如上“手印学”课,根据王建伟老师的讲授,抓住要领,记住特征,反复观察,最终只要给一个硬币大的殘缺手印,就能准确无误地判定是何手何部位的掌纹,或何手何指何部位。这为以后的侦查破案工作打下了基础。
1986年5月16日我们宿舍几位同学在学校大门合影。左起:刘家佐(时任金湖县公安局长,班党支部书记)、葛新春(时任南通公安局刑警大队股长,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李兆喜(时任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股长,我所在的党小组长)。
2009年6月16日中午,我打手机把儿子从班上叫出来,在学院门前合影,到警官学院东侧的排挡里吃中饭,这是他上大学以来我第一次来看他。我向他讲述多少年前这里的故事。
我告诉他:上中专时,我在这里加入共青团;上大专时,我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在这里的学习、生活,也许就没有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

在今天,人们讲文凭,讲学历,讲学位,比母校是什么名校的时候,当有人问我:“你是那个学校毕业?”时,我仍然一点不自卑地说:“我的母校是公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