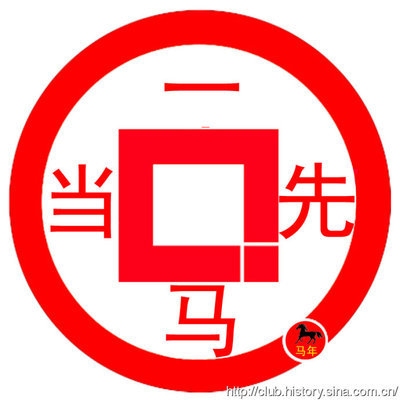本文为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医疗史”专题第五篇文章。点击阅读前四篇:一、二、三、四。
近代上海医疗卫生史的另类考察
——以医疗卫生广告为中心的分析(1927— 1937)
撰文:杨祥银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前言
近代上海广告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中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与商业竞争的产物。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商将国外经销商品的各种广告手段引进上海,尤其是那些国外的跨国公司,它们纷纷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以占有中国市场。而这些跨国公司又相当重视广告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而受到这种市场意识的影响,后来的华资企业也纷纷设立广告部,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中外商业广告战。
近代上海的广告形式多样,按照徐百益先生的分析,主要有布告招贴广告、报纸广告、图书杂志广告、无线电广播广告、路牌广告、街车广告、霓虹灯广告、印刷品广告(包括传单、说明书、目录、小册子、小画片、月份牌)以及电影幻灯片广告。近代上海广告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广告机构(包括企业的广告部、广告代理商、专业广告公司以及广告同业公会),有力地推动了广告的市场化、企业化与规范化发展。同时,为规范广告业的正规化发展,广告行业协会以及政府都颁布了相应的广告管理的行业规范准则与政策法规。
综观现有近代上海广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广告已经成为研究近代上海历史与上海文化的一个重要媒介物。它虽然无法反映社会的整体面貌,可是却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视角。正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先生所说,“广告可以说是社会中想象力和愿望的浓缩,是社会目标的产物,而有效的广告诉求正代表了该社会中消费者所认可的生活体验……藉此而了解一些透过其他性质的史料所不易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笔者以为,对于广告的观察不仅仅是限于对社会现象的反映,更为主要的是,它以图片与文字的双重信息呈现了现象反映之外的更为深层次的象征意义的表达。尽管,对于象征意义的理解会因为个人诠释的出发点和知识背景的差异而造成偏差或者是“无中生有”,笔者不知道这种诠释是否完全可信或客观,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在这些诠释中得到什么最终结论,而仅仅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医疗卫生史写作方法的可能性。
进入正文之前,笔者首先对文章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一交代与澄清。
1. 为什么是医疗卫生广告?
笔者在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医疗卫生史的过程中,需要查阅《申报》上的相关报道,而在翻阅过程中却发现关于医疗卫生的广告特别多。这里笔者将根据戈振公先生关于1925年《申报》和胡俊修先生关于1933年《申报月刊》上的广告统计情况来说明医疗卫生广告占有大部分(虽然两个统计分类方法并不相同,这里仅供参考)。

笔者以为,医疗卫生广告的频繁出现除了商家的商业利益考虑之外,是否还能反映出当时上海社会医疗卫生消费背后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呢?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广告跟当时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在1928 — 1937年上海市政府举办的16届卫生运动(其中有3届未能举行)过程中,当时很多药房和医院都参与了这些卫生运动,并且在广告言说中巧妙地以卫生运动为契机大肆推销。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很多广告都以“卫生运动”为标题。正是如此,文章试图超越传统的从政府医疗卫生政策出发考察医疗卫生的做法,希望以广告为中心做一文本分析,看看是否可以呈现另一幅景象?
2. 为什么是1927 — 1937年?
本文这样划分显然是出于研究的方便。不过也有其他考虑,主要是因为从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建立(1930年7月 1日改名上海市政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的10年是上海从20世纪初到建国前最为稳定的时期。而且,南京国民政府为实现国家重建的任务开展了一系列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现代化建设计划,而上海就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试验地。所以,本文也将会考察政府如何通过医疗卫生现代化以及卫生与国家的关系来表达它对于建立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诉求。
3. 卫生(hygiene)是什么?
卫生包括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而在英文书写中通常将前者表示为“hygiene”,而后者表示为“public health”,但有时又用“health” 来泛指卫生与保健。在传统的中国知识论述中,卫生通常指“养生之道”,主要指个人保健。可是随着西方卫生观念的影响以及以生物医学和细菌学为代表的西方医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卫生在官方论述中从过去的身体保健转变为以改善公共环境和加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能力为主的公共卫生观念。这种转变我们可以从1928— 1937年之间上海卫生运动的内容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卫生运动主要是针对如何改善街道卫生、加强传染病预防与控制能力。可是,从当时的医疗卫生广告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日常生活论述领域,卫生兼具个人保健与公共卫生的意义。因此,本文的医疗卫生广告范围,除了包括医药、卫生用品(牙膏、卫生巾、现代浴室设备、肥皂与香皂等)之外,还会包括保健品广告(包括各种补品与营养品)。
身体与国家:卫生的政治性
这里笔者将集中根据一些医疗卫生广告中的图像与文字内容及其象征意义的诠释来分析个人身体、卫生与国家如何通过对于医疗卫生产品的(想象性)消费联系在一起。当然,文章也会从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出发考察个人卫生对于国家的意义,以及政府如何通过个人卫生的社会总动员(通过卫生运动)来实现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医疗卫生政策成为国家加强社会控制的正当性借口。首先列举一些当时的关于医疗卫生广告言说的内容,然后进行分析。
(1)救国必先强民,救民必先强身,我国连年战争,利权外溢,国弱民病,已至极点。若不设法挽救,后患何堪。本药房秘制下列四种药品,为治病强身之惟一圣药。望我爱国同胞服愈病体,借可振作精神为国争光,将来国富民强,俾有厚望焉。(上海联昌德大药房德轩氏四种良药广告,《申报》,1928年4月27 日。)
(2)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呈请提倡国货。薛部长继冯总司令之后,提倡国货,不遗余力,近呈国府,拟具办法五条,均属切要,呈文有云:“我国教育未能普及,人民爱国思想亦未十分发达,无怪群趋于购用外货之一途”,现在民众站在青天白日旗帜底下,是必各具热忱,矢志爱国,一致改用国货,拒舶来品于千里之外,国强民富,庶几有焉。(上海中法药房人丹等广告,《申报》,1928年4 月27日。)
(3)卫生强国。精制卫生用品,提倡卫生要义。拭秽草纸,虽为微物,然其关系人体卫生极大,我国人日常所用草纸,多欠清洁,故常人患痔疮者,不能用草纸,即因其不洁而未消毒者,虽近来有外国货之卫生纸输入,比较清洁,然而利权外溢,用者痛心。本公司有鉴于此,特向利用纸厂定制卫生草纸……本公司制造公众棉织日用品等,质料精美,立意新颖,永不退色,切合实用,固已有口皆碑,毋庸赘述。现在国内之青天白日旗下,市政日渐革新,各处多宣传提倡卫生,近日上海特别市政府亦有卫生运动大会之举行,可知卫生之于人生,实称重要。(三友实业社卫生用品广告,《申报》,1928年4月28日。)
(4)体弱多病,其第一原因,在不讲求卫生,人民羸弱,遑言强国,故欲强国,必先注重卫生,现在上海特别市有卫生运动大会之举行,督促民众注意卫生,意良善也,本公司有许多精美卫生日用品,供给公众卫生上所需要。(三友实业社卫生用品广告,《申报》,1928年4 月29 日。)
(5)市政与卫生。市政改良,为今日当务之急,如翻筑宝山路及大统路、修建新闸桥、及添建乌镇路桥等、以便行人、此均为今日市政治设施、见诸实行者、市民卫生、亦市政之一、尤有改良之必要、市政府亦有种种之设施、夏令将届……霍乱吐泻、绞肠痧症、宜服虎标万金油……(上海虎标永安堂广告,《申报》,1928年5 月9 日。)
(6)雪耻!外侮侵凌,国家之耻。疾病侵凌,身体之耻。欲去疾病,首在强身。(上海九福公司百龄机补片广告,《申报》,1928年5月9日。)
(7)如何可使中华居国际之上风乎?国为个人集合而成,故一国之情形,恒视其个人之情形而定,苟一国之男女老幼,皆康强精壮,则其国必兴,否则病弱之躯无裨于建设,徒为社会之累而已,职是之故,凡属国民均应立志使其体格健全无亏厥,职如是则集腋成裘,人人皆为兴国之健者。(上海韦廉士医生药局红色补丸广告,《申报》,1931年 1月25 日。)
(8)世界文明各国,因卫生的进步,传染病已很少发现了;但是我国多数人不讲求卫生,所以各种传染病盛行,尤其是夏天里的霍乱症最烈。年来中央和地方卫生行政机关,对于公共卫生都十分注意,清洁检查,防疫运动,不断的举行,我们民众也应当热烈的参加。(上海五洲大药房亚林防疫臭水广告,《申报》,1936年6月15日。)
(9)强国必先强民,强民必先强儿。(美国宝华公司牛奶粉广告,《良友画报》,第 14期,1927年4 月。)
通过上述广告言说内容,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这些广告都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结于国民身体的病态,进而得出结论:“欲强国必先强民,欲强民必先强身”。(详见第(1)和(7)条广告)而身体多病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讲求卫生。(详见第(4)条广告)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卫生作为一种日常生活行为,因为对于亡国灭种的担忧,因为对于强大国家的向往与渴望,而变得富有浓厚的政治寓意。就连普通的卫生纸的使用和牛奶粉的饮用都成为国家强大的象征性行为。三友实业社在1928年4月28日《申报》上更是以巨大的篇幅注销以“卫生强国”为标题的卫生用品广告,其视觉效果足以激发起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与购买这些产品的欲望。很显然,这种购买与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赋予了政治色彩。
其次,我们从广告内容【详见第(3)、(4)、(5)、(8)条广告】可以看出当时的政府积极地领导了上海的卫生建设。如前所述,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建立之后一直致力于包括建立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在内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反映在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就是从1928年至1937年期间上海市政府举办了16届(其中第八、第十和第十一届未能举办)卫生运动。
通过对于卫生运动内容与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政府倡导的卫生运动中卫生如广告中的言说一样,被赋予了政治意义,身体成为民族复兴的基本要素。这种象征意义始终贯穿历届卫生运动。上海市长吴铁城给第十三届卫生运动的题词就是“强我民族”。《申报》在谈到第十四届卫生运动的意义时指出,“这次卫生运动除了促进民众健康建立民族外,还含有两种重大的意义:(1)近代物质文明的向上,使欧美先进国家的卫生事业走上了最健全的路……我国卫生事业的落后是很明显的事实,卫生事业的前进或是落后,颇足表现社会文化的髙下,因此这次卫生运动其所含有的最高意义,就是提高我国的文化水平。”在这里,卫生更是成为国家竞争与文明程度高低的衡量标准。1936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在给上海市第十五届卫生运动特刊的题词中同样反映了这种思想,“自强不息象天行健,卫国卫民生机烂缦,合群并进相观益善,民族复兴此其左券”。陈调元更是直接以《卫生运动与民族复兴》为题来谈两者的关系:“使各个人皆有康健的身体,自强的精神,推己及人,相习成风,不特为我人强身之本,实乃强国之基。方今国难日亟,谋我者日张我人为复兴民族计,必须全体国民总动员,从民族健康改造,使人人有卫生的习惯,养成壮健的身躯,一扫老大病弱的风气,必自踊跃参加卫生运动始。固知我人健强之基础在卫生。卫生,乃为复兴民族最实际而且最基本之要素。”在最后一届也就是第十六届卫生运动大会宣言中,为了突显身体健康要素在民族生存竞争中的意义,便通过与其他要素的比较加以论证,“民族生存的竞争,到现在已经成了最急迫的时代了。其竞争的要素有六:体力、智力、勇敢、机敏、耐久与团结。这六种要素虽然包含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然而,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没有强健,决没有健全的精神,所以复兴民族的根本要素,还是在求身体的健康,而要使身体健康,最基本的,还是要切实的提倡卫生。”
上述之所以反复引用关于卫生运动与民族复兴的关系,就是试图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卫生运动与其说是为了提高市民的身体健康和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倒不如说是通过卫生运动进行一场以倡导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的社会总动员。这种社会总动员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实现对于其统治政权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认可。或许从这里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国民政府将卫生运动作为其定都南京后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积极推行的“七项运动”之一。同时,为加强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总动员的方式以及作为一种仪式的规训作用,上海市政府卫生运动筹备委员会为卫生运动的开幕典礼规定了一套严格的程序。以第十四届为例,开幕典礼包括:行礼如仪、主席报告、市长致辞、来宾演说、学生童军代表行卫生劝导日宣誓礼、奏乐、摄影和散会。
第三,通过对当时广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将个人卫生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的广告主一般都是一些华资企业,主要是当时的一些药房和制药公司。这些企业为了应对来自同行的西方商家的激烈竞争,而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广告言说方式来刺激国人对于这些产品的购买与消费欲,当时有一句极为流行的话,那就是“用国货即爱国”。【详见第(1)和第(2)条广告】同时,为推销其产品和赢得社会声誉,这些企业积极地参与上海市政府领导的卫生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在即将举行卫生运动的时候,当时的广告言说内容中就会相应地加入关于卫生运动的信息或者以卫生运动作标题来吸引顾客。【详见第(3)和第(5)条广告】对于广告主来说,这些行为虽然是出于商业考虑,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企业有效地传播和强化了政府对于卫生运动与民族复兴这种密切关系的诠释。
就这样,承载个人卫生的身体被不断地国家化,身体的存在已经不再是肉体的延续,它俨然已经成为国家富强的基础。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都参与了这种卫生与国家富强关系的建构与想象,而显然政府在这种关系中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它有利地引导着对于这种关系的诠释。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黄金麟先生指出,(在近代中国)身体之所以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成为各种论述和实践性行动出发的起点,其实是和此前各种改革运动(同治时期的自强运动、光绪时期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后的清末新政)的失败有莫大的关系。身体并不是从一开头就与国家的存亡或族国的兴盛,产生密切的联想关系。显然,身体的国家化是亡国灭种危机下所引发的另外一种民族救亡运动。从上述的广告言说中和卫生运动大会的宣言中,我们无不看到对于中国贫弱的担忧与反思。
黄金麟先生对于近代中国身体国家化的考察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近代以来,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致力于各种各样的身体改造运动,建构一种有关身体的“应然”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他以1902 —1919年的军国民运动、梁启超的新民主张、1920年代中后期的公民教育运动和党化教育以及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为例来探讨近代中国身体的国家化过程。正是通过这些身体改造运动,使身体作为一种国家工具的历史发展获得一个“爱国”的美名包装。同时也说明了身体在近代中国已然变成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场域,一个满是教化权力与知识交结介入的场域。笔者以为,上述提到的卫生与民族复兴关系的建构与想象也同样是一种近代中国身体国家化的重要表现,这显然是黄金麟先生所忽略的。
现代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作为商品的卫生保健
对于近代上海商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新的关注点。可是,对于近代上海消费文化仍然缺乏整体性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商业文化与生活方式研究中提及消费文化,当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忻平先生的研究指出,在具体的生活消费中可以看到20 —3 0年代上海人对新生活的理解、追求与新的生活方式的创造,也展示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性的张扬,这一切都体现了一种对现代生活方式的理性的本能的选择。他通过对于上海人具体的日常生活消费的研究得出20— 30年代上海人消费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1)新的俭奢观。即上海人对消费的俭与奢认识渐趋稳定,个人均按照自己的收入与对生活的经历及前景的预测来决定生活的态度与消费的方式和程度。(2)上海人的消费已从低层次的单纯生存所需上升到体现自我价值与张扬个性的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了,并成为一种主导潮流。他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它为我们理解近代上海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乃至上海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视角。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研究超越传统的经验性论述,而是通过对于当时上海不同阶层人口的收人水平以及日常开支的具体分析得出的。忻平先生的研究也注意到大众传媒对于推动这种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作用,可是并没有展开讨论。这里将通过对于当时的医疗卫生广告的分析,试图说明广告如何通过对于产品的言说加强卫生保健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这些广告论述中,卫生保健被商品化和符码化了,因为对于医疗卫生产品的消费不仅能带来身体健康,同时还能带来一种新的现代生活方式。
通过广告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这种新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向往最集中地体现在对于美好幸福家庭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医疗卫生广告不断地通过一个个幸福的家庭生活场景来向消费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希望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就必须购买它们的产品。以《良友画报》上散拿吐谨延年益寿粉(德国柏林华发大药行制造,后改名为德国荷兰华发大药行)的三则广告为例,我们就能够看得更为清楚。
(1)如欲新精力与新健康,请即服德国制造散拿吐谨延年益寿粉。快乐家庭之基础。家庭之快乐,基乎夫妇之健康。但现代人事日繁,身心劳悴,以致脑力容易消耗,精神欠佳,肝火太旺。每因细故,使夫妇间爱情冷淡。故欲使家庭快乐,必须战胜此种衰弱情形。欲战胜此种衰弱情,唯有连服正真补品,即散拿吐谨……散拿吐谨,在短时期内,可使君身体健康,青春长旺。
(2)如欲新精力与新健康,请即服德国制造散拿吐谨延年益寿粉。个人康健已是乐事,合家康健更觉可喜。康健乃人生至宝,个人康健,享尽人生之乐趣。合家康健,享尽天伦之乐趣。君欲使个人与合家康健,请即遵从千万热心服用散拿吐谨者之忠告。
(3)如欲新精力与新健康,请即服德国制造散拿吐谨延年益寿粉。保君府康健,驱除一切病魔,品妙健康保障。疾病为人生之劲敌,不独减少愉快,且能促短生命,惟有健康,方可与之抵抗。强健之道,不外补脑与益血,近代物质文明,人事日繁,吾人用脑尤多,每营养不足,神经衰弱,是故补脑实为第一要事……服散拿吐谨,可于短时期内,使神经增强,重享青春之康健,而对于病后复元及孱弱儿童,更有反弱为强之惊人神效,已经全球二万五千以上名医试后书面证明。
通过上述三则广告的文字与图片内容我们可以暂时做以下分析。首先,像散拿吐谨延年益寿粉这样的卫生保健品不仅能够带来身体健康,同时它还是幸福的家庭生活的基础。在这种广告论述中,健康被作为一种促销手段被消费,同时它还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被潜在的消费者所想象。其次,通过广告图片上的家庭成员的穿着,我们可以发现代表传统的旗袍和长衫与代表现代的西式服装既形成鲜明的对照又看上去是那么的和谐。其实,这正好论证了李欧梵先生所说的,上海的现代性并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现代中包含着传统。第三,在广告的影响下,当时的上海人形成了一种超越商品物质性之外的符号意义的消费。最为典型的就是崇尚洋货的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西药、西式保健品、外来肥皂的消费以及中药西药化实际上都蕴含了对于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想象与向往。这种符号消费完全是广告塑造出来的。所以说,广告在消费文化的塑造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而当时的上海企业家就具有非常敏锐的广告意识与高超的广告手段,就连外商企业都望尘莫及。上述提到的高家龙先生关于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的广告策略研究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卫生保健之于现代生活意义这套论述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那些具有现代西方医疗卫生知识的社会精英通过以报纸和传单(当时的医院与药房都会相应地出版有关卫生和健康指南)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工具强化了这种知识并影响到大众。正是这样,上海的企业家、以广告为代表的现代传媒与那些有着相当医疗卫生知识的知识分子都有意无意地为现代性做广告,借此促进了上海消费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建构。
结语:民族国家、日常生活与中国现代性
什么是中国现代性?如何反思中国现代性?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着那些致力于探讨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学者。在本文中,笔者自知无法对于这两个问题做出解释,而笔者试图要表达的是本文对于医疗卫生广告的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两个问题提供一种参照。
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内容。而这个结论的得出也基本上是基于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分析。学者们最乐意研究的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父——梁启超。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便成为学者们的主要分析文本,便以此认为,梁启超的国家思想经历了传统的“天下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转变过程。就这样,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精英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民族国家的知识论述体系,而这种论述体系一直宰制着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讨论。而近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甘阳先生指出,无论梁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20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 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梁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家” 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
对于这个观点,笔者并不赞同。从上述关于医疗卫生的广告言说中,我们不断地看到对于民族国家的诉求与想象,看到卫生对于建立一个现代独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不过,本文的意义并不在于通过医疗卫生广告来论证中国现代性的这套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主流话语体系。而是试图思考当某些类型的话语体系相对于其他话语取得优势乃至主宰地位并合法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其他维度。通过医疗卫生广告对于促进现代生活方式形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性的其他面向,那就是对于日常生活的物质与精神世界的需要与欲望。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但是,由于这种需要与欲望在亡国灭种的独特历史场景下,被以救亡与启蒙为中心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所压制。
那么医疗卫生广告在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又扮演着什么作用昵?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一方面它强化与传播了社会精英分子所倡导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知识论述;另一方面它又为现实生活中近代中国无法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残酷现实(即使有国家存在,但是也未能真正独立与强大)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暂时舒解了中西冲撞下中国处于下风的失落与紧张心理。而从日常生活来看,广告不仅刺激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物质文化乃至都市快感的欲望,同时也为那些无法真正消费这些物质文化与快感的人提供一种想象的空间。
本文选自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出版。作者授权东方历史评论转载。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