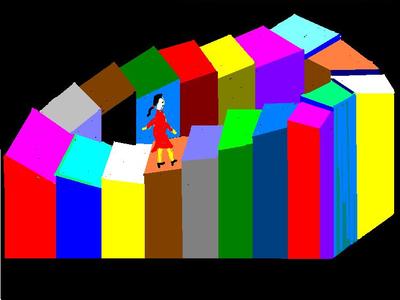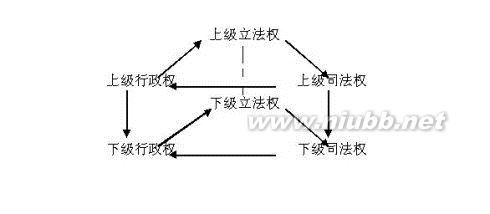1
我承认,我是个俗人,识人先识脸。
也曾看不起“以貌取人”这样的行为,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却愈加相信“以貌取人”自有它一定的道理。
生活中,我们形容一个人“面相和善”,不过是他传递给你一种舒服、亲切的感觉,与之交谈,如春风拂面,暖人心窝。
在我不长不短,二十几年的生命轨迹里,就有人给我的心灵,播撒了这样一颗种子。
2
那是幼年时期,我还住着四合院的矮小平房,那时候,隔壁有一位特别的奶奶。
奶奶独居,有个孙女,高挑漂亮,在外学芭蕾。那个年代,提倡保守与节俭,美丽不被看好,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说成庸脂俗粉、思想腐败,似乎任何对外昭显的美都成为一种罪恶。
纵然是那样的时代,奶奶却活成了特立独行的存在。
自有记忆起,只要是晴日,我总能在微弱星光的晨曦里听到遥远而悠扬的曲目,揉揉眼睛,就看到奶奶在小院里练太极。
那时候的奶奶,头发半青半白。待她练完拳,我也醒了,戳在门口望着她。
那时候的奶奶真好看,眼睛像挂在天上弯弯的月牙,明媚着动人的光彩。
3
奶奶从不对自己的容貌懈怠。她每天换下衣服,认真清洗自己的脸,在斑白的鬓角抹好油,擦上孙女从上海寄来的雪花膏,穿合身的绸缎衣服,提一个竹篮,去菜场。
每到这时,总会招来闲言碎语,女人们聚在一起耳语交接:“六十好几的人了,穿那么好看去菜场干吗?给咸鱼铺子看啊?不害臊……”

她总是不慌不忙地走过,微笑着向她们点头,而女人们只是尴尬地咧开嘴角。
我想她不是不知道,只是不以为意。
一次,我玩得一身泥,敲家里的门,无人回应,忘了父母还没下班。
一瞬间,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跌坐在台阶上,抠着手里的泥巴。
奶奶像是听到了我的叹息,推开窗,探出脑袋,“阿琼,到我这来吧。”
那是我第一次到她家,一进屋,就被震撼到。
洁净一新的地板,错落有致的家具,我甚至找不出一点儿灰尘。奶奶披着毛绒小毯招呼我坐下。
我忽然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忸怩地站着,看着自己脏兮兮的鞋子和满手泥,摇了摇头,“不,奶奶,我怕给你弄脏了。”
她扑哧一声笑了,半弯着腰,“傻孩子,那你实在怕弄脏,我给你洗洗吧。”
于是带我去洗手池,打开水,我冲了个干净,正打算甩手,奶奶给我抹上香皂,搓着我的手,柔声道:“要记得用香皂,去去指甲里的细菌,这东西吃进了肚里,会长虫的。”
我问奶奶在家做什么,怎么不像院里其他女人跟鱼似的窜来窜去。她笑着指了指茶几上摊放的书。说年纪大了,眼力不好,戴上老花镜好些工夫才看得完一本书。
说罢,她问:“阿琼,五年级了吧,喜欢看书吗?”
这一问我怔住了。每天,回家写作业,我心里惦记的都是动画片里的小人,哪还有心思沉下来看书。
我不由得低下了头。
奶奶像是察觉到我的低落,拉着我的手,不紧不慢地说:“我怕不看书、不学习就跟不上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我每天练拳,打理容貌,也是提醒自己的身体,还活在这世上。
既然活着,就应当不只是活着。要记住,读书以明智,好的书本和文字能涤荡一个人的心灵。”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记住了那句“读书以明智”。
4
几年后,我上中学,奶奶也随孙女搬去上海,再往后,我离开小院,住进了四方的楼房,我没有再见过奶奶,可她的音容笑貌,时至今日,都不曾让我忘怀。
成年后我才明白,她教会我的除了待人的谦卑,谈吐的优雅,还有,饱读诗书,丰富内心之后,它们投射在你容貌上的善与美。
这种美绝非浮浅的美丽,它是一个人剥离了外表之后的素养,是放在浩瀚人群里也能一眼分辨出的气场。
都说,内在的涵养和思想,能够潜移默化一个人的容貌。你是戾气缠身,还是和颜悦色,其实,都能从容貌中略知一二。
因为,你的脸就是你灵魂的模样。
5
我看过在酒堂饭店对人颐指气使的食客,他们喧哗不已,毫无礼仪,吃得饭桌上、地下无处不及,更是对忙碌的服务员呼来喝去,纵然穿金戴银,美艳精致,可这样的灵魂,如爬满蛆虫之恶。
我还看过精致优雅的法国女人,她们一生在学习与保持美丽。从不认为“美貌”只可赋予年轻的生命,她们相信 “不管我活到什么岁数,一定美丽到老”。
以貌取人,取的是什么?
是你的内在,在岁月的沉淀下交付给外在的容貌。
一个人的面容,先天的遗传不可逆转,但内在的气质和涵养却得以在后天的培养中逐渐打磨光整。而容貌终将随着气质变化而发生变化。
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体恤对方,推己及人。这何尝不是一种高级的修养。
所以,我相信一个自持修养,精致律己的人,他的容貌不会太差。而事实证明,我接触了大部分这样的人,确也如此。
同样,一个对自身容貌都疏于整理的人,我不相信他的灵魂能高贵到哪里去。
庄严地爱着自己,与年岁无关,在有限条件下依然悉心打理,并能对这个世界抱有最初的善念,就是一种美。面相即心相,相由心而生。
以貌取人,取之有道,我所希望的,就是你的灵魂对得起你的美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