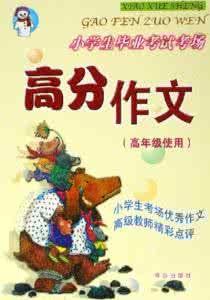除夕,好想对文字说说话。
不言媚众的、应景的、概念式的话。只说心苏醒了,拔节了,由黄泛绿了,你看。你听。
窗外,游人稀了,私家车少了,孩子们多了!街上,鞭炮噼里啪啦,燕雀儿从这边的电线杆飞往那边的楼台上。习惯了,也平然多了。
阴郁了多日,天上,也不见半个雪片儿筛下来。一个人的屋子,一颗心,幽幽,空空,寂寂。喧嚣之外,时间默默地流淌。然,惊了心,扰了魂。
这是头一回在他乡过年。安静得有点后怕。怕午夜的鞭炮轰鸣。怕拂晓打开门,突然间涌了一屋人。
老家的除夕,女子转锅台,男子忙院落,孩儿骑上竹竿逗乐儿。等对联贴了,灯笼挂了,开始走家访户了。哥儿姐儿的,围成圈儿包饺子,唠一串儿土的掉渣的嗑。似乎走进了相声里,争相“丢包袱”,傻笑。只等着子夜,炮竹声声辞旧岁了。
年初一,大早就起床了。争先恐后地洗漱。后在院心摆好方桌,献上枣馒头、麻花、苹果,毕恭毕敬地上香、敬酒、念诺儿。那一刻,时间、空间、物质就忽然里归于了寂静。仿佛已故的亲人都来了,聆听着,将祝福听成一朵莲花了。
那一刻,你知,我知,硝烟味儿知。
最后,大年的节目像早就彩排好了似的:燃烟花,拜年,爆年景。壮心,托起了冬日暖阳!
下午眯瞪了会儿,醒来,闪念出小我两岁的琴来。她是大侄女,两小无猜大的。不知在外忙碌了一年,返乡了否?正想着,电话响了。是琴!
于是,手牵手的画面扑来,心情飞了。

记得过年,或走亲戚或看戏,都小手儿牵着,宛若一对小兄妹。记得下雪天,一并看雪,听树桠上窸窸窣窣落的声音,眉间都皱成了雪的样子了。那时光,悠长,凉薄,却温暖……
记得上大学那年冬的配眼镜,琴陪我。天朦胧,寂无声,即使一丁点的响动,也惊得汗发直竖。到时已中午了。琴在外看自行车,我进了眼镜店。出来时,琴气咻咻说:刚才有个人赶我走,说我叫花子,真可恨!琴穿的是漂染的格子粗布衣,打了补丁的,脸儿冻得红扑扑,像《白毛女》的喜儿。我又气又急,直骂城里人是狗眼看人低,王八蛋!又哄她,大了,小叔给你买好衣料。可几十年过去了,琴倒是成了老板,穿金戴银的,富甲一方。
电话中,她叔长叔短的,亲近和儿时一样。
一恍惚,依稀走回了儿时,来到了小村旁。看见了家。
然他乡,永远不会是家。家,应该是尊卑有礼、长幼有序的心心相守的地方。而非一声“彼此彼此”,似近却远、熟悉却陌生,不知所谓的笑。家,有古朴的巷道,熟悉的方言,有鸡鸣狗吠,而不是洋楼普通话。家,是生命扎根的地方,是冬天里的童话,是梦的住家。
无论天涯海角,说你想,就想;说你在,便在。家装在背包里,烙在心上。
年前,因故回了趟家。办完事,给母亲烧了些纸扎的家什。www.250rz.com坟头,看草枯风凄,不禁悲上心来,念碎碎:妈,我在上海挺好的,信或不信,都跟去看看哪,也就安心了……
之后,就常梦见母亲。更有一晚,爷爷、奶奶、二叔、三哥都来了。其实今生从未见爷爷、二叔的?母亲笑着,不语,流溢着浓的化不开的温柔。妻说她也梦了,想必是母亲真的来了!我说妻,既然妈来了,就得和家里过年一样,蒸煮炸一样儿也不少。
明天,要一早上香祭祖,给母亲叩首。我知道,有诸多亲人在,我的心就是一朵盛开的莲。
——毕竟,四世同堂了!
除夕,一个人的屋子,幽幽,空空,寂寂。但心暖且柔。因为有亲人在。有文字,你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