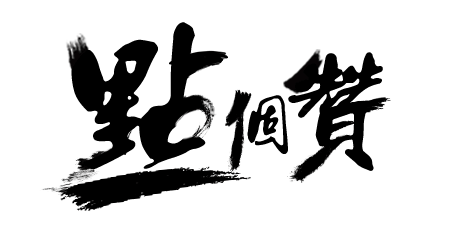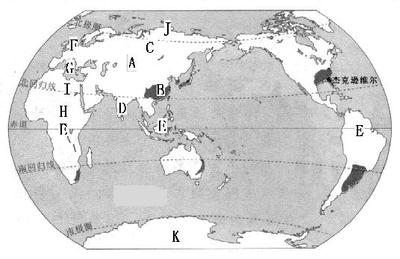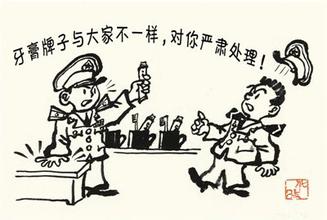所谓思维,就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发现我们所做的事和所造成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思维有两端,反省前的情境,即一个迷惑、困难或纷乱的情境,产生思维必须解答的疑问;反省后的情境,即一个解决了的问题,疑难情境的消除。思维就在这两端间进行。所以,“反省思维的功能在于,将经验到的模糊、疑难、矛盾和某种纷乱的情境,转化为清晰、连贯、确定和和谐的情境。”即思维从疑难的情境趋向于确定的情境。在这两端之间,思维有以下五个形态:“(1)暗示,在这里,思维跃进于一种可能的解决;(2)感觉的(直接经验的)困难或迷惑的理智化,成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一个必须找到答案的疑问;(3)用一个又一个的暗示,作为领导观念或假设,以发起和引导观察和其它心智活动,搜集事实材料;(4)推演观念或假设的涵义(推理,指推论的一部分,不是推论的全部);(5)在外表的或想像的行动中检验假设。”杜威进一步指出,五个阶段的顺序不是固定的,可依具体问题具体选择操作策略。“五的数目,原来也没有什么神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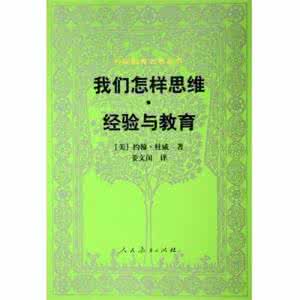
关于教学,杜威认为持久地改进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唯一直接途径,在于把注意集中在要求思维、促进思维和检验思维的种种条件上。思维是有教育意义的经验的方法,因此教学法的要素和思维的要素是相同的。即“第一,学生要有一个真实的经验的情境──要有一个对活动本身感到兴趣的连续的活动;第二,在这个情境内部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刺激物;第三,他要占有知识资料,从事必要的观察,对付这个问题;第四,他必须负责一步一步地展开他所想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五,他要有机会通过应用来检验他的想法,使这些想法意义明确,并且让他自己去发现它们是否有效。”
杜威认为,在学校里,学生思维训练失败的最大原因,也许在于不能保证象在校外实际生活那样,有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因此,他的方法论中,活动居于中心地位,儿童中心实际是儿童的活动中心,因为,没有活动就没有经验,而联系活动与经验的桥梁则是思维,反省的思维,所以他特别主张从“做中学”。在《我们怎样思维》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教师,看到学生做小数乘法,小数点放错,不知怎么办,数目是乘得对的,但是数值全错了。……这个结果表明,学生虽然算对,但他们并不思考。因此,他派学生到一家木行去买手工工场所需的木材,预先和商人约好让他们计算货价。数的运算和教科书里的习题相同。小数点全没放错。”杜威不仅主张学生在做中学,而且要求教师要参与到学生的活动中去。这种教学,教师不是旁观者,而是共同参与者。在这样的活动中,教师成为学习者,学习者也是教师,无论教师还是学生,愈少意识到自己在那里施教或受教,教学也就达到了愈好的境界。
杜威的教育思想涉及的教育问题非常广泛,这里只做了选择性的介绍。杜威以儿童为出发点,以民主社会为归宿,在广泛吸收历史上诸多教育思想家的教育思想之基础上所创建的博大精深的教育理论,喊出了其时代的教育最强音。他是继卢梭之后,又一个以关注儿童的天性,发展儿童的个性,解放儿童的身心为主题,向压抑儿童,强迫儿童的传统教育坚决作战的勇猛战士。他以现代教育的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挑战传统教育中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的思想;无疑具有片面的深刻性,影响久远。他不仅理论上建树颇多,而且亲身投入教育实践,创办实验学校,推行他的教育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有众多的思想追随者,他们所发展起来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当时的美国乃至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的上半叶可谓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从20世纪30年代起,批评之声就由所谓新传统教育派中发出。特别到了1957年,苏联卫星事件给美国朝野带来了强烈冲击,人们把美国教育的落后归咎于进步教育,归咎于杜威,使其失去了教育理论界的统治地位。美国的教育经历了60年代的培养天才后,70年代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教育的发展处于一个反省的时期,提倡回到基础学科,之后从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的世界教育改革中,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可见一斑。全面的评价杜威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过,历史已经并将继续做出最好的回答。
——摘自诸惠芳:《外国教育史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分类:教育理论:传承与创新 | 评论:0 | 浏览:772 | 举报 | 收藏转发至天涯微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