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诗词创作,先得明白什么是诗。我所服膺的理论,是以“释”释诗的——人秉七情,应物斯感,为之困惑,为之兴奋,为之辗转反侧;必得释而放之,而后归于恬静。借助语言的释放,便产生诗。《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要义是说,诗是情志的释放,释放的形态是语言,其作用首先诉诸听觉,有节奏有旋律,故诗、乐、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汉儒的这个见解,非常高明。
因此,诗词创作话题虽多,我以为首要话题有三个,就是:兴会,语汇,韵律。
一、兴会
一位英国小说家说过:“若无创造性情绪,才气和技巧不会有多大用处。但这三者加在一起,你可以创作出震动世界的小说。”(戴安娜《小说写作技巧》)诗词既是情绪释放的产物,就更是这样了。西人云:“诗始于喜悦,止于智慧。”所谓喜悦亦即兴会。兴会也就是诗人的创造性情绪,是诗词创作的原动力,又称灵感,兴致,兴趣。陈衍《石遗室诗话》云:“东坡兴趣佳,每作一诗,必有一二佳句。”便是说东坡饶有兴会,故每作必有佳句。
毛泽东云:“诗人兴会更无前”(《浣溪沙·和柳亚子》),《词六首》发表之初,亲加按语云:“这些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足见兴会之高;“年深日久,通忘记了”——释放即是发表,未更想发表;而“人民文学编辑部收集起来,要求发表”——刊用是第二义的发表;“因以付之”——要发表就拿去发表吧(对作者说来无关紧要)。这是什么状态?这是什么风度?这是诗词创作的状态。这是真正诗人的风度。
兴会并非空穴来风。兴会来自独特的生活阅历、独到的生活感悟以及新鲜事物的刺激。有此,纵无心插柳,亦能成荫,故“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郭沫若《鲁迅诗稿序》)。时下作者,或昧此理。我曾收到家乡一位老同志寄来的“请教”的词稿,有一首《沁园春》,是为县师范建校五十周年改为职业中学而作——事属沧桑,加之作者对该校非常熟悉,半个世纪的人事变迁、人情反复,或美好或悲怆的记忆,作者应有兴会,所作应有可观。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抛开了独特阅历、独到感悟不写,而去写一个浅显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这所师范学校五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多少人才。尽管形式中规中矩,却成为公共之言,不成其为诗词。这个例子很典型,——时下不少人就这样“不在状态”地进行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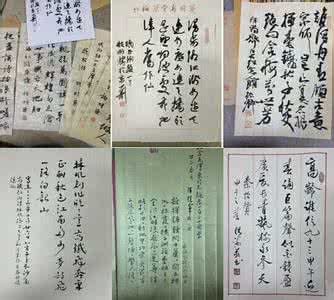
不在状态是因为没有兴会。不在状态,写出的东西就索然无味,不是真诗(更不用说好诗)。宋谋瑒先生感喟过:有些人写了一辈诗词,却不知道诗味是什么。知堂老人辛辣讽刺过:没有灵感而做诗,就像没有性欲而做爱。不幸得很,这样扫兴之事,在当前诗词创作领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沧浪诗话·诗评》)空间开阔,万象新奇,不但皆供诗材,尤能激发思绪。唐人郑綮自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故诗词作者理应走出门去,面对社会现实,接触新鲜事物,增添生活情趣,开拓诗词题材。宁肯写得少点,但要写得好点。切莫仅凭年年都有的那些个纪念日、喜庆事,闭门造诗,那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黑毛猪崽家家有”,也必然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元好问《论诗》)。
二、语汇
作为语言艺术的诗词创作,仅有兴会是不够的,还得有词儿。没有词儿,就会茶壶里装汤圆,肚子里有,却倒不出。词儿——也就是语汇。不少人动辄侈谈意境,却很少注意到语汇。事实上,不有语汇,成何意境!“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毛泽东《送瘟神》初稿),与“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定稿),两字之易,意境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措语使然也。
诗有言不尽意,然无言更不能尽意。诗词语汇之贫富,及表达之流畅与否,决定了诗歌的可读性和耐读性。小说家说,只有一个名词,只有一个动词,只有一个副词,只有一个形容词,才能准确表达一个意思,诗词也一样。在你的语汇贮存中,永不要缺少那一个词儿。语汇丰富与否,永远是衡量创作水准的重要尺度。黄庭坚道得好:“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其要义是说,诗词语汇大体的分类有二,一为“自作语”,一为“来处语”。
“自作语”即不含故实的语汇,钟嵘例举“思君如流水”(徐干《室思》)、“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诗》)等句即是,不过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序》),一个“皆”就把话说过了。“自作语”在出口成章、兴会绝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出彩,唐人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即一例。南宋杨万里笔端有口,亦多此种。当代诗如“昨夜洞庭月,今宵汉口风;明朝何处去?豪唱大江东”(熊亨瀚《途中》)、“吃饱今朝好插秧,半锅马料(指油箍)作人粮。老妻花上还添锦,三个田螺做碗汤”(熊鉴《插秧》)、“未可轻看三点水,奔腾欲涨洞庭涛”(杨起南《赠湘乡书法协会》)、“杏坛总是向阳地,桃满春原李满林”(雍国泰《赠李满林》)等,俱是佳例。
“自作语”说是自作,其实也有来处——即生活。因为是首次用于诗词,故称“自作语”。过去有一种误解,认为黄庭坚反对“自作语”,其实不然。黄是尊杜的。元稹对杜诗,即有“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之赞叹。今值信息时代,新词层出不穷,而良莠互见,虽不可照单全收,然披沙拣金,亦往往见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代作者,多有尝试。聂绀弩诗云:“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钟三四清归》),上句全用杜诗,下句则以时髦语加国骂对之,对得字字工稳,故愈俗愈雅。“愤青”一词,不经不韵,而滕伟明诗云:“知青有典故,愤青作何讲?邂逅实偶然,得之因特网。”(《愤青》)从语源措手,拈来自然巧妙。拙作《竹枝词》云:“峨眉自古路朝天,最是公来不封山;半边容我与君走,尚与路人留半边”,熔裁邓小平语“我们是游客,人家也是游客,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也是“自作语”。非经作者注释而不能明了之新词,即落第二义。生造词语,则是应该尽量避免的。总之,“自作语”要望文知意,到口即消,融古今于一炉才好。“自作语”虽信手拈来,却不一定皆成妙谛,故黄庭坚说“自作语最难”。
“来处语”即来自书本的有出处之语,是作者博览群书,含英咀华,从典籍汲取或熔铸的语汇,是读书受用的结果。运用得当,可使人于字面之外,结合语源,产生更多的联想,事半功倍,故古今胜语更多。诗词作者须多读书,多贮语。昔人称饱学为“腹笥甚广”,意思是读书多、语汇贮存量大,故语言能力强。南宋辛弃疾作词,《论语》《孟子》《诗序》《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汉书》《世说新语》《文选》以及李杜诗,都是他措语的源泉。一旦激情奔放,便觉古人于笔下奔命不暇,安放无不如志,无不切贴。功夫不到,即成“獭祭”(或称“掉书袋”)。“来处语”运用之妙,在于惬心贵当。陶先淮《赠何诗嫦赴美留学》:“中华自古擅风流,岂让欧洲更美洲?碧海青天凭寄语,嫦娥灵药不宜偷。” 诗劝人学成归国,后二句语本李商隐诗,以“嫦娥”切诗嫦,尤臻语妙。
年前李敖来大陆,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说:“你说这是女孩子,那是老头子,这不是最好的中文。你说这是红颜,那是白发,这是最好的中文。”他所谓“最好的中文”,其实是指诗词语汇中的词藻,藻绘。藻绘的作用是好看。王实甫《西厢记》二本一折《混江龙》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王季思注云:“意即金粉香消,精神清减耳。六朝、三楚,不过借以妆点字面。好看而已,不可落实。”藻绘妙在点缀,忌在堆砌。过犹不及,令人生厌。李白“莫使金樽空对月”、王昌龄“无那金闺万里愁”等,最为得之。当代如聂绀弩《刨冻菜》:“千朵锄刨飞玉屑,一兜手捧吻冰姿”,亦有新意。
三、韵律
诗词是诉诸听觉的艺术,因而有韵律的追求。诗有内在韵律,有外在韵律。内在韵律指的是诗中情绪的消长,本文姑且不谈。外在韵律主要指诗词格律。毛泽东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致陈毅》)吾师宛老(敏灏)戏云:“写《西江月》如不合律,不如改题《东江月》。”要之,近体诗词应讲求格律,是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关于平仄的划分,到底依据古典诗词,还是依据现代汉语?在普通话中,入声字已分属四声,归属阳平者尤多,如何认定其平仄?主流的办法是率由旧章——即保留入声字,仍归仄声。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仅仅因为好之乐之者,对入声字并不陌生,“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张爱玲语),若把入声字作平声用了,不用留神,也会刺眼;而且因为在不少方言区内,入声字依然活在人们的口头——如果不理会这一事实,就会顾此失彼,进退失据。
另一个问题是,诗韵分部太窄,用韵要不要放宽?我的看法是要。放宽用韵,要不要有个限度(标准)?我的看法还是要。以表意为主的汉字,其读音不仅有古今之异,而且有地域之异。用韵问题,古人已觉难办,因此才制定了诗韵、词韵,让人依从。
当代诗词创作用韵,不外有三种办法,一、凛遵传统诗韵、词韵,二、将诗韵放宽到词韵,三、从当代口语取押。我看前两种办法都行得通,而“当代口语”——如果指的是普通话,就牵涉到入声字问题,从而也就牵涉平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弄不好会自乱其例。宛老说:“予既主张从当代口语取押,或混合诗词韵而从其便。但自作则仍依《佩文韵府》及《词林正韵》等,畏人斥为不知韵也。”(《晚晴轩诗词选序》)这样主张从宽、操作从严的作者,在当代诗词创作中远不止宛老一个。
后代诗词作者都是受古典诗词沾溉陶育的。没有一定量的古典诗词垫底儿,在创作资格上就存在问题。古典诗词的根基和积淀非常雄厚,传统观念(平仄以及诗韵、词韵的观念)深入人心。好之乐之者,对诗韵、词韵的认知,一如对入声字的认知,是不成问题的。在一位挚友寄来的诗中,有句云:“吾幼嗜读太白诗,太白诗夺造化功;诗笔雄奇呈五彩,掷地铿锵响有声”,诗意尚可,惟独用韵令人感到不对劲、不习惯——“功”“声”二字在诗韵、词韵中均不同部,连邻韵都算不上。而邻韵(如“江”“阳”)的通押,是没有扞格之感的。词韵大体是在诗韵基础上,对邻韵进行合并的结果。所以,将诗韵放宽到词韵,倒是顺理成章之事。若再要放宽,也得有个规范——我看不妨以《诗韵新编》为准。此书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邀请了上海文史馆七位馆员协助编纂),1965年初版后,多次重印。这是一本依据现代汉语,而又区分了入声字的新编韵书,经过时间检验,证明非常实用。
韵律,属于形式范畴。形式,毕竟是服务于内容的。所以一时兴到、当下成诗,偶尔出韵也使得,如毛泽东“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虽出韵,感觉不坏。不讲平仄也使得,如吾乡毛良行先生《自遣》诗云:“不愿无来不愿有,但愿长江化为酒;日夜躺在沙滩上,一浪浪来喝一口”,此诗看似颓废,其实表现出一种顺应自然、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四句一气流转,纯乎天籁,风度绝佳,一听就记得住,忘不了。我觉得它比唐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自遣》)之类浅派诗还好,至少是毫不逊色。虽不讲平仄,谁不以为然耶?不过,倘没有如此酣畅的兴会,不得援以为例。
(原载《岷峨诗稿》2007年夏,总第84期)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