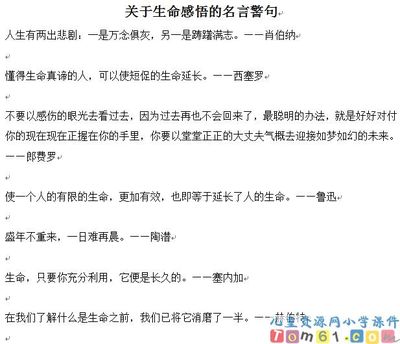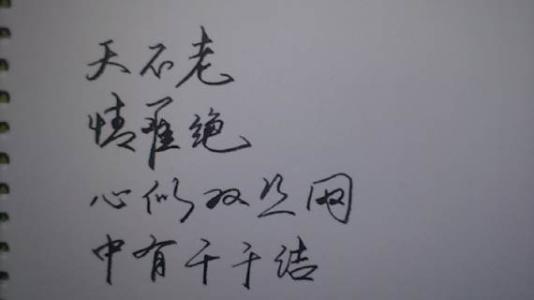诗歌 ‖画春光
作者:芷妍
突然
云影开始在湖面上行走
薄冰炸裂的声音清脆欢快
我站在你的眼睛里
一团团迷路
跌入阡陌纵横的田野
大片的金黄色在身上跳跃
瞬间桃之夭夭
春水喧闹
恰一个转身的急流
就是你在笑
我原本爱这世间所有美好的男子
突然
一下子小性儿
只爱你沉默辽远的深情
雨落钟声
惊蛰 春分,一路低眉
雷声新绿
雨丝有些懒
各色枝条闭目双掌合十
小学校停电了
下课铃变成钟声
敲钟师傅拿着榔头
依然带着他的迷彩帽子
白发从帽檐下撇出
从操场这头走到那头
没有撑伞
钟声弥漫
从佛经遗落
把春天绾个结
画春光
一朵花,涨满了蜜汁
无数的花,涨满了蜜汁
一定有船儿在蜜波上行走
有欸乃的回音
迟暮的云雨临幸山川湖泽
我在一根针里开花
整个春天的妩媚都是用来相遇
你说,春天我要和你寻欢作乐
那我就坐在春风里
等你拉我的手
万物生
灰色在大风里飞
喧闹的寂静匍匐
黄土流沙从善如流
![关于徒步春光的诗歌 [诗歌]画春光 ‖ 芷妍](http://img.aihuau.com/images/e/76886/1420060408144821924624.jpg)
勾起殷红的指甲
一切恰好
恰好 一半是飞扬跋扈的色厉内荏
一半是媚眼颤栗的樱花
太初有道
神说:要有光
无数细小的庞大的子宫开始喜悦阵痛
无数细小或庞大的精灵星夜兼程
只待一朝分娩
半糖
我的口袋里只要半块糖就好
不用太甜
还有一世孤单呢
那是时空里一粒尘埃小巧的黑
我背对着春风
北方的春
阳光淡
风声薄
如远去的故人捡拾不起
恰好是我三十岁以后低度浅白色
我背对着春风
穿过我的长发,风衣
曾经执念
如今就像医院洗干净的旧床单
安静的躺在病房里
一切都轻飘飘的
透明的在风里飞
睁着春天的媚眼
湖水推开远山隆起的小腹
我背对着春风
烟花的果实
我猜到
这些果实来自烟花
你只爱我瞬间的凌波微步
如我怀里揣着白玉兰,牡丹,或者樱花
我在陌上行
迎面有你逆 流而上的喜悦
你却看不穿我的透明
我在风里燃烧
我也安静如灰
交叉而过的眼神
不能编织经纬
烟花的果实 正是恰好
倒垂的风筝
阳春三月
季节颠沛流离后
开始休整的光阴
白玉兰花种在天空里
世园会建设的各种新场馆已经收尾
满天风筝自由的笑
远远的成了一个个黑点
想追溯天空的源头
清洁玻璃幕墙的工人们腰里系着绳子和小桶
风中摇摆
远远的也成了一个个黑点
他们是春天里倒垂的风筝
紧张
早晨的阳光从树上筛下来
沿墙壁匍匐下行
浇灌着墙根下几个老人
只要是晴天
他们就坐着马扎或轮椅
下棋,说话或者发呆
几乎都戴着灰或黑的帽子
阳光硬着身子挤进额头的皱纹和昏黄的眼珠
墙角小草胆怯试探早春的底线
好像怕惹出一个江南来
他们在这里切出一半的明确
等午饭时间
等晚饭时间
还等什么
每天晚上下班再经过时
只有夕阳把树影安放在墙壁上
墙根下空荡安详
总让我心里紧张一阵
痣
老公脖子后面中央有一颗痣
点掉了
后来偶然在网上看到几句
脖子后面正中有痣的人
没有喝下让自己忘记前程往事的孟婆汤,
今生带着标记来寻找前世情缘未了的人
我说
老公,你的痣点掉了,是不是就把我丢了
他说
已经找到你就不需要了
醒来
午睡醒来
习惯坐在藤椅上发呆
好像与前世的自己再次重逢
尽管我只与我分离了几十分钟
炉火中香已燃尽
灰渍在动荡的烟雾中返璞归真
白日梦是青铜色
一场古老的花事
繁花如设想的前程如锦
阳光倚着门楣
折叠进茶杯
一副中年人的态度
茶叶在杯底
和我睡着时一样
下午五点多在北新道上
下午五点多
天暗下来
在北新道上走
踩着白雪 黑雪
路上人群,车子已经看不清细节
剩下红色蓝色绿色白色黑色
和汽车鸣笛声
一柄尖锐潮湿的冬拦路抢劫
像我半生中挑拣出的反骨
不过现在我很少说
太冷了
冻死我了
只是沿着北新道走
天黑前应该能到家
劈开
一刀劈开身体里种了几万年的荒凉
随风飞到田野山坳
埋进今冬的大雪里
等明年享受从头到脚的春光乍泄
窗影
早晨
窗影斜着身子清楚的绣在西面墙壁
中午
窗影完整方正的印在北面墙壁
傍晚
窗影成了软软的菱形描在东面墙壁
春深何处
一夜碎雨
挑落春的盖头
日初晴
花枝摇
影落石上
颜色渐浓
风扫落红处
不知几寸深
新绿的叶
铺开春的战场
一片金戈铁马
害怕
爸爸妈妈饭后聊天
老爸吸烟看着镜子里的皱纹说
“65岁了老了”
老妈说
“是啊,65了
50岁时我没什么感觉
过了60岁就害怕了”
一缕烟圈慢悠悠的飘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