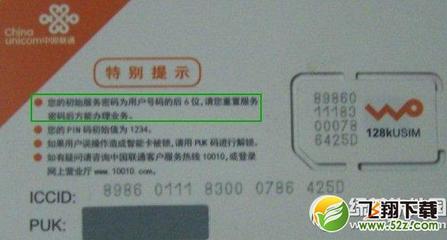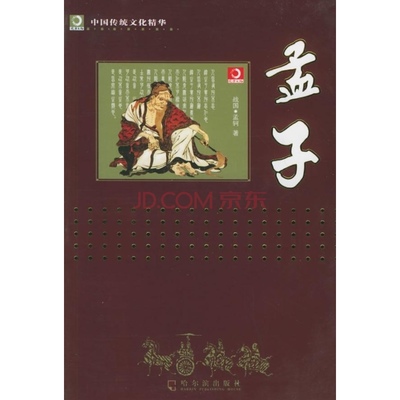明清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情色小说的一个高峰,此时出现了大量后世耳熟能详的小说,无论是文学性还是艺术性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例如作者未留真名只以笔名写下的《金瓶梅》,被不断翻拍成电影的《肉蒲团》,甚至连我们伟大的作家鲁迅都研究过此类文学。
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共鸣,性欲伴随着人类的历史长河从未间断。依照马尔库塞理论,在一切艺术中,性的表现应该是最重要的表现部分,而且它的“艺术性”将是永恒的。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得以流传下来并且对后代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几乎都是情色作品,从产生于西周的《诗经》到唐宋的风流诗词再到元代的散曲戏剧及明清的青楼小说,无不说明这一点。情色文学,构成了中国文学最耐人寻味的一道无法拒绝的风景。
说到情色文学,不得不提到唐代。对后期文学影响巨大的并非是白居易李白杜甫的诗,而是李商隐的无题诗及杜牧等人的浪性诗。李商隐的无题诗极其艳情旖旎,例如,下面这首无题诗就非常入情细致地刻画了一对男女幽会时欢爱的情景: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篷。

宋代重文轻武为艳词留下了丰沛的生长空间。如柳永、晏殊、晏几道、吴文英、秦观的词。像晏殊的“醉折嫩房和蕊嗅,天丝不断清香透”,柳永的“洞房悄悄。锦帐里,低语偏浓,银烛下,细看俱好”,横看竖读,都是情色。秦观曾因一首词被苏东坡称为山抹微云君,而秦观的这首极负名气的《满庭芳》却是相当情色的。如他词中写道:“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这一句,如果用现代白话文翻译一下,没有一二十句,又如何能透出那“消魂”二字。
元朝的元曲也是不甘示弱。如王和卿的一支散曲中就写道:“夜深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那情况,难当。一翻翻在人身上,偌长偌大,偌粗偌胖,厌匾沈东阳”。而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情色描写更是比比皆是。如:“往常时见敷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谎;今日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着小生心儿里早痒、痒。迤逗得肠荒,断送得眼乱,引惹得心忙。”
明清时期,情色小说真正迎来了高峰。明清有影响的情色文学可以列出一长串出来。而明清的情色小说,在艺术上也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及李渔的《肉蒲团》成了许多小说家的研究范本。鲁迅也曾对这些小说做过研究,并将《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花月痕》和《青楼梦》列为四大狭邪小说。
情色文学不仅仅是描写性爱,性爱仅仅是男女的一种沟通方式。情色文学不同于色情文学,色情文学除了写性之外还是写性,写男人,只是一个阳具,写女人,只是一个阴具。男人与女人的联系,就是阳具与阴具两个点的直线联系,它给人的冲动纯粹是肉体的,即时的。
而情色文学,它是把男人的阳具和女人的阴具分散到他们身上每一个部分,并且一直分散到他们各自的心灵中,甚至在他的生活环境中都有所投影。这时候,男人与女人的结合,就不是两个点的连接,而是多个面一个立体的结合。性在他们的生活中,实际上是起了一种沟通的作用。就像一个球一样,男人的阳具在南极,女人的阴具在北极,它们的交融是通过无数条经纬线连成的一个丰富的球体世界。它给人的冲动是心灵的、持久的。现代小说如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杜拉斯的《情人》,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都是现代情色文学的典范。
无论何时,性爱都是永远存在于人类中的。性爱是两性中最本质最直接最生命的联系,这就注定了情色文学是文学中最基本的色调,离开了这种基本色调的文学,一切所谓形式或主义的文学,都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