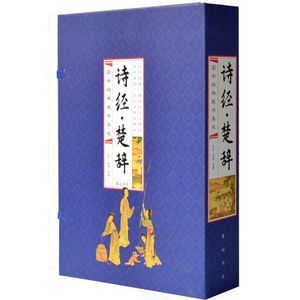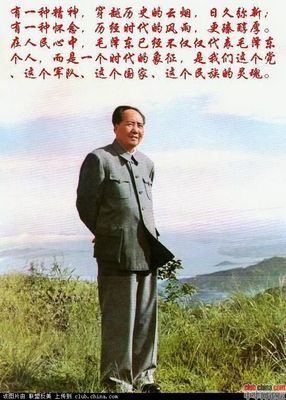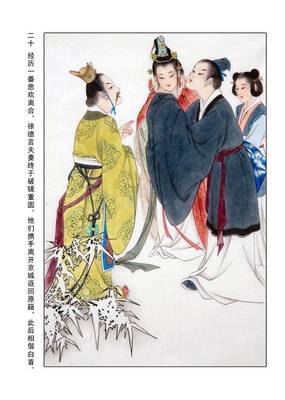贾 柯
史铁生的文字担当了生命不息的寻求者,在此荆途,他将自己置于无边黑夜的状态,诚实听从内心的深隐、细弱、破碎,真实呈现人性深处那潮汐般一脉一脉的微渺、变幻、莫测。与此相对,那些途中以神灵之姿宣告人生是非答案的人是多么盲目、轻浮、无知。洞悉生命,也许只需耳朵贴近内心,在寂静中倾听。
对美人容颜的工笔描写一向生不出兴趣,如手若柔荑肤如凝脂眉如青山眼如秋水,美得凝滞,卧在纸里没有生命的真气。读到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之句时,却有牵肠之感,当人的容颜与情感、光阴、命运相联,有了真实莫测的颤动、起伏、变幻时,打动人的就不只是眼目,而是叹息着深入心灵的内殿。
“我的生命只需好,不需长。”惊心这句,数日无语。有的文字不是隔岸观火隔水听箫,它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么轻,不想惊扰任何人,又那么沉,让抑结心胸出不得声。为什么?看梵高会蹦出眼泪,读他生命末期的书信,他说自己在用生命作画。语言多余了,一同赏花写爱吧,直到最后一滴眼泪安静落尘。
“呼唤与被呼唤的很难同时呼应。”哈代这句说明爱情就是个概率事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到了徐志摩,爱情更是一场宿命。爱情文字读到生了倦意,生生死死一往情深可以,至少要值得,值得不是数算是自尊,可以谦卑但不必低进尘埃,真的不必。爱在或不在,一个人总要有风有骨地活在那里。
早年,读川端康成晚期的《睡美人》和《一只胳膊》,觉得气息透着些许颓废和轻度变态。现在感觉不一样了,那沉迷感官的老人不过象世上一切的生命物种,繁时已过,战兢地面对着自身的枯萎,对青枝绿叶泄露出的饥渴,恰似落日沉入大地的一刹,有着回光返照的烈焰,那是蕴籍至终的叹息,不舍,世界这样美。
多年前读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觉得那不是小说而是生活本身,某些情节刻骨铭心,有多次没有流出的眼泪,和静默背后的浑身颤栗,那是因为翻阅的文字成了一个引子,直接把自己牵回到了成长期某些沉重得难以呼吸的角落,如同一次还原性的坠落,重新承受一回人性泥沙俱涌袭来时不堪的纠结与苦痛。
真正对村上春树有所感觉始自一事一文,真欣赏他多年钟摆一样坚持长跑,一生里,登一次珠穆朗玛峰是眩目的特立独行吧,而默守四季般数十年对一人一事一物的恒常,那古典的深情更令人倾心。在耶路撒冷的获奖感言《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坚定不移的平民立场和对个人尊严的捍卫,使他站在了精神人格的高峰。
“耶酥哭了。”是整部《圣经》最短的一句,它是饱含人性的神性,没有一丝训诫,没有马上安慰,面对死亡来临的碎裂一瞬,耶酥呈现了他道成肉身的软弱、颤栗、心痛,那一刻,他不在天上而在地上与拉撒路的亲人们一起承受苦难。这眼泪每每滴在自己心中不去拂拭,记得爱并不只救赎、神迹,还在共情同悲。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朱自清《荷塘月色》这样起的头,隔了多年,隐隐记得那文的风物笔墨是工笔细描,但那荷是怎样的美近于忘干净了,忘不掉的竟是开头一句。在想,有时,作品呈现的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有时,或相反,当作者身陷泥淖不得其所,也许借艺术的观照来寻求对现实的疏离,升华,超然。
“乘兴而行,尽兴而返。”一思起王子遒雪夜访戴那份写意、畅快、风神就令人向往不已。生之前,未有人,空空如也,死之后,人不在,如也空空。能于天地行走呼吸倾泪含笑的不过数十年,除却一地碎屑两分纠结三分辛苦……,人能有几刻可堪尽兴?那所有的得与不得,也许真可居其次,有痴念,已足够美。
张岱,一个明末之人,也真真是袭了魏晋风度,短文《湖心亭看雪》,片片净白无一丝余尘,堪奇的是那寂至空无的亭子,竟升腾着炉酒,水泡沽沽,静谧地舒放着浓烈的热度,世间茫然时,最见出三两个痴人。痴,也如冬藏,越是深埋越是生长,只携胸腔跳动的真性情,任雪飞火,火燃雪,自成一界凛冽醉倒。
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更接近真实,这些人不是观念的化身,不担负起简单的善恶身份,每个人都是复合体,内心如同音乐的多声部,会发出几种声音。而人与人的区别,取决于在生命穿越各样情境之时,一念之间,哪一种声音更强,哪一种声音更弱。因此,陀氏的笔不是伸向理想星空,而是直接触及人心海底。
感觉,是第一真实,瞬间的质感只合体会。即使一支最精微的笔,以追风之速,也不过仓促补捉它的影廓。佛语“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真是洞明。可是啊,明知缄默最智慧,听红尘声声依然,春来摇唱烟絮冬往寒述孤寂。世上倒底凡人多,谁又不是呢?偏偏,理设篱笆处,正是,心潮萌动时。
“当下欢喜,一世欢喜。”真是体贴字句。每日,洗脸梳头出门,散发更衣入眠,有什么比肤发更体已的呢?可那发丝如繁星,谁人曾数清?一已之身尚难洞明,漫说什么他年悲欢情?当下这一杯,不思不量,全情饮下,沉醉地归沉醉,清醒地属清醒。投入片刻,便是在与一世交了杯。
“时间可以浪费在更美好的事物上。”不经意读到塔莎奶奶迷人的话,恍如深醉花丛。秋已晚,冬将来,衰败的将衰败,可是,也真好啊,把那大把冬日的光景变成一场舒缓的精神休眠吧,让时光是透着光透着气的,象花与叶子间隙的光晕,象爱与被爱怀想的神秘,有些氲氤漫绕,又还瞧见几分童真气自在地跑。

有时,流泻而出又起念遗忘的或许是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读李叔同《悲欣交集》的书信,几次见“阅毕即焚”,有些心惊,有字可写便是有情挂怀如水流淌,刻意而忘可又是不堪传于人世。写与不写,忘与不忘,如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游荡。
肉身显现于世,灵魂隐于内心,看见肉身只需一双肉眼,洞悉灵魂却得深入内殿。灵肉相伴,是一生不离的光与影。天空尚且有裂可补,人间又怎可个个表里俱澄?引憾者,莫若美好的灵魂错置于丑陋的肉身,《巴黎圣母院》敲钟人的爱情就是那悲中之悲,可上天倒底是制衡的,让肉身渐次残败,独留灵魂不被朽坏。
“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令人激赏。人生在世,难免为自己设前方的路标,或以人,以事,或以物。有时,因着过度崇拜与仰视,却一叶障目,从整体到局部滋生出了遮蔽与失真。平视,客观,审慎地观圣人读经典,并不失尊重之意,还会添体恤之实,使之不至沦为化石,可嵌于世,流成活水。
有没有一个字,是心中的最爱?“光”,一定是这个字。在文字世界里,见过最难忘的名字是“光和盐”。一个人,可以欢欣,可以宁静,可以悲伤,可以粉碎,但不可一日心中无“光”。一个人,可以读诗,可以作画,可以饮茶,可以醉酒,但不可一日生活无“盐”。
龄官,《红楼梦》中酷似黛玉的唱戏女孩令人铭心,她独自在雨中蔷薇下一遍遍画“蔷”(贾蔷),看痴了贾宝玉,那一刻他才知“各人得各人的眼泪”,本是人间情爱的实祗。如果说秦可卿是性启蒙者,林妹妹是灵魂知已,龄官算是他的情感勘察师,为他丈量出爱情各有方向各有尺度。
高翔,扬州八怪之一,是春节里数次想到的古人,八人都可爱,体已来说最感亲近的是他。尤喜他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境界,有谁比他更爱日常?“山盹睡迟三市晓,”“卧听儿读妻织屦”,不传奇,不艺术,怪得平静。有谁比他更纯粹?足不出城,内心纳得起高山活水,笔底翻滚出大江大河,一挥一洒都是胸襟。
因《在细雨中呼喊》,我喜爱余华。两年前四位作家来校讲座,其中有他,衣着朴素,头发稍显蓬乱,发言状态是即兴的,对提问有一句说一句,整个人质朴,实沉,兼少许木讷感,真好,他不是一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人。曾读到他的生活很常态,真好,一个人通往深广,不必强将道路拧成绳索,危崖,异途。
文贵简净,也怕太简净,剔得离了地气。这好比住在过于洁净的旅店,漆味犹存,簇新得陌生,不见尘屑,下脚入室都似乎是一种亵染,每一个箱柜空空荡荡,如荒凉的洞穴,每一处细节,都礼节又疏离,无言提醒着,你与这一窗一几一床一被之间,来是偶然,去也是偶然,交托不了多长的光阴,你,只是它的过客。
所喜文字,简净是根,又保留着有生命感的细枝末节。就象是家,窗明几净,让人感觉亮堂,厅房,总有几样旧物随性地溢出,厨房,隔年的一二瓶罐还倚在角落,少许的凌乱,象春风来时那一片扫不尽的乱红烟絮,透着尘气,人气,真气,就是那么有体温的,有情绪的,有生机的,来来回回地荡涤着生生不息。
1849年12月22日这一天,陀斯妥耶夫斯基被宣判死刑,同一天,在刑场改判为服役,心理上真实地死过一回。如此陡峭的人生,世上有几人经过?他作品那些逼至绝处的灵魂拷问,也许正出自尖锋时刻的个体体验。巨大的惊恐,在生命下坠时,如一渊黑洞,让人在失重的临界点,再无处规避生死的善恶的,出口。
好作品该是怎样的颜色?是满天繁春?还是黑白二色?思量,遮蔽与虚假,常暗通款曲;绝对与粗暴,或一纸之间,好与之隔岸相向。愿,是在看见一个完整的世界,途经复杂,幽暗,莫测之境,一路存疑,自省,探寻,不止于单一的薄纯,不坠入杂芜的乱渊,因着光照粹炼如归,一路曲折地向善,尚美,趋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