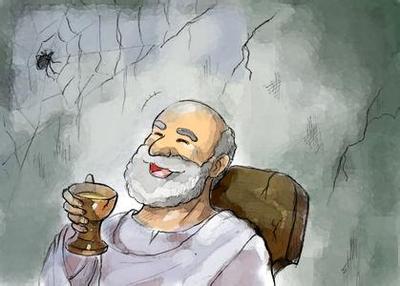古希腊哲学的简略轮廓
古希腊罗马哲学如果不包括希腊神话、赫西俄德在内,从泰勒斯开始也将近1100年,几乎占据了西方哲学史迄今2500余年的一半,所以古希腊罗马哲学非常重要,希腊罗马哲学史研究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基础。古希腊罗马一般分为三个时段:早期希腊哲学、希腊古典哲学和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早期希腊哲学从泰勒斯算起的话,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原子论学派德谟克利特有150多年,《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收的资料到德谟克利特为止,智者并没有收进去,这是对的。虽不算很长,但其诸多的学派、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及其演变,对后来的希腊罗马哲学以至后来整个的西方哲学都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早期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史的基础和首要环节。
早期希腊哲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哲学,包括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学派;另一个是西部南意大利哲学传统,毕达戈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以后,早期希腊哲学进入了一个深化发展的阶段,从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到希腊本土雅典改造复兴的伊奥尼亚哲学思潮,包括阿凯劳斯、第欧根尼、希波克拉底。随着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进展,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综合了前一阶段的两种哲学传统,大为推进了本原论、宇宙论、认识论、逻辑思维以及社会和道德思想方面的思考。
早期希腊哲学以自然哲学为主,但它也包含相当丰富的内容,图拉称其为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突出了早期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的水乳交融,重在对自然界本性的一种哲学探究。早期希腊哲学的第一个主题是“自然”,希腊文phusis,本义是“呈现”“生成”。早期希腊哲学家认为他们研究的自然是涵盖整个宇宙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的自身以及他的活动,所以其哲学也包含了不少对人自身本性的思考;第二个主题是宇宙论,关于宇宙生存、演化和结构;第三是灵魂、人的认识和思维;第四是自然科学思想,当然自然科学也交融在它的自然哲学里面;第五是宗教神学,不但包括希腊传统的奥林匹亚,也包括奥菲斯教,对毕达戈拉斯、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都有深刻的影响;第六是社会伦理和审美的思想。早期希腊哲学虽以自然哲学为主,但也已呈现出希腊人文精神的曙光,也是向希腊古典哲学过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前苏格拉底哲学残篇的整理:DK、KRS
关于早期希腊哲学资料的掌握,历来是一个曲折不断的难题。因为早期希腊哲学家大部分都有著作,好多都叫“论自然”等。但是由于历史的沧桑变迁,它们几乎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希波克拉底文集》留下来了。当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原著中保存了不少早期希腊哲学的思想。另外关于早期古希腊哲学家的生平,拉尔修的著作保留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虽然后来一些流派的哲学家著作中有片断的记载和相关论证,但残篇的保存和流传从亚里士多德弟子塞奥弗拉斯特编撰《自然哲学家的意见》历经艾修斯、斯多葛、西塞罗、基督教早期一直到辛普利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第一卷有专门篇章谈到残篇的保存和流传。所以,要编辑整理这些残篇是不容易的,翻译更有难度。
近现代西方学者对早期希腊哲学进行比较科学的整理,开始于德国的学者第尔斯,第尔斯在1903年出版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他去世以后,由克朗兹在1934到1937年出版了这部书的第五版,即德文版DK,为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奠定了最扎实的文献基础。该书分了AB两个部分,A的部分都是关于其他人转述的哲学家生平事项,B是早期希腊哲学家著述的残篇。对于从事古希腊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DK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因为它的完整丰富性、细致的考证,其他本子与其不可同日而语。
DK的B部分过去英语国家有弗里曼的译本《<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对照》。但很长时间里英语学界前苏格拉底研究相对较弱。直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第一版即KR的出版,才改变了这种情况。25年后,该书第二版基尔克、拉文、斯科菲尔德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出版,即KRS。KRS对推动整个英语学界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起了决定性作用,该书也是整个英语世界比较广泛使用的一个文本。当然,进入2000年以后,有许多新的、更加便携的一些本子,但是在专业的研究领域,最常使用的英文文献仍然是KRS。过去苗力田主编的《古希腊哲学》,早期希腊哲学残篇也是参照这部书翻译的。
当然,KRS也并非尽善尽美。KRS仿效DK的做法,把残篇和证言(后来的作家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思想、生平等等的记述)分开了,但是大部分的残篇是从证言里面抽出来的。早期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这种残篇抽离证言的方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有许多地方的论述可能是故意把前人的讲法融汇其中,他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对前人问题意识的重新修正,那么我们就很难脱离这个残篇出现的背景来单一地理解。KRS之后英语学界一个重要的汇编是201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格雷汉姆版,增加了许多证言,把这残篇放到了证言的脉络里。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出版的意义
古希腊哲学,目前国内研究成果最多的还是希腊古典哲学,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因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中译本比较多。而早期希腊哲学和希腊化罗马哲学的研究相对薄弱,因为早期希腊哲学家所留存的几乎都是残篇,没有全部翻译成为中文,罗马哲学家的拉丁文原著翻译成中文的也很少。
以学术翻译和学术资料的建设来促进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术资料是教学和研究的基本资源,学术资料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首要环节,关系到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如果缺乏这些的话,那无疑是无米之炊。基尔克、拉文、斯科菲尔德编著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判史》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资料汇编,而是研究性的著作。现在聂敏里教授将之中译,其中残篇以中文、古希腊文、英文三文对照形式出版,是非常重大的基本学术建设,必然会促进早期希腊哲学,乃至整个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学术资料建设和学科发展。
前苏格拉底哲学是很重要的一门学科,虽然相比于后面的那些体系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好像显得很零碎、可解释的空间很大,但它确实是很基础、很基本的。但国内做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学者很少,论文也很少,近十几年是比较冷门的。如何在国内推进这个学科,比如说和中国古典的研究,特别是先秦古典建立起关联性的比较,这些方面有很多值得探讨、思考的地方。另外,原文经典文献的翻译,特别是古希腊哲学方面,我国从上个世纪以来也有所积累。就前苏格拉底哲学来说,《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不是第一部,前面还有北大编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苗力田主编的《古希腊哲学》,里面都收了很多残篇。
聂敏里基于他二十年来对古希腊哲学,尤其是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贯通性的研究基础上翻译KRS。对中国学者来说,该书比原来的英文版更有帮助。残篇的翻译并不是根据英文,而是直译自古希腊文,并且希腊文、英文和中文三语对照,而且中译文比英译文更加精确。KRS的翻译多为意译,亦即附加了一些原文没有的解释性句子。但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更为严谨的中译本会对不完全精通希腊语的学者在引用和研究上提供更好的基础。
近三十年来的国际学术界,前苏格拉底研究已成为古希腊哲学研究里非常活跃的领域。《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译本巴门尼德部分注释非常多,而且详细讨论KRS的第二版和第一版为什么采取了不同的读法。这部分其实也是巴恩斯评论第二版时,认为较第一版非常大的改进。这不仅是基于研究对巴门尼德在翻译上有一些新的选择,关键是尝试提出了关于巴门尼德的非常重要的解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译本不完全同意KRS第二版的处理方式,并作了一些讨论和说明,这是学术价值非常高的部分。
又比如概念“心”,其实有不同来源的希腊词,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区别得非常清楚,但在早期它的含义就比较模糊;古代哲学的概念经过拉丁化后就变成了现代哲学的基础概念,古希腊哲学对后来的哲学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是否有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系统?怎么把汉语关于现代哲学的概念与古希腊哲学贯通?聂敏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中译就是这方面经验的一个重要积累。
聂敏里想借由中译《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和学界一起讨论怎样更好地翻译古希腊经典作品,并使它们构成汉译经典文献,通过这种异域学术的引入对汉语哲学思想进行一种塑造。就是重塑西学汉译的经典,然后用这种经典来重新寻求一种汉语哲学思想的表达。
关于西学中译的对话
聂敏里:翻译是一项活动在忠实与不忠实之间的工作。一方面,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不忠实的翻译不能称之为翻译,而是创作。但是另一方面,过于忠实原文的翻译也不是翻译,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也就不需要翻译了。翻译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不忠实于原文,所以有一个平衡需要把握。但有时这个平衡很难把握。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是以忠实于原文为主,不仅努力想要把原文的意思准确翻译过来,甚至想要把原文的语法,比如说作者写这个语句的语序、句子的结构、句子的语法关系等等也尽量准确地翻译过来。因为我觉得哲学家所写的文字,内在的语言顺序、轻重,前后的重点等等,也是有他想要传达的一些哲学内涵的,所以我努力想要把这种在字面意思之外的一些语法方面的信息也传达过来。但是如果这样来要求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间就会遭遇到一些难以避免的困难,就是有时候所翻译的句子会超出汉语句式所能够承受的限度。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适当调整以适应汉语语法,但我感到,所采用的这个汉语句式达到了它自身所能够允许的汉语语法的极限。比如会产生一些汉语习惯上很难接受的主谓宾、定状补这些成分过多、过长的句子,或者因为忠实于它的一些原文语序,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太惯常的汉语语法,比如说倒装句、插入句等等。所以有时候在汉语表达上就显得不是很流畅、很自然,显得很笨重,甚至生涩。
我记得陈康先生曾在他翻译的《巴曼尼德斯篇》序言中说过一个翻译原则——“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义”而不是“辞”,所以他说“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在我们公认的信、达、雅三原则中,他说信是最重要的。他认为追求信的翻译不但时常是不雅和不辞的,而且有时候还很难避免汉语所不习惯的一些语法或句式。在这种情况下陈康先生宁可选择不雅和不辞,他认为这样才能够传达和塑造一种汉语思想所不曾有的外来思想。
当然,完全不雅、不辞的翻译,即超出了汉语所能够接受限度的翻译,也就失去了翻译的初衷,因为翻译还是需要让汉语读者能够接受、能够理解。如果超出了汉语语法能够接受的限度,那么就和翻译的最基本出发点相违背了。因此翻译究竟是更多地忠实原文,从而读起来不那么流畅,还是更多地迁就汉语,使它读起来通顺流畅,换句话说,学术性翻译在语言上更为流畅些好呢还是更为生涩些好?这是我的一个困惑。要达到一种既能够很准确、同时又显示出很高汉语水平的翻译,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姚介厚:聂敏里刚才讲了两点哲学翻译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难度。由于语言本身的多义性,同一个概念,英文、希腊文和中文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对应,所以有时你选择一个语词来表达,甚至必须赋予其在汉语语境中新的意义,这是不容易的。
廖申白:古希腊哲学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都公认的规范。大家从不同的领域进入古希腊哲学研究,如从物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等,最开始接触的史料范围是不大相同的;有些是在国内受的教育,有些在国外;不同的哲学系学术的氛围和学术见解也不一样。所以分歧很大,很多术语,甚至名称、人名、文献名等等,都很难得有规范共识。
对古希腊哲学理论比较重要的概念、术语,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地表达出它在文本中的呈现方式,以及此方式要表达的关于概念、思想的那种连续性。我倾向于认为,重要的概念和术语尽量保持一致。这里一个很大的困难,比如说“是”(to on),它的根基是一个系动词,系动词转成种种变形,通过这种变形又名词化,而这个概念在古汉语里就没有,这就需要一个必要的扩展,不扩展就表达不了。
李秋零:聂敏里一开始谈到忠实与不忠实这个度怎么把握的问题。从我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来说,我自己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把握。我们应该忠实于什么?我觉得最应该忠实的是它的信息量。在忠实于信息量的基础上,还有一些东西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比如说倒装句、前装句,为什么这个词放在最前面?其实这里分明含有作者的意图,那么如何体现这些细微的信息量,这就见功力了。对于“信、达、雅”三原则,我觉得信、达能够统一起来,信则必达,不信则不可能达;同样的,不达不可能信。但是唯独“雅”,我历来是有看法的。比如我翻译康德的书信。康德是东普鲁士哥尼斯贝格人,哥尼斯贝格是一个文化上的穷乡僻壤。康德可以说思想上深厚,但是他谈不上雅。他的书信很多地方甚至文法不通,我们把它翻出雅来,是不是不达、不信?有时候一些文法拙劣的地方,我就让它呈现出一点拙劣。翻译一个文学作品,“达”不仅仅是意思的达,还包括文艺风格的“达”;翻译哲学作品, “达”也不仅仅是词句概念的“达”,也包括哲学家思维风格的“达”,即内涵上的“达”,对于词句的“雅”似乎用不着太重视。
王路:我觉得西方哲学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它有一种语言形式,第二个层面是我们对这种语言形式的理解。我们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如果这种语言形式能够包含、保留原语言想表达的诸种意思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形式就是好的。反之,如果通过翻译我们从字面上消除了它本来可能既有的某一种或者某几种含义的话,那么这种翻译一定是不好的。比如说把Being翻成“是”或者 “存在”,我觉得仅仅这么考虑是不够的,特别是作为资料性的东西。翻译语言从字面上能够容纳原文所包含的那种理解,给别人的不同理解留下空间,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比较好的翻译,古希腊语言更是这样。有一个柏拉图的注释本,它如此这般翻译:这个词希腊原文有六种含义,在第一种含义上理解,那么这句话应该是什么意思;如果是第二种含义又是什么意思;第三种是什么意思;最后译者说他取第四种含义。就是说,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加了一些理解。

韩东晖:我觉得李秋零老师对信达雅的理解有点问题,特别对“雅”的理解,他总是往文采方面讲,但是“雅”的本意是正声,《文心雕龙》里面讲“风正四方谓之雅”,也就是说“雅”是一种正音。当年严复讲“雅”就是指周秦诸子散文的正统笔法,用这种笔法来翻译。我们现在显然不可能用周秦诸子的文风去翻译古希腊残篇,虽然它们在时代上是比较接近的。现代汉语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太适合于表达比较古朴的前苏格拉底残篇。我觉得“雅”更多的是如何采用一种译者心目中比较规范典雅的语言来转译。在这个转译过程中,“信”更多的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达不达的问题。因为从“信”来说,不同的译者根据自己不同的研究心得,他会有不同的判断。翻译古典语言,我觉得“信”是与“达”、与自己的研究水准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在寻求中文表达时,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汉语本身的特点,在充分揭示作者意思的基础上,用比较典范的汉语来表达,这种译文能够成为传输比较长久的、具有典范性的翻译。比如贺麟先生翻译的《伦理学》,很多句子我觉得跟原文有些出入,但是要让我再重新翻译或者改动贺麟先生的文字又非常困难。《伦理学》的翻译以及它的遣词造句,整体上很难再有特别大的改进,而且有很多句子的表达也已成为典范的、又忠实又信达的一种语言表达。所以,我觉得翻译一方面必须要以研究为基础,这是一个前提;另一方面,它要以比较典范的汉语来表达。这样可能会产生一部在这两方面都比较成熟的翻译作品。
吴增定:翻译方面,我比较偏达和雅,信在其次。为什么呢?因为做专门研究的,坦白说很少依据中译本,一般直接阅读原文。当然会参考别人的中译文,但是阅读肯定是原文,否则你的学术品质肯定会降低。
中译本的意义就在于有人读它,而且是非专业的人读它。今天的学术进步到大部分做专业研究的基本上外语都过关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做翻译?其实就是为大多数潜在的爱好者。这就像鱼和水的关系。池塘的鱼就那么几条,但是这个水特别多,不断地滋养这些为数不多的鱼,使得你这个学术价值变得有意义,否则你做的领域会越来越窄。我虽然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平常还是会读一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如果有好的中译本,自然首先读中译本,第一节省时间,你不可能从原文开始读,对于非专业研究来讲太浪费时间了。第二,因为母语非常亲切,这种亲切感是其他任何语言无法取代的。所以信达雅我直接取了后两者,其次是信,因为中译主要是针对非专业人群,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看法。
成官泯:翻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方面是给那些洋文不好或者不懂洋文的人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法门。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老师的老师苗力田先生在翻译康德的时候就说,翻译康德是教康德说中国话,康德本来说的不是中国话,通过翻译让康德说中国话,这样让只懂中国话的人都能懂康德。翻译是个普及的工作、启蒙的工作。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西学研究学界都在做翻译。不论你的洋文有多么好,只要你不是用洋文进行思考和写作,那么这中间都不可避免存在翻译的过程。套用苗老师那句话,翻译是我们中国人学说康德的话,学说德语。就像翻译佛典,丰富了我们的语言、思想和文化。翻译这方面的意义非常巨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