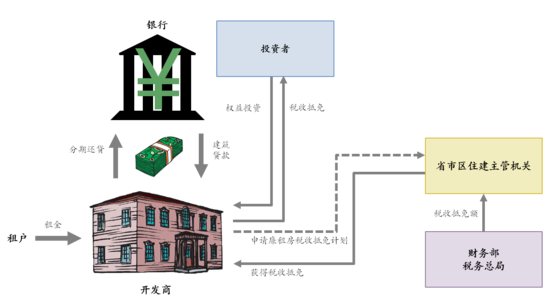那一晚,惠欣公寓被声浪席卷,吼声掌声叫好声如骇浪般浇向整栋楼。楼上的窗子里探出无数好奇看热闹的脑袋,看着楼下红心中央,一脸紧张又期待的男生的脸。
二十分钟后,大家都喊累了,蜡烛也烧尽了。刘斯箴寝室的窗,还是没有打开。
第二天,她的室友告诉我们,当晚她就在宿舍里,就在窗旁边的桌前。
室友说,在听到表白和起哄的瞬间,她慢慢地掏出耳机,调大音量,坐在桌前,开始写作业。自始至终,没有向下看一眼。
风雨不动,安如山。
第二天早晨,她把作业论文交给学委老呆。老呆怔怔地看着她的背影,后又拿出她的作业,像研究文物一样仔细看,看着看着,就叹了口气。他转过头来对我们说,没戏了。
我们说你别灰心,以后还有机会啊。人家也没明确拒绝啊!
老呆把她的作业给我们看。
一手工整的小楷流丽如溪水,又稳定如磐石。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简直是满分论文的范式。
老呆说,但凡对我有一点点感觉,昨晚这论文,她也不至于写得如此冷静。
3
那之后,生活如旧。老呆后来还是与一个学妹在一起了,我们和刘斯箴也失去了交集。只有每天上课时,偶尔一瞥说不定会瞥见她。
大学生活如此丰富精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八卦和故事。她就像一阵风,渐渐地被我们忘却了,甚至姓名都模糊在脑海。
大三课程少,学校管理也松散得不像话,去上课的人已经不多了。可是每次我去教室,总会看见她坐在前排,像一颗沉默的石头,旁若无人地安静在那里。
我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她度过了如此乏善可陈的大学生活,却收获了学业上的成绩。天道酬勤,我们的确不如她勤奋。
可是,这样的日子,还能叫做青春吗?规律如时钟,不动如参禅。
大二下学期,学院要对学生的档案重新整理归卷。我是班委,辅导员便叫我过去抄表。表上是每个人刚开学时填写的信息。我看着一张张表格,一张张一寸彩照,像是看见了两年前,身边的同学们青春逼人的脸。在抄到刘斯箴的信息时,她的家庭住址写得非常简单:青岛市,市南区。父母的信息,除了名字之外一模一样。
父亲,青岛市某某纺织厂工人,月薪3000元。
母亲,青岛市某某纺织厂工人,月薪3000元。
一如既往地普通,不贫穷,也不富有,一如她彩照上安静的脸庞,清清静静,如同细细的河。
一张张脸孔,在两年的时间里,多多少少都变了模样。貌似只有她没变,一己之力,以安静的姿态与时间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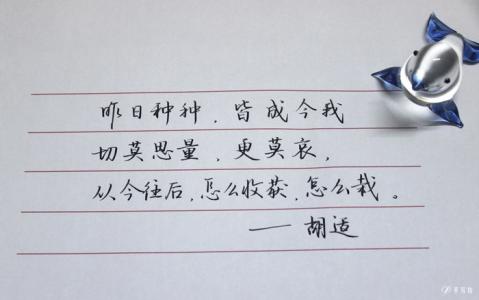
蓦然,我竟觉得,这也是一种勇敢。
青岛市,市南区。两年了,我才知道原来她和我住在一个城市,她是我的老乡。
4
在那次讲座之后,我开始对刘斯箴感兴趣。说实话,我被她流利的口语震撼住了。要知道,在我们这所只注重司法考试的学校里,许多人到毕业的时候,英文还处在初中的水准。
可惜,她还是毫无新意地继续安静着,让我无从挖掘。像是一块默默无闻的石头。
就这样,到了毕业。我也再没看到过她的光芒。
有时我会怀疑,那天,那个讲座,那是一场梦吗?那个在讲台上光芒逼人的她,如天神下凡般打破人间的静寂。那是真的吗?
毕业时,有的同学去考了公务员,有的做了律师,有的去了企业,有的连工作都找不到,双手空空。
刘斯箴就像是老师夸赞的得意门生,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那样—
她呀,上课认真听讲,平时坚持自习,不谈恋爱,也不瞎玩,珍惜时间,勤奋努力。
最终?最终考上名牌了呗。
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院校的研究生。我比较幸运,凭着小聪明和考前几个月,也被一所高校录取。我的学校离她很近,就在隔壁。
毕业晚宴上,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喜笑颜开,有人面色困窘。大家推杯错盏,拥抱,亲吻,大哭,大笑。
她坐在角落里,仍像一块石头。我喝得迷迷糊糊的,耷拉着脑袋靠在椅子上,目光一瞥,看见了她。
那时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喧闹的房间里,成群的人在抱着,拥挤着,诉说着,哭笑着,杯子碰得噼啪响。她坐在那里,仿佛别人是一个世界,她自己是另一个世界。
她喝光最后一杯果汁,开始给自己倒酒。不与任何人碰杯,自顾自地一仰而尽。再倒,再喝,再倒,再喝。她喝酒极快,完全不像不会喝酒的女孩儿,而仿佛久经沙场的老手。在她拿起酒杯的那一刻,气质瞬间变了。像是卸甲归田的老将,十年之后重新拔剑。剑光如水,波光倾泄,杀气腾腾,不可一世。
我醉眼迷离地看着她喝酒,转眼之间就是三瓶。她起身,倒白酒。三两的杯子,一口饮尽,她的脸开始红了,眼睛却很亮,透着一种蓄势待发的狠辣,亦是一种蛰伏十年的自负。
在喝完第二杯白酒时,她开始流泪,一点声音都没有,不擦,不捂,神色仍是安安静静。
泪水蜿蜒,在她的脸上垦出了两道河。她神经质地摇了摇头,又笑了笑。像是一种不屑地嗤笑。
最终,她终于憋不住了,趴在桌子上,把脑袋埋在手臂间,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摇摇晃晃地起身,轻拍她的后背,不停地说,够了,够了。
哭吧。想哭,就哭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