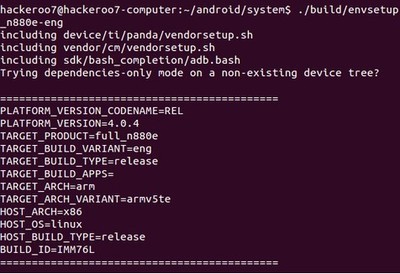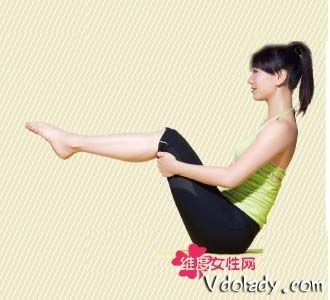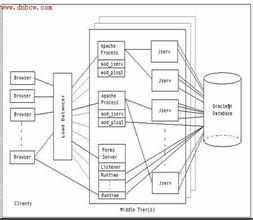小探有话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内思想界试图超越西方近代以来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提出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世界秩序主张,包括天下秩序、新天下主义、新世界主义等,引起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其中也包括许多亟待深入讨论的分歧。
为了给世界新秩序的各种主张搭建一个对话和讨论的平台,《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于3月5日在上海松江泰晤士小镇召开了“天下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峰论坛。通过讨论,各位持不同主张的学者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问题上增进了共识。《探索与争鸣》杂志第5期刊发此次论坛的发言实录,保留了讨论和争辩实况以飨读者。内容经发言者审订,略有调整和删节。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调整后的实录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由一篇主旨发言、两篇主评议和自由讨论三部分组成。
今天,小探为您奉上第一单元,且看赵汀阳、王家范、姚大力、高全喜、任剑涛、徐英瑾、白彤东、刘擎等大家共论天下体系的未来可能性。
天下体系与未来世界秩序 · 之一历史学不要试图替未来算命
王家范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
原题《历史学不是设计学,更不是未来学》
? 观点先看 ?
如果某个时候宣布社会“天人合一”了,那人类社会就不存在了;如果某人宣布“天人合一”掌握在他的手里了,这个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刹那刹那,舍旧布新。这样的理念,我总觉得跟西方的理念不一样。
历史不是设计出来的,所有的历史结果跟原先的主观设计一定不一样。历史学不是设计学,更不是未来学。历史学不要试图替未来算命。
——王家范
赵汀阳教授对《周礼》评价很高,好像是为他的“天下的当代性”大议论做铺垫的。周礼、周公,这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所以有亲切感。我清醒地知道,哲学与历史学的话语系统是不一样的。学习,首先就得学会倾听和理解,我努力地想这样做。
司马迁说过“三王之道若循环”。我注意到,现在的政治家也好,学者也好,发现应付当代有许多困难,想从古代那里找资源,再一次应验了太史公的“三王之道若循环”。人类追求理想“天下”的进程,“终而复始”,极富有趣味性。
不正规地说一句感慨,当代的“天下”,依我古代史的眼光,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总觉得都像是处在司马迁说的“周文”产生了严重问题,“礼崩乐坏”那样乱套,像是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因此提出了克服“文之弊”,将用什么去拯救?不知这种感觉对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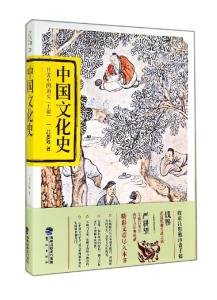
除了赵教授说到的,我在这里补充一点,中国的历史哲学,跟西方以分析为主的哲学体系,感觉上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个人对《周易》是非常崇拜的,认为它是中国人的哲学之根,是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个“八卦图”是永远处在动态中,负阴抱阳,周而复始。
还有一点很有趣,阴鱼里头有阳眼,阳鱼里头有阴眼,纯阳纯阴是极端;走到极端,就靠这“眼”迅速转向,克服不平衡病态,从而走出“天下”新的变局。阴与阳的功能并非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吉或凶),纯阴纯阳倒会走向最坏的结局。但中国人不担心,因为它不可能停住,刹那刹那间便变卦。
所以在中国人的哲学之根里,没有绝对的观念。西方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总想定出一个绝对好坏的标准。这是两种很不相同的思想方法,我觉得有些人还注意得不够。
再回过来说赵教授崇拜的“周天下”。西周变东周,一下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天下瓦解”了。这就是春秋战国的局面。所谓“百家争鸣”,说透了,鉴于周公设计的“天下”破碎了,大家都想缝合出一个新的“天下”,有许多方案。这情景,司马谈描述得最惟妙惟肖,叫做“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我很欣赏《古文观止》里的“六家要旨”,推荐学生必须读一读,对理解中国的历史哲学有帮助。我读出来的味道是,历史从来不是主观设计出来的,所有的历史走向都跟人的主观设计不符合。嬴秦得胜,似乎是法家的“天下观”赢了,到头来收获的却是秦短命而亡。汉家先是以黄老治天下,又宣布儒家一尊,其实这“汉家天下”是杂牌货,里头包含有“百家”的多种成分,但又不是它们原来的“纯种”。
所以,我主观偏执地认为,历史不是设计出来的,所有的历史结果跟原先的主观设计一定不一样。历史学不是设计学,更不是未来学。历史学不要试图替未来算命。
END
编辑:碧华
校对:优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