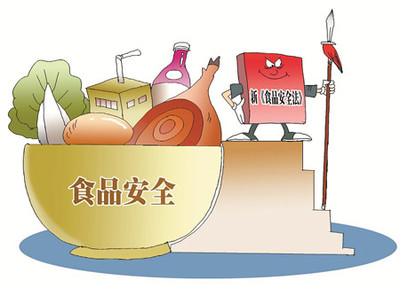《恆先》淺釋
李 銳(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
2004年4月2日上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举办的“简帛讲读班”第三十二次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办公室以会读的方式举行。李学勤先生、廖名春先生带领我們研讀李零先生提供了初步考釋意見的《恆先》一文。李先生、廖先生提出了許多精辟的意見,使我們受益匪淺。會後,我們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廖先生寫出了《上博藏楚竹書〈恆先〉簡釋》(一),詳細考證了前三支簡的内容。在李先生、廖先生的研究基礎之上,筆者不揣淺陋,作出此篇《〈恆先〉淺釋》,有不少地方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乞請方家指正!
下文將先提供筆者校訂后的《恆先》釋文,然後作逐句考釋。
恆先無有,樸、清、虛。樸,大樸;清,太清;虛,太虛。自厭不自牣,“域”作。有“域”焉有“氣”,有“氣”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未有天地,未1有作行、出生,虛清爲一,若寂水,夢夢清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2生,不獨有與也,“域”恆焉,生“域”者同焉。混混不寧,求其所生。異生異,歸生歸,違生非〈違〉,非生違〈非〉,依生依,求欲自復,復3生之。“生”行,濁氣生地,清氣生天。氣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異性,因生其所欲。業業天地,紛紛而4復其所欲;明明天行,唯復以不廢,知幾而亡思不天。“有”出於“域”,“生”出於“有”,“音”出於“生”,“言”出於“音”,“名”出於5“言”,“事”出於“名”。“域”非“域”,無謂“域”;“有”非“有”,無謂“有”;“生”非“生”,無謂“生”;“音”非“音”,無謂“音”;“言”非“言”,無謂“言”;“名”非6“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詳宜利主。采物出於作,作焉有事,不作無事。與天之事,自作爲事,用以不可賡也。凡7多采物,先樹有善,有治無亂。有人焉有不善,亂出於人。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焉8有剛。先有圓,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長。天道既裁,唯一以猶一,唯復以猶復。恆氣之生,因9言、名先。諸“有”,殆亡言之後者,校比焉舉天下之名所屬,習以不可改也。舉天下之作,強諸果,天下10之大作,其冥蒙(?)不自若作,庸有果與不果?兩者不廢,舉天下之爲也,無舍也,無與也,而能自爲也。11舉天下之生,同也,其事無不復。天下之作也,無許極,無非其所。舉天下之作也,無不得其極而果遂,庸或12得之,庸或失之?舉天下之名無有廢者,與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予?13
恆先無有,樸、清、虛。樸,大樸;清,太清;虛,太虛。
李零先生指出“恆先”也見於《馬王堆漢墓帛書·道原》(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作:“恒先之初,迵同大虛,虛同為一,恆一而止”,同樣是以“恆先”表示“道”(參看李學勤《帛書道原研究》,收入所著《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62——168頁)。“恆先”指作爲終極的“先”,“有”作爲道家概念,是相對於“無”。“恆先”是道,道始虛無,故曰“恆先無有”。
廖名春先生指出:樸:原作“”,李零以爲與“樸”字形不合,讀爲“質”。按,“”字所從下部與一般“樸”、“僕”所從“菐”之下部不同,“樸”、“僕”右旁一般是“丵”(下無十)下有“臣”,而此字“丵”(下無十)下似作“矢”。但與中山王鼎讀爲“業”的“”字上部相似。疑此字從“厂”從“菐”,隸作“”,讀爲“樸”。《文子?道原》即以“純粹素樸”爲“道之形象也”之一。又:《文子?自然》:“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此即“大樸”。
“清”,原作“寈”,李學勤先生讀爲“清”。廖名春先生指出:文獻中“靜虛”、“清虛”並多見,但下文受“大”修飾,讀“太靜”不如讀“太清”。《莊子?列禦寇》:“太一形虛……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鶡冠子?度萬》:“其德上反太清,下及泰寧。”《能天》:“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 “大虛”。《老子》第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虛極”,即“太虛”。《文子?精誠》:“老子曰:若夫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遊心乎太無,馳于方外。”“至虛”與“太無”並稱,即“太虛”。《莊子?知北遊》:“不過乎昆侖,不遊乎太虛。”帛書《道原》:“恒先之初,迵同大虛。”
案:《老子》中“樸”用以形容“道”,如第32章:“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而第28章則指出:“樸散則為器”。
《文子·精誠》: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
《文子·上德》: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
自厭不自牣,域作。有“域”焉有“氣”,
李零:“焉”,這裡是“乃”、“則”之義。
“牣”,原作“忍”,李學勤先生指出可以讀為“牣”或“仞”。《說文》:“牣,滿也。”《小爾雅·廣詁》:“牣,塞也。”或借“仞”為之,今讀為“牣”。
“域”,原作“或”。廖名春先生指出:“或”,本爲“域”本字。而“域”與“宇”同(《墨子·經下》“或過名也”孫詒讓閒詁)。“宇”爲空間。《文子?自然》:“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淮南子·齊俗》同。《尸子》佚文則作:“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可見“或”即“域”,也就是“宇”,指空間。“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老子》25章“域中有四大”王弼注),“域”是一個相當抽象的表示空間的概念。《淮南子·天文》:“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道始於虛霩”即“恒先無有”,“虛霩生宇宙”相當於“域作”,“宇宙生氣”相當於“有域,焉有氣”。可見《淮南子》說與此相當接近。
李學勤先生指出“域”乃宇宙,《老子》“域中有四大”,河上公注解为“八极之内”,陈柱先生认为“域”即宇宙。
案:《淮南子》使用生成的理論,《恆先》則在後文指出“氣是自生”。
有“氣”焉有“有”,
李零:此句是說“有”從“氣”生。下文說“濁气生地,清氣生天”,簡文“有”可能即指天地萬物。
案:“有”不指“天地萬物”,當是表示尚未具体化的“有”,此一階段,後文明說:“未有天地,未有作行、出生。”
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
李學勤先生指出“往”乃终、归之意;以上所論“有”、“始”、“往者”之先後,是邏輯上的先後。
案:“始”指開始,“往者”當連讀,《集韻·漾韻》:“往,歸嚮也。”《老子》第35章:“執大象,天下往”即用此意。《老子》第52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始”為“母”,乃“子”所復守之對象,故《恆先》中“始”為“往者”所歸守之對象。
未有天地,未有作行、出生,虛清爲一,若寂水,夢夢清同,
原釋文讀為“未有天地,未有作行,出生虛靜,爲一若,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李零:“一”,疑指道。“若”是“和”、“及”之義。“”,此字似可分析爲从水从尗从戈,疑以音近讀為“寂”。“夢夢”,《爾雅·釋訓》釋為“亂也”。子彈庫楚帛書有“夢夢墨墨”,《馬王堆漢墓帛書·道原》有“濕濕夢夢”,都是形容茫昧不明的混沌狀態。“靜同”,《道原》有“虛同”,是類似表達。“同”是表示“虛”、“靜”的普遍。
案:“出生”與“作行”接近,應當皆是“未有”之列,且帛書《道原》說:“虛同為一”,此處當連下讀為“虛清為一”。“”下似有“=”符,此處疑表示合文,可以讀爲“寂水”。
《文子·九守》:“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為一,寂然清澄。”
而未或明、未或滋生。
李零:“滋”指“滋生”。“未或明”、“未或滋生”,似指將明未明、將生未生的混沌狀態。牠們都含有“或”字。我們懷疑,原文此段就是講“或”。
案:《書·五子之歌》:“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尹文子·大道上》:“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未或”為古人習語,即是未有。
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
李零:“恆”,指上文“恆先”,即道。此句的意思是說道並不直接產生氣。
恆氣之生,不獨有與也,“域”恆焉,生“域”者同焉。
李零:“恆氣”,作爲終極的“氣”,最原始的“氣”。
案:第二“恆”字,當為使動用法,《書·洛誥》:“和恆四方民”,蔡沈《集傳》:“恆者,使可久也。”
混混不寧,求其所生。
“混混”,原作“昏昏”,廖名春先生指出:“昏昏”,與其解爲“不明”,不如讀如“混混”,解爲滾滾不絕。“昏”與“混”,兩字韻同聲近,當可互用。《孟子·離婁下》:“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晉書·傅咸傳》:“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混混”同“滾滾”,是水奔流不絕的樣子。
“所生”,廖名春先生讀為“所以生”,“所”下似有“=”符,待考。
異生異,歸生歸,違生非〈違〉,非生違〈非〉,依生依,求欲自復,復生之。
“異生異,歸生歸,違生非〈違〉,非生違〈非〉,依生依”,原文為“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非,非生韋,生”,李學勤先生指出:“異”是區別,“歸”是趨同,“韋生非,非生韋”有倒文,當作“韋生韋,非生非”,違是離,非是否定,依是肯定。
案:前一“復”字,當為歸、反(返)之意,詳下文;後一“復”字,意為重復、繼續。《老子》第16章:《老子》第16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云云,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老子》第52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生”行,濁氣生地,清氣生天。
《淮南子·天文》:“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
氣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異性,因生其所欲。
李零:“云云”,是衆多之意。李學勤先生指出《老子》第16章有:“夫物云云”。
業業天地,紛紛而復其所欲;明明天行,唯復以不廢,
“業業”,原釋文讀為“察察”。該字下有“=”符,字形與《孔子詩論》簡5“業”字近,可以視“=”爲合文讀爲“察察”,也可以視爲重文讀爲“業業”,《詩·大雅·常武》:“赫赫明明……赫赫業業”,毛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似當讀為“業業”。
《管子·五輔》:“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韓非子·制分》:“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莊子·天下》:“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復”,《爾雅·釋言》:“復,返也。”“返”、“反”或通用,《易·雜卦傳》:“復,反也。”《易·復·彖》“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注:“復者,反本之謂也。”,引申為“歸”,《書·舜典》:“卒乃復”,鄭玄注:“復,歸也。”《易·復》李鼎祚《集解》引何妥注:“復者,歸本之名。”
《易·復·彖》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老子》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動”。
知幾而亡思不天。
“天”原作“”,廖名春先生指出“”乃古文天字,又見於行氣玉銘、《華嶽碑》等。
案:“幾”原從“既”聲,“幾”與“既”古通[1]。“亡”,原作“巟”,“巟”从“亡”聲,疑可讀為“亡”,下簡10从巟从心者同。
《五行》:“幾而知之,天也。”《五行》說文中有:“‘聖之思也輕(經)’,思也者,思天也”。
“有”出於“域”,“生”出於“有”,“音”出於“生”,“言”出於“音”,“名”出於“言”,“事”出於“名”。
案:此一段講域、有、生、音、言、名、事的先後順序。
“域”非“域”,無謂“域”;“有”非“有”,無謂“有”;“生”非“生”,無謂“生”;“音”非“音”,無謂“音”;“言”非“言”,無謂“言”;“名”非6“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
案:《墨子·經說下》:“謂,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域、有、生、音、言、名、事皆不是恒久之物,故實際上僅是有名以指稱者,有文無實。
《莊子·齊物論》:“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詳宜利主。
“詳”,原作“恙”,李零先生讀為“詳”。
案:《荀子·修身》:“拘守而詳”,楊倞注:“詳,謂審於事也。”《古書虛字集釋》:“‘宜’,猶‘殆’也。(訓見《經轉釋詞》。按‘殆’是疑而有定之詞。)”
采物出於作,作焉有事,不作無事。
廖名春先生指出:“采物”見於《左傳》和帛書《二三子》,指區別等級的旌旗、衣物,相當於禮儀制度;“采物出於作”,“作”下有重文符,釋文脫漏。
案:《左傳·文公六年》:“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并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采物”為同意詞連用,與《左傳》隱公五年之“物采”同[2]。
與天之事,自作爲事,用以不可賡也。
案:“庸以”,《尚書·康誥》、《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雖見,但疑非此之意。“庸”、“用”古通;“以”,《古書虛字集釋》:“‘以’猶‘則’也。”賡,續也。
凡多采物,先樹有善,有治無亂。
案:《國語·鄭語》:“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韋昭注:“多,衆也。”“樹”,原作“者”,“尌”與“者”古通[3]。前引《左傳·文公六年》即云:“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并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
有人焉有不善,亂出於人。
案:此當指人之故意作爲,“與天之事”、“自作爲事”。
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焉有剛。先有圓,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長。
案:此一段講對立面之形成。
天道既裁,唯一以猶一,唯復以猶復。
案:“裁”,原作“載”。“天道既裁”,當指上文所言對立面之形成。對立面形成之後,“一”仍不變,往復之運動仍不變。
《老子》第39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帛書《道原》:“恒先之初,迵同大虛,虛同為一,恆一而止”,《莊子?天地》篇說:“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關於“一”,帛書《道原》後文也說到:“一度不變,能適規(蚑)僥(蝚)。鳥得而蜚(飛),魚得而流(游),獸得而走。萬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見其刑(形)。一者其號也……”。《恆先》沒有具體談“一”,當是有與《老子》、帛書《道原》、《莊子·天地》相近的文獻作爲不言自明的思想鋪墊。
恆氣之生,因言、名先。
案:《墨子·經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孫詒讓《閒詁》:“因,蓋與固是義同。”
諸“有”,殆亡言之後者,校比焉舉天下之名所屬,習以不可改也。
“校比”,從李零先生釋。
案:“諸”,原作“者”。“殆”,原作“”。“亡”,原从巟从心。“所屬”,原作“虛”,郭店《老子》甲簡2“或命之或豆”廖名春先生讀爲“或命之有所屬(囑)”[4],簡文“虛”也當讀爲“所属”。此句當是說先有衆物,然後才有其可以用言語稱謂之名,名本來乃人所給予,用以指實。然人在校比事物之時,往往舉名而責實,習以爲常,遂以爲名在物先。
《墨子·經上》:“舉,擬實也。”《經說上》:“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墨子·經說上》:“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
舉天下之作,強諸果,天下之大作,其蒙不自若作,庸有果與不果?
“蒙”,原作“尨”廖名春先生疑讀為“冥蒙”,待考。“庸”,廖名春先生以爲相當於“何”。
案:“果”,《論語·子路》:“言必信,行必果”,皇侃疏引繆協云:“果,成也。”[5]“強諸果”,強使之成之意,與《老子》第三十章“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強”之說相反。“自若”,《淮南子·泰族》:“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韓詩外傳》卷五第九章、《說苑·談叢》略同(《韓詩》少第一句)。“自若”與下文“自爲”之意相近。
此句疑指人所稱舉天下之“作”,往往是人勉強文飾而成之“作”。天下之大作,非自作,(乃是自然天成),無所謂果與不果。
兩者不廢,
案:疑指中、外,小、大,柔、剛,圓、方,晦、明,短、長等對立面不可偏廢,故下文云“無舍也,無與也”。
舉天下之爲也,無舍也,無與也,而能自爲也。
“舍”,原作“夜”,李零先生讀為“舍”。
案:《經轉釋詞》:“‘而’,猶‘乃’也”。
此句疑指天下之為,當輔助之但不能過於人爲,乃能使其天然自爲。
舉天下之生,同也,其事無不復。
案:此句疑指天下生物皆有相同之處,皆復其所欲,復歸其本。

天下之作也,無許極,無非其所。舉天下之作也,無不得其極而果遂,庸或得之,庸或失之?
“許”,李零先生引《墨子·非樂上》“吾將惡許用之”,訓為“處所”。
案:“極”,原釋文以爲從亙從止,但字形與一般“亙”不同,疑當釋為“亟(極)”。果,成也,說見前。“果遂”,猶《老子》第17章“功成事遂”。《左傳·昭公十二年》:“事不善,不得其極。”《國語·周語上》:“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
此句疑指天下之作,本來順應自然自爲,或未得其極,但處處亦可謂得其極。稱舉之作,則必稱舉得其極已成之事,其實無所謂得失成敗。
舉天下之名無有廢者,與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予?
案:“予”,原作“”,中山王鼎“”用作“慮”。“呂”古音屬來紐魚部,此疑讀為“予”(喻紐魚部字)。
此句疑指以天下有名有實之物(一、恆、道),以與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必將有求必應,事事可成。
[1] 參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第890頁,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2]參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548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5月。
[3]參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第277頁。
[4]詳廖名春師:《郭店楚簡老子校釋》,16——19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
[5]轉摘自程樹德:《論語集解》,929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8月。
[社会] 楚简《恆先》初探 [复制链接] night_11 night_11 当前离线 积分 56946 在线时间 12 小时 帖子 14503 注册时间 2010-3-17 精华 0 经验 42437 点 威望 0 点 金币 42457 狗仔卡17
主题0
好友5万
积分大家网博士后
大家网博士后, 积分 56946, 距离下一级还需 43054 积分 积分 56946 帖子 14503 精华 0 经验 42437 点 威望 0 点 金币 42457 发消息 1楼 发表于 2010-4-27 16:29 .pcb{margin-right:0}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三)》中的《恆先》篇,是一篇首尾完具的先秦哲學文獻。《恆先》經李零先生整理並發表以來,先後有李銳、廖名春、李學勤、龐樸等先生加以討論,已經對文義的理解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恆先》是論説性文章,其義理玄奧,又是以戰國文字寫成,其語言詞彙和論辯方式也有特點,因此比較難讀。今參照各家討論,先寫出釋文並斷句,再詳加注釋,在盡量對文本本身進行疏通的基礎上,來討論其思想傾向和學派的性質,以判斷它在先秦哲學史上的地位。先對本文的體例作幾點説明:1、釋文隸定在問題不大的地方從寬,有問題的盡量從嚴,破讀字加“()”括注;2、原簡行文中有“-”和“=”兩種符號,對於如何斷句和文義理解很重要,釋文照抄;篇末的篇章號,用“◥”來表示;3、今見龐樸先生對簡序重新進行編聯為:1-2-3-4+8-9+5-6-7+10-11-12-13;又美國學者顧史考先生認爲第3、4兩簡應該位置互換,並認爲2+4連接處的“之生”二字為衍文(顧史考:《上博楚簡〈亙先〉簡序調整一則》,2004年4月24日美國Mt. Holyoke 大學舉行的“Confucianism Resurrected”中國出土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首次發表)。本文經過斟酌,仍然認爲李零先生原來所編的簡序較合理,因此採用原簡序進行注釋和討論;4、所引直接關於本篇的各家之說,見下列文獻的不另出注:
李 零:《恆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廖名春:《上博藏楚竹书《恆先》简释》及其“修订稿”[ii];
李 銳:《〈恆先〉淺釋》;[iii]
朱淵清:《“域”的形上學意義》;[iv]
李學勤:《楚簡〈恆先〉首章釋義》;[v]
(以上四篇先見于“孔夫子2000”網站的“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不久又發表在“簡帛研究”網站)
龐 樸:《〈恆先〉試讀》,簡帛研究網站,2004/4/26。[vi]
另外,拙稿寫成以後再讀簡文,有些新的理解,也發現有幾個非常不妥的之處。但是按照新的理解,拙稿應作較大的改動,筆者一時無力重新寫過。因此寫了一些補記加在文中,供讀者參考。
一、釋文
恆先無有,、靜、虛,大,靜大靜,虛大虛。自猒(厭)不自忍,“或(域)”乍(作)。有“或(域)”焉又=氣=(有“氣”,有“氣”)焉又=又=(有“有”,有“有”)焉又=詒=(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未有天地,未【1】有乍(作)行出生,虛靜爲弌(一),若(淑)=(寂寂)夢=(夢夢),靜同而未或明(萌)、未或茲(滋)生。“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2】生”不蜀(獨),有與也,“或(有)恆焉生或(域)者”同焉。昏=(昏昏)不寍(寧),求其所生。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非=(非,非)生韋,生。求慾自復=(復,“復)【3】生之生”行。宔(濁)氣生墬(地),清氣生天。氣信神才(哉),云=(云云)相生,信浧(盈)天墬(地),同出而異生(性),因生其所欲。=(業業)天墬(地),焚=(紛紛)而【4】“復”其所慾。明=(明明)天行,隹(唯)“復”以不灋(廢)。智(知)(既—幾)而巟(無)思不(天)。“有”出於“或(域)”,“生”出於“有”,“音”出於“生”,“言”出於“音”,“名”出於【5】“言”,“事”出於“名”。“或(域)”非“或(域)”,無謂“或(域)”;“有”非“有”,無謂“有”;“生”非“生”,無謂“生”;“音”非“音”,無謂“音”;“言”非“言”,無謂“言”;“名”非【6】“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恙宜利(丂?主?)。采勿(物)出於作=(作,作)焉有事,不作無事。舉天之事,自作爲事,甬(庸)以不可賡也?凡【7】多采勿(物),先者有善,有(治)無亂。有人焉有不善,亂出於人。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少(小),焉有大;先有矛(柔),焉【8】有剛;先有囩(圓),焉有枋(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耑(短),焉有長。天道既載,隹(唯)一以猶一,隹(唯)復以猶復。恆氣之生,因【9】言名,先者,“有”(待)“(無)”言之,後者學(校)比焉,舉天下之名虛(屬),習以不可改也。舉天下之作,(剛—強)者果;天下【10】之大作-,其(敦)尨(厖)不自若-(若;若)作-(作,“作”)甬(庸)有果與不果?兩者不廢。舉天下之為也,無夜(舍)也,無與也,而能自爲也;【11】舉天下之生,同也,其事無不復;天下之作也,無許(所)(極),無非其所;舉天下之作也,無不得其(極)而果述(遂):甬(庸)或【12】得之?甬(庸)或失之?舉天下之名無有灋(廢)者,與(舉)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甬(庸)有求而不(予)?◥【13】
恆先【3背】
二、注釋
恆先無有,、靜、虛,大,靜大靜,虛大虛。
馬王堆帛書《道原》第一句舊釋為“恆无之初”,李學勤先生改釋為“恆先之初”[vii],李零先生據此指出“恆先”即“道”。李學勤先生指出,“恆”訓“常”,則《莊子·雜篇·天下》“建之以常無有”之“常無有”也即“道”。廖名春先生認爲,“恆”、“先”都是道的同義語。龐樸先生認爲,“恆先”是絕對的先。
按:“恆先”可如龐樸先生所理解,是絕對的“先”。絕對的“先”是“道”之體。凡舉一事,而“道”常在其先。“恆先”與“無有”是“道”的兩個方面。“恆先”是就道的時間屬性而言,而“無有”是說“道”是絕對的“無”。《莊子·外篇·天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名”,其“泰初有無”可以跟“恆先無有”對看。
不過,在道家文獻中,還提到“常後”。《淮南子·原道》“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文子·自然》“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常後”是道家所謂的“無為”,《文子·道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為也”,《老子》“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先〉後相隨。[viii]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恆先”是道之體,“常後”是道之用,二者對立統一。考慮到歷代避“恆”字諱有改“恆”為“常”的現象,“常後”也許原本就有寫成“恆後”的。
“”字目前有“質”(李零)、“全”(李學勤)、“樸”(廖名春、李銳、龐樸)三種講法。從文義來衡量這三種説法,我認爲,此字似以釋“樸”為優,而“質”、“全”恐怕都不足以描述道。
“樸”、“靜”、“虛”都是文獻中描述“道”時候常用到的詞。“靜”是說“恆先”而不動;“虛”是說“無有”。“樸”則是說“道”的體無形狀、量無大小。文獻所見對“道”的描述曾用到“樸”字的例子如:《老子》說:“樸雖小,天下不敢臣”;《老子》又說:“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樸”就是“道”;《文子·道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又說:“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文子?自然》“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而“道”也是“至大者無度量”。可見,“樸”是描述“道”有“至大無外、至小無内”的屬性。《恆先》的作者意識到以語言來描述“道”所受到的局限,所以,在列舉了“道”的三種屬性“樸”、“靜”、“虛”之後,又著重加説明“樸”為“大樸”、“靜”為“大靜”、“虛”為“大虛”,以同一般所謂的“樸”、“靜”、“虛”區分開來。
從字形上說,“菐”旁有讀為“殘”聲之字的例子。但是此字形容有其它用法,例如,在鄴城故城發現戰國陶文中的“鄴”字寫作“(業)”,跟《恆先》“樸”字偏旁寫法相似。《恆先》“樸”字偏旁寫法跟《說文》所見的“菐”字及从“菐”聲之字的偏旁很類似。目前所知古文字材料中雖未見過這樣寫的“菐”,但“樸”與“翦”、“業”聲音相去較遠,它們之間恐怕是形近訛混關係,或者是同一個會意字表示了“翦”和“璞”這兩個不同的詞,這一點有待在今後的發現中得到研究和證實。
自猒(厭)不自忍,“或(域)”乍(作)。有“或(域)”焉又=氣=(有“氣”,有“氣”)焉又=又=(有“有”,有“有”)焉又=詒=(有“始”,有“始”)焉有“ (往)”者-。
“厭”是“足”。“忍”似可訓為“容”:《論語·八佾》“是可忍也”皇侃疏“忍,猶容耐也”;《淮南子·本經》“而莫之充忍”,王念孫《讀書雜誌》讀“忍”為“牣”,《小爾雅·廣詁》“牣”訓為“塞”,“塞”、“容”義相近。(補記:“忍”訓“容”似嫌不妥,待考)這句似是說:道可以自足,但不自我容含(因爲道是“其大無外”的,見《管子·心術上》“道在天地閒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而容含它物,於是“或作”。
李學勤先生讀“或”為“域”,茲從之。我認爲,“域”跟“虛”相關,是對“虛”的闡釋。“虛”跟“厭(滿)”相對,大虛則一體無別,也即大滿;大虛也可以有所含容,也即容納它物的“域”。所以“域”是講“道”能容物的屬性。
“氣”是“域”首先所容含的,因爲“氣”跟“域”是相對而一體的(補記:參看下文對“恆氣之生因言名”的解釋);在“道”的虛無屬性中剖判了“域”跟“氣”的概念,則產生了“有”,而“氣”尚不屬於“有”的範疇。聯係前面的“恆先無有”來看,“有”相對“無有”而言;“始”在時間概念上立說,是相對於“恆先”而言。“往”似是“往而不反”之“往”,“有往”而無“復(或‘反’)”,還不能生出萬物,因此下文說“未有作行出生”、“未或明、未或滋生”。
對於“有‘有’”和“有‘始’”,《莊子·内篇·齊物論》有一段著名的論辯:“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通過連續不斷地否定,《齊物論》所追溯到的境界也是“恆先無有”。
未有天地,未【1】有乍(作)行出生,虛靜爲弌(一),若 (淑)=(寂寂)夢=(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茲(滋)生。
前面兩小節都是對“道”的屬性作重新界定所產生的認識。《恆先》的作者在這裡又指出,上述在“域”中存在的“氣”、“有”、“始”、“往”這些概念仍然是一個混沌僵局,此時既無實體(“未有天地”,與“虛”相對),也無產生實體的動力和運動(“未有作行出生”,與“靜”相對,沒有“復”的“往”也不能看成是運動),因此是一個“虛靜為一”的混沌狀態。“靜同”可看《文子·自然》“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馬王堆帛書《道原》說“恆先之初,迵同大虛,虛同為一,恆一而止”,據《文子·自然》“靜則同”,《道原》的“虛同為一”也即《恆先》的“虛靜為一”。
“一”是“道”的原始狀態。《恆先》所見的“道”,既有成爲宇宙根源的“道”,也有位于天下的“天道”。自《恆先》的作者看來,“天道”是從屬於“道”的,這與後文所見“天下之作”從屬於“天下之大作”的邏輯相同。不過“道”跟“天道”的共性是“一”和“復”,因爲“天道”的“一”和“復”是本於“道”的,因此下文又說“天道既載,唯一以猶一,唯復以猶復”。
通觀《道原》,《道原》著力於“道”的虛無狀態,而對道的“靜”則無所屬辭。《恆先》說“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則有意強調“道”在運動之前的“靜”態,其目的是為下文講“道”的運動提供鋪墊。
“ ”字下有重文符號“=”。李銳先生以爲是合文而釋為“寂水”。今按:“ ”字所从聲符見於楚文字“戚(原字从艸)郢”之“戚”字所从[ix],“戚”、“寂”的基本聲符都是“尗”,因此可以讀為“寂”。《老子》形容“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其“寂”字在馬王堆帛書甲本《老子》作“繡”,乙本作“蕭”,都是通假字。“夢夢”,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夢夢墨墨,亡章弼弼”;《道原》“濕濕夢夢,未有明晦”;《詩·大雅·抑》“視爾夢夢”、《小雅·正月》“視天夢夢”;《爾雅·釋訓》“夢夢、訰訰,亂也”郭璞注:“皆闇亂”,又引孫炎注“夢夢,昏昏之亂也”;又《爾雅·釋訓》“儚儚、洄洄,惛也”郭注“皆迷惛”。據上,“寂寂”是形容不動的狀態,“夢夢”是說昏亂的樣子。二者都是描述“道”在運行之前的混沌狀態。
“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2】生”不蜀(獨),有與也。“或(有)恆焉生或(域)者”同焉。
“是”當讀為“寔”,訓為“實”,[x]在句中做表示強調語氣的副詞,而非判斷動詞“是”(或稱之為“系詞”、“系動詞”)。[xi]
據本文上面所理解,“或(域)”與“氣”都是對“道”的屬性作重新界定所產生的認識,因此“或(域)”跟“氣”之閒不是生化的關係,而只是對“道”的不同理解而產生的“衍生”概念。那麽,“恆先無有”之“道”跟“或(域)”、“氣”之間是不是生化(或創造)關係呢?《恆先》作者下面要用到“生”的概念,他擔心讀者的誤解,因此在此作出解釋。
“或(有)恆焉生或(域)者”——先有“恆”,然後有“或(域)”,這個道理跟上文“有或(域)焉有氣”——先有‘或(域)’然後有‘氣’的道理類同。“同”,即《墨子·經說上》所說“同”之一義“有以同,類同也”。
“恆氣之生不獨,有與也”中的“不獨”跟“有與”相對為文,可參看《慎子·德立》“立天子者……害在有與,不在獨也”。“與”訓為“助”,這句是說,恆氣雖然是自生自作,但它的出現並非孤立,其前面有“恆”、“或(域)”的定義作爲先決條件;同理可以推知,“或(域)”的出現,也以先定義“恆”作爲先決條件。
“恆”訓為“常”,這裡兩個獨用的“恆”字可能都是“恆先無有”之“道”的簡稱;“恆氣”還見於下文“恆氣之生,因言名”,此“恆氣”似相當於文獻中的“元氣”。《論衡·談天篇》“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混沌為一’”,《恆先》上文“虛靜為一”即是元氣未分的狀態;《說文》“地,元气初分,清輕陽者為天,濁重陰者為地,萬物所陳列也”,《恆先》下文講氣的最初運行狀態,也有“濁氣生地,清氣生天”的話,可以證明“恆氣”相當於“元氣”。
《恆先》這一段定義了“恆氣之生”的“生”為“派生”,是要與下文“復生之生”的“生”區分開來。
昏=(昏昏)不寍(寧),求其所生。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非=(非,非)生韋, 生 。求慾自復=(復,“復)【3】生之生”行。宔(濁)氣生墬(地),清氣生天。氣信神哉,云=(云云)相生,信浧(盈)天墬(地),同出而異生(性),因生其所欲。
“昏昏不寧,求其所生”承上文省略了主語“氣”或“恆氣”,代詞“其”即指代“氣”。“昏昏”跟上文訓為“昏亂貌”的“夢夢”義近。“寧”訓為“安”。“昏昏不寧”是說“氣”的狀態不安定。
因爲前文說“氣是自生自作”,所以“求其所生”是“氣”與“氣”相求。《易·文言》引孔子語釋乾卦九五爻辭“飛龍在田,利見大人”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應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春秋繁露》第五十七章題為《同類相動》,謂“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類之相應而起也”;“同氣”之說亦見於《論衡·說日篇》:“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必殊;如誠同氣,宜合為一,無爲十也”;又《論衡·譴告篇》“凡物能相裁割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必同氣者也”。據此,“同氣”則相匹配、聚合,與“求”同聲系的“逑”字可訓為“聚合”、“匹配”,這兩個詞義都可以看作“求”的引伸義,也可以幫助理解。所以,“昏昏不寧,求其所生”是說“氣”不安定而產生自身的運動,它不斷同類相聚相配。
李學勤先生認爲“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非=(非,非)生韋,生”有錯倒之文,本應作“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韋,非生非, 生 ”。茲從之。“ ”字還見于《甲骨文合集》第27959號卜辭:“壬戌卜:馬咼…… 弗乍王乎……”,其字象重衣之形,《說文》云:“褺,重衣也”(文獻或作“襲”,參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又“複,重衣也”、“ ,重衣皃”。“ ”字可能與此三字中的某一個字有關,其音義待考。
繼續承《恆先》上文,“異”、“鬼”、“韋”、“非”、“ ”似乎都說的是“氣”的不同性質或狀態,也許可以分別稱爲“異氣”、“鬼氣”、“韋氣”、“非氣”、“ 氣”。大家知道,中國古代哲學常對舉“陰”“陽”二氣,《莊子·雜篇·則陽》“陰、陽者,氣之大者也”,但陰、陽二氣並不“同氣”,《鶡冠子·環流》“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合同也”。《越絕書·外傳·枕中第十六》“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也是說陰、陽二氣各自同氣相求從而產生萬物,可資參考。此處所見五種“氣”的性質,尚待考查。據上文所說的“同氣相求”,“異生異”等句之“生”字義近“感應”,含義跟“恆氣之生”的“生”不同。
“求欲”詞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求欲無厭”、《呂氏春秋·為欲》“(晉)文公可謂知求欲矣”、《申鑑·政體》“賤求欲而崇克濟”,此是“求”、“欲”義近連用作名詞的例子;《風俗通義》卷三“故御史大夫胡毋季皮獨過相侯,求欲作衰,曰:‘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此“求欲”為動詞。《左傳》僖公八年“予取予求”,裘錫圭先生解釋為“我只取我所要求的”[xii],“求”義也跟“欲”接近。《恆先》“求欲自復”謂“求欲”反于“求欲”,例如所生出之“異”反于原生之“異”。
“同出而異生(性)”是說同出於恆氣而有“異”、“鬼”、“韋”、“非”、“ ”之類的性質差別,“因生其所欲”則是概括“異生異”等五類運動的結果。
“濁氣生地,清氣生天”這類的話常見于古書講天地的生成,如《淮南子·天文》:“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易緯·乾鑿度》:“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
“氣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是說:氣誠然很神奇啊!自我相聚而生,誠然充斥了天地。“信”是副詞,可訓為“實”、“誠然”、“真”(《爾雅·釋詁上》“允,信也”郝懿行《疏》;又參看劉淇《助字辨略》卷四“信”字下的按語“誠也,實也,允也,果也”,舉例有《史記·田齊世家》:“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楊樹達《詞詮》“按:今語言‘真’”,舉例有《左傳》昭公元年“子皙信美矣。”、《孟子·公孫丑下》“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xiii]同類用法的“信”見於包山楚簡文書類第121號訊獄記錄“小人不信竊馬,小人信……殺舒睪”(又136簡:“不信殺某人”、137簡“信察問知”、144簡“信以刀自傷”、90簡“某地信有某人”),作爲副詞的“信”在戰國時的楚地可能是比較口語化的詞彙。
概括説來,此段是講因爲“氣”有往復不已的“同氣相求”運動,最終產生天地萬物。雖然同出于“氣”,卻有不同的稟性,因為五氣各自產生它們自己所欲求的同類,即所求不同,因而求得的結果也相異。
=(業業)天墬(地),焚=(紛紛)而【4】“復”其所慾。明=(明明)天行,隹(唯)“復”以不灋(廢)。
對“ =”字,李銳先生指出該字下有“=”符,其字形與上博竹書《孔子詩論》簡5“業”字近,可以視“=”爲合文讀爲“察察”,也可以視爲重文讀爲“業業”,並引《詩·大雅·常武》:“赫赫明明……赫赫業業”,毛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最後他認爲“似當讀為‘業業’”。今按:釋為“業業”是對的。
“紛紛”,《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尚書帝命驗》“東南紛紛”鄭玄注“紛紛,動擾之貌”。
“明明”,《爾雅·釋訓》“明明,察也”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天行,天道運行。“唯復以不廢”即“唯復不廢”,其“以”字用法略同于“而”。
很顯然,這裡強調的是“復”。聯係上文,“復”具體過程為“求其所生”、“因生其所欲”、“求欲自復”、“復其所欲”,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據此來看,“求”也可以視爲“往復”之“往”的動作,也就是“有始焉又往者”的“往”。所謂“天行”,是天之運行,《恆先》認爲“復”是天之運行的最根本原理和動力所在,唯有“復”的存在,“天”才能得以正常運行而不廢止。
智(知) (既—幾)而巟(無)思不 (天)。
“智而巟思不(天)”,李零先生讀作“知既而荒思不殄”,廖名春先生從之;李銳先生釋文作“知幾而亡思不天”,並引馬王堆帛書《五行》“經”文“幾而知之,天也。”及《五行》“說”文“‘聖之思也輕(經)’,思也者,思天也”為例。
今按:李銳釋讀正確,但語焉不詳。下面試為補充解釋。
“既”讀為“幾”,《易·歸妹》、《中孚》二卦爻辭均有“月幾望”,《釋文》也都說“荀作‘既’”,二字為見母雙聲,物、微二部對轉。《說文》“幾”字一訓“微也”,典籍“幾”字或作“機”,《說文》云:“機,主發謂之機”,此義是從“幾”字訓“微”義引申而來。《莊子外篇·至樂》“萬物皆出於機”,成玄英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
“智(知)既(幾、機)”見於《易·繫辭下》: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孔穎達《疏》:
“‘知幾其神乎’者,神道微妙,寂然不測,人若能豫知事之幾微,則能與其神道合會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上’謂道也,‘下’謂器也,若聖人知幾窮理,冥於道,絕於器,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王弼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說:
“幾者,去無入有,理而無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睹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昭,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於毫末;吉凶之彰,始於微兆,故爲吉之先見也。”
由此來看,《繫辭》所謂的“知幾”似可理解為:知道事物發展的最初徵兆及其普遍規律,就可以預先知道事情的發展,這種狀態通于神明。《恆先》“知既(幾)而無思不 (天)”的“既(幾)”當承上文指“復”而言(補記:這個理解似嫌狹窄),“復”是“天”運行的規律,所以“知幾”即知“天道”。
《恆先》“天”、“ ”並見,“ ”以“天”為聲符,該字也見於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戰國行氣玉銘,玉銘云:
行氣: 則畜,畜則神(申),神(申)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長,長則復,復則天。天其本在上,地其本在下,巡(順)則生,逆則死。
其中“天”跟“ ”也同時出現。陳邦懷先生認爲玉銘“ ”字从“天”聲而讀為“吞”,“復則天”的“天”則訓為“顛”。[xiv]但《恆先》“ ”字顯然跟玉銘“ ”字義不同,應另有其特殊的含義。
《鶡冠子·天則》“天者,捐物任事,故能莫宰而不天”,《度萬》“天者神也,地者形也……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王鈇》“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觀其下文,是說成鳩氏得道,可與天齊等,所以用“天”來形容;《天權》“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比利時學者戴卡琳認爲,上引《鶡冠子》諸例的“天”,可看作是對“天”的重新定義。[xv]于此可見,《恆先》“亡思不 ”的“ ”字用法與上舉《鶡冠子》各例“天”字類似,也應該表示一種等同於“天”的極致狀態,是“極高明”、“極其神明”的意思。
據此,“知幾而無思不天”是說:知道了天之道(“復”),則無有思而不明的事物(所思皆極其神明,也就同於“天”),語義跟《易·繫辭下》“知幾其神乎”相近,實際說的都是“不思而得”(語出《禮記·中庸》)。
郭店竹簡本及馬王堆帛書本《五行》之“經”文先說“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三者都是“謂之進之”;最後說“幾而知之,天也”(帛書本《五行》此處經文殘缺,據與之相對應的“說”文,應與竹簡本“經”相同),此“幾”當據《易·繫辭下》“知幾其神乎”解釋,“天”字的用法與“無思不”之“”同。
至於李銳先生所引帛書本《五行》“說”文“‘聖之思也輕(經)’,思也者,思天也”一句,並不是“幾而知之,天也”的經說,跟“知幾而無思不”能否對應以及該如何對應,尚需研究。
“有”出於“或”,“生”出於“有”,“音”出於“生”,“言”出於“音”,“名”出於【5】“言”,“事”出於“名”。“或”非“或”,無謂“或”;“有”非“有”,無謂“有”;“生”非“生”,無謂“生”;“音”非“音”,無謂“音”;“言”非“言”,無謂“言”;“名”非【6】“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恙宜利 (丂?主?)。
此節前半部分可與《鶡冠子·環流》篇開始的文字對看: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
《恆先》此處可據前文“……或作。有或焉有氣,有氣焉有有……”及後文“恆氣之生,因言名”等加以補充,並與《鶡冠子·環流》比較(所缺以“□”表示):
《鶡冠子》:一、□、氣、□、□、意、圖、名、形、事、約、時、物
《恆 先》:道、或、氣、有、生、音、言、名、□、事、□、□、綵物
二者雖然論述方式不同,但其聯係是顯而易見的。“一”即是“道”,也即“恆先無有”之“道”的簡稱“恆”。
後半部分雖是承上“或(域)”、“有”、“生”、“音”、“言”、“名”、“事”而言,但是所要表達的意思有個轉折。以“或非或,無謂或”為例,可以説明這類的句子的邏輯為:前一個“或”是“名”(“所以謂”),後一個“或”是“實”(“所謂”),“無謂”是“無‘所謂’”的簡省,沒有所謂的“或”,即沒有被稱爲“或”的“實”。前六個小分句順次為後者的條件:因爲“或”本是屬於“無”的範疇,所以“出於或”的“有”(即“無中生有”)也是無其所指之實;同理可以推知,“有”、“生”、“音”、“言”、“名”、“事”這些“名”都是虛名無實。
“恙宜利 ”一句不懂,待考。
綜上,此節先從“無”說到“有”,再據“無”而說所有的“有”都是虛指之“無”。以此處為轉折,《恆先》大概可以分爲前後兩部分,此前都是講“道”的運行而生天地萬“有”及“名”,下文則都是破除“名”和“有”。
采勿(物)出於作=(作,作)焉有事,不作無事。舉天之事,自作爲事,甬(庸)以不可賡也?
“采物”可如廖名春先生讀為“綵物”(見馬王堆帛書《二三子問》、《左傳》文公六年),典籍或作“物綵”(《左傳》隱公五年)。《左傳》文公六年孔颖达《疏》:“綵物,谓綵章物色,旌旗衣服,尊卑不同,名位髙下,各有品制。”《左傳》隱公五年孔《疏》:“取鸟兽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饰,谓之为物。章明物綵,即取材以饰军国之器是也。”從構詞方式上看,二字是“采(綵)”、“物”義近而連用。但文獻所見“綵物”或“物綵”的詞義内涵較小,專指象徵等級制度的旗章服飾之屬,這個意思用在《恆先》這裡是不合适的。
《荀子·正名》“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萬物利於器用者,也被專稱爲“綵物”。“采(綵)物”在《恆先》中的意思,似偏指“物”,就是萬物。“綵物出於作”的“作”,可訓為“用”。細繹文義,“綵物出於作,作焉有事,不作無事”之“綵物”似專指萬物之名而言。這是說人欲應用萬物,而分辨萬物進而給萬物命名,於是天下有事(《恆先》前文“事出於名”)。如果人不利用萬物,則無名無事。
“舉天之事,自作爲事,甬(庸)以不可賡也?”似省略了“人在天下,人事即天事”的前題,若此,舉凡“天之事”,都是“天”的自我作為,難道是不可繼續的麽?此是說從“天”的角度來看,天下的任何事物都是“天”自我作為的“天之事”,事物發展呈無終無始、無先無後的循環往復狀態,因此在任何一個時刻上都是承續前事和繼續天事。
“甬”讀為“庸”,楊樹達《詞詮》謂“反詰副詞,豈也”,研究虛詞的學者訓此種“庸”為“豈”、“何”、“安”、“詎”、“寧”,其所在的句子都是反詰語氣的疑問句。[xvi]下文“甬(庸)”多次出現,皆同此。
古書“賡”字皆訓為“續”,《說文》以“賡”為古文“續”字;《爾雅·釋詁》“賡、揚,續也”;《書·益稷》“乃賡載歌”,偽孔《傳》:“賡,續也”;《詩·小雅·大東》“西有長庚”,毛傳“庚,續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謂“庚”、“賡”同義,“庚”有“續”義,故古文“續”字取之以會意。《管子·國蓄》“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通典·食貨十二》引《管子》並注為“賡,猶償也”,其“賡”字亦可訓為“續”。
凡【7】多采勿(物),先者有善,有 (治)無亂。有人焉有不善,亂出於人。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少(小),焉有大;先有矛(柔),焉【8】有剛;先有囩(圓),焉有枋(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耑(短),焉有長。
“先者”參比下文“先者,‘有’待‘無’言之,後者校比焉”,是表示一種陳述的語氣,“有人焉有不善”之前省略了“後者”。
在萬物產生以後、未有人類以前,最初一切都是挺好的,天地萬物遵循自然規律(也就是“道”)而處於自然狀態,無所謂善惡,所以是“有治無亂”。後來,有了人,事情才開始變壞,所以“亂”出於人爲。這是因爲,人為規定了制度以後,萬物被劃分類別,有對立和比較。因此,“治”與“亂”、“善”與“不善”這些價值判斷都出於人為,而非自然。《老子》“故失道而後德,……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即指此。
天地萬物原本是統一體,並無中外、小大、柔剛、圓方、晦明、短長之分,這些分別,是人爲地區分和對立,看起來好像是“治”,實則是“亂”,因此是“不善”;而未分狀態的眾多綵物,遵循自然之道而一體無別,才是真正的“治”,因此是“善”。由此可見《恆先》作者反對人爲,主張無為而萬物因循其自然。《老子》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先〉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成功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跟《恆先》思想一致。
天道既載,隹(唯)一以猶一,隹(唯)復以猶復。
《恆先》論“道”,而“道”字只出現一次,其前尚有“天”字以爲修飾。自《恆先》的作者看來,“天道”是從屬於“道”的,這與“作”從屬於“大作”的邏輯相同。所謂“天道”,似可理解為“恆先無有”之“道”的運動表現,或理解為天地之間自然規律的運行。
“載”訓為“行”(《書·臯陶謨》“載采采”孔穎達疏“載者,運行之義,故為行也”、《淮南子·俶真》“日月無所載”高誘注“載,行也”)、訓為“始”(《書·益稷》“乃賡載歌”鄭玄注、《禹貢》“冀州既載”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引《詩·秦風·駟驖》“載獫歇驕”毛《傳》“載,始也”),“既載”是說天道已經開始運行,古書也說 “天道已行矣”(見《莊子·雜篇·庚桑楚》)。
“唯一以猶一,唯復以猶復”以及“唯復以不廢”中的“以”都是助詞,可訓為“而”,去掉以後對理解文義基本沒有影響。這三個短句是說天道在運行之後,其本體還是“一”,其動力還是“復”,這兩個屬性仍然不變,與“恆先無有”之“道”相同。
這裡的“一”和“復”都是重要概念。前文所見“道”在運行之前“虛靜為一”,而先秦哲學常見以“一”來譬喻道,此不贅引;“復”是往復循環,關於“復”的闡釋,詳見後文。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三)》中的《恆先》篇,是一篇首尾完具的先秦哲學文獻。《恆先》經李零先生整理並發表以來,先後有李銳、廖名春、李學勤、龐樸等先生加以討論,已經對文義的理解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恆先》是論説性文章,其義理玄奧,又是以戰國文字寫成,其語言詞彙和論辯方式也有特點,因此比較難讀。今參照各家討論,先寫出釋文並斷句,再詳加注釋,在盡量對文本本身進行疏通的基礎上,來討論其思想傾向和學派的性質,以判斷它在先秦哲學史上的地位。
先對本文的體例作幾點説明:1、釋文隸定在問題不大的地方從寬,有問題的盡量從嚴,破讀字加“()”括注;2、原簡行文中有“-”和“=”兩種符號,對於如何斷句和文義理解很重要,釋文照抄;篇末的篇章號,用“◥”來表示;3、今見龐樸先生對簡序重新進行編聯為:1-2-3-4+8-9+5-6-7+10-11-12-13;又美國學者顧史考先生認爲第3、4兩簡應該位置互換,並認爲2+4連接處的“之生”二字為衍文(顧史考:《上博楚簡〈亙先〉簡序調整一則》,2004年4月24日美國Mt. Holyoke 大學舉行的“Confucianism Resurrected”中國出土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首次發表)。本文經過斟酌,仍然認爲李零先生原來所編的簡序較合理,因此採用原簡序進行注釋和討論;4、所引直接關於本篇的各家之說,見下列文獻的不另出注:
李 零:《恆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廖名春:《上博藏楚竹书《恆先》简释》及其“修订稿”[ii];
李 銳:《〈恆先〉淺釋》;[iii]
朱淵清:《“域”的形上學意義》;[iv]
李學勤:《楚簡〈恆先〉首章釋義》;[v]
(以上四篇先見于“孔夫子2000”網站的“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不久又發表在“簡帛研究”網站)
龐 樸:《〈恆先〉試讀》,簡帛研究網站,2004/4/26。[vi]
另外,拙稿寫成以後再讀簡文,有些新的理解,也發現有幾個非常不妥的之處。但是按照新的理解,拙稿應作較大的改動,筆者一時無力重新寫過。因此寫了一些補記加在文中,供讀者參考。
一、釋文
恆先無有,、靜、虛,大,靜大靜,虛大虛。自猒(厭)不自忍,“或(域)”乍(作)。有“或(域)”焉又=氣=(有“氣”,有“氣”)焉又=又=(有“有”,有“有”)焉又=詒=(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未有天地,未【1】有乍(作)行出生,虛靜爲弌(一),若(淑)=(寂寂)夢=(夢夢),靜同而未或明(萌)、未或茲(滋)生。“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2】生”不蜀(獨),有與也,“或(有)恆焉生或(域)者”同焉。昏=(昏昏)不寍(寧),求其所生。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非=(非,非)生韋,生。求慾自復=(復,“復)【3】生之生”行。宔(濁)氣生墬(地),清氣生天。氣信神才(哉),云=(云云)相生,信浧(盈)天墬(地),同出而異生(性),因生其所欲。=(業業)天墬(地),焚=(紛紛)而【4】“復”其所慾。明=(明明)天行,隹(唯)“復”以不灋(廢)。智(知)(既—幾)而巟(無)思不(天)。“有”出於“或(域)”,“生”出於“有”,“音”出於“生”,“言”出於“音”,“名”出於【5】“言”,“事”出於“名”。“或(域)”非“或(域)”,無謂“或(域)”;“有”非“有”,無謂“有”;“生”非“生”,無謂“生”;“音”非“音”,無謂“音”;“言”非“言”,無謂“言”;“名”非【6】“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恙宜利(丂?主?)。采勿(物)出於作=(作,作)焉有事,不作無事。舉天之事,自作爲事,甬(庸)以不可賡也?凡【7】多采勿(物),先者有善,有(治)無亂。有人焉有不善,亂出於人。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少(小),焉有大;先有矛(柔),焉【8】有剛;先有囩(圓),焉有枋(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耑(短),焉有長。天道既載,隹(唯)一以猶一,隹(唯)復以猶復。恆氣之生,因【9】言名,先者,“有”(待)“(無)”言之,後者學(校)比焉,舉天下之名虛(屬),習以不可改也。舉天下之作,(剛—強)者果;天下【10】之大作-,其(敦)尨(厖)不自若-(若;若)作-(作,“作”)甬(庸)有果與不果?兩者不廢。舉天下之為也,無夜(舍)也,無與也,而能自爲也;【11】舉天下之生,同也,其事無不復;天下之作也,無許(所)(極),無非其所;舉天下之作也,無不得其(極)而果述(遂):甬(庸)或【12】得之?甬(庸)或失之?舉天下之名無有灋(廢)者,與(舉)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甬(庸)有求而不(予)?◥【13】
恆先【3背】
二、注釋
恆先無有,、靜、虛,大,靜大靜,虛大虛。
馬王堆帛書《道原》第一句舊釋為“恆无之初”,李學勤先生改釋為“恆先之初”[vii],李零先生據此指出“恆先”即“道”。李學勤先生指出,“恆”訓“常”,則《莊子·雜篇·天下》“建之以常無有”之“常無有”也即“道”。廖名春先生認爲,“恆”、“先”都是道的同義語。龐樸先生認爲,“恆先”是絕對的先。
按:“恆先”可如龐樸先生所理解,是絕對的“先”。絕對的“先”是“道”之體。凡舉一事,而“道”常在其先。“恆先”與“無有”是“道”的兩個方面。“恆先”是就道的時間屬性而言,而“無有”是說“道”是絕對的“無”。《莊子·外篇·天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名”,其“泰初有無”可以跟“恆先無有”對看。
不過,在道家文獻中,還提到“常後”。《淮南子·原道》“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文子·自然》“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常後”是道家所謂的“無為”,《文子·道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為也”,《老子》“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先〉後相隨。[viii]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恆先”是道之體,“常後”是道之用,二者對立統一。考慮到歷代避“恆”字諱有改“恆”為“常”的現象,“常後”也許原本就有寫成“恆後”的。
“”字目前有“質”(李零)、“全”(李學勤)、“樸”(廖名春、李銳、龐樸)三種講法。從文義來衡量這三種説法,我認爲,此字似以釋“樸”為優,而“質”、“全”恐怕都不足以描述道。
“樸”、“靜”、“虛”都是文獻中描述“道”時候常用到的詞。“靜”是說“恆先”而不動;“虛”是說“無有”。“樸”則是說“道”的體無形狀、量無大小。文獻所見對“道”的描述曾用到“樸”字的例子如:《老子》說:“樸雖小,天下不敢臣”;《老子》又說:“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樸”就是“道”;《文子·道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又說:“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文子?自然》“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而“道”也是“至大者無度量”。可見,“樸”是描述“道”有“至大無外、至小無内”的屬性。《恆先》的作者意識到以語言來描述“道”所受到的局限,所以,在列舉了“道”的三種屬性“樸”、“靜”、“虛”之後,又著重加説明“樸”為“大樸”、“靜”為“大靜”、“虛”為“大虛”,以同一般所謂的“樸”、“靜”、“虛”區分開來。
從字形上說,“菐”旁有讀為“殘”聲之字的例子。但是此字形容有其它用法,例如,在鄴城故城發現戰國陶文中的“鄴”字寫作“(業)”,跟《恆先》“樸”字偏旁寫法相似。《恆先》“樸”字偏旁寫法跟《說文》所見的“菐”字及从“菐”聲之字的偏旁很類似。目前所知古文字材料中雖未見過這樣寫的“菐”,但“樸”與“翦”、“業”聲音相去較遠,它們之間恐怕是形近訛混關係,或者是同一個會意字表示了“翦”和“璞”這兩個不同的詞,這一點有待在今後的發現中得到研究和證實。
自猒(厭)不自忍,“或(域)”乍(作)。有“或(域)”焉又=氣=(有“氣”,有“氣”)焉又=又=(有“有”,有“有”)焉又=詒=(有“始”,有“始”)焉有“ (往)”者-。
“厭”是“足”。“忍”似可訓為“容”:《論語·八佾》“是可忍也”皇侃疏“忍,猶容耐也”;《淮南子·本經》“而莫之充忍”,王念孫《讀書雜誌》讀“忍”為“牣”,《小爾雅·廣詁》“牣”訓為“塞”,“塞”、“容”義相近。(補記:“忍”訓“容”似嫌不妥,待考)這句似是說:道可以自足,但不自我容含(因爲道是“其大無外”的,見《管子·心術上》“道在天地閒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而容含它物,於是“或作”。
李學勤先生讀“或”為“域”,茲從之。我認爲,“域”跟“虛”相關,是對“虛”的闡釋。“虛”跟“厭(滿)”相對,大虛則一體無別,也即大滿;大虛也可以有所含容,也即容納它物的“域”。所以“域”是講“道”能容物的屬性。
“氣”是“域”首先所容含的,因爲“氣”跟“域”是相對而一體的(補記:參看下文對“恆氣之生因言名”的解釋);在“道”的虛無屬性中剖判了“域”跟“氣”的概念,則產生了“有”,而“氣”尚不屬於“有”的範疇。聯係前面的“恆先無有”來看,“有”相對“無有”而言;“始”在時間概念上立說,是相對於“恆先”而言。“往”似是“往而不反”之“往”,“有往”而無“復(或‘反’)”,還不能生出萬物,因此下文說“未有作行出生”、“未或明、未或滋生”。
對於“有‘有’”和“有‘始’”,《莊子·内篇·齊物論》有一段著名的論辯:“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通過連續不斷地否定,《齊物論》所追溯到的境界也是“恆先無有”。
未有天地,未【1】有乍(作)行出生,虛靜爲弌(一),若 (淑)=(寂寂)夢=(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茲(滋)生。
前面兩小節都是對“道”的屬性作重新界定所產生的認識。《恆先》的作者在這裡又指出,上述在“域”中存在的“氣”、“有”、“始”、“往”這些概念仍然是一個混沌僵局,此時既無實體(“未有天地”,與“虛”相對),也無產生實體的動力和運動(“未有作行出生”,與“靜”相對,沒有“復”的“往”也不能看成是運動),因此是一個“虛靜為一”的混沌狀態。“靜同”可看《文子·自然》“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馬王堆帛書《道原》說“恆先之初,迵同大虛,虛同為一,恆一而止”,據《文子·自然》“靜則同”,《道原》的“虛同為一”也即《恆先》的“虛靜為一”。
“一”是“道”的原始狀態。《恆先》所見的“道”,既有成爲宇宙根源的“道”,也有位于天下的“天道”。自《恆先》的作者看來,“天道”是從屬於“道”的,這與後文所見“天下之作”從屬於“天下之大作”的邏輯相同。不過“道”跟“天道”的共性是“一”和“復”,因爲“天道”的“一”和“復”是本於“道”的,因此下文又說“天道既載,唯一以猶一,唯復以猶復”。
通觀《道原》,《道原》著力於“道”的虛無狀態,而對道的“靜”則無所屬辭。《恆先》說“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則有意強調“道”在運動之前的“靜”態,其目的是為下文講“道”的運動提供鋪墊。
“ ”字下有重文符號“=”。李銳先生以爲是合文而釋為“寂水”。今按:“ ”字所从聲符見於楚文字“戚(原字从艸)郢”之“戚”字所从[ix],“戚”、“寂”的基本聲符都是“尗”,因此可以讀為“寂”。《老子》形容“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其“寂”字在馬王堆帛書甲本《老子》作“繡”,乙本作“蕭”,都是通假字。“夢夢”,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夢夢墨墨,亡章弼弼”;《道原》“濕濕夢夢,未有明晦”;《詩·大雅·抑》“視爾夢夢”、《小雅·正月》“視天夢夢”;《爾雅·釋訓》“夢夢、訰訰,亂也”郭璞注:“皆闇亂”,又引孫炎注“夢夢,昏昏之亂也”;又《爾雅·釋訓》“儚儚、洄洄,惛也”郭注“皆迷惛”。據上,“寂寂”是形容不動的狀態,“夢夢”是說昏亂的樣子。二者都是描述“道”在運行之前的混沌狀態。
“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2】生”不蜀(獨),有與也。“或(有)恆焉生或(域)者”同焉。
“是”當讀為“寔”,訓為“實”,[x]在句中做表示強調語氣的副詞,而非判斷動詞“是”(或稱之為“系詞”、“系動詞”)。[xi]
據本文上面所理解,“或(域)”與“氣”都是對“道”的屬性作重新界定所產生的認識,因此“或(域)”跟“氣”之閒不是生化的關係,而只是對“道”的不同理解而產生的“衍生”概念。那麽,“恆先無有”之“道”跟“或(域)”、“氣”之間是不是生化(或創造)關係呢?《恆先》作者下面要用到“生”的概念,他擔心讀者的誤解,因此在此作出解釋。
“或(有)恆焉生或(域)者”——先有“恆”,然後有“或(域)”,這個道理跟上文“有或(域)焉有氣”——先有‘或(域)’然後有‘氣’的道理類同。“同”,即《墨子·經說上》所說“同”之一義“有以同,類同也”。
“恆氣之生不獨,有與也”中的“不獨”跟“有與”相對為文,可參看《慎子·德立》“立天子者……害在有與,不在獨也”。“與”訓為“助”,這句是說,恆氣雖然是自生自作,但它的出現並非孤立,其前面有“恆”、“或(域)”的定義作爲先決條件;同理可以推知,“或(域)”的出現,也以先定義“恆”作爲先決條件。
“恆”訓為“常”,這裡兩個獨用的“恆”字可能都是“恆先無有”之“道”的簡稱;“恆氣”還見於下文“恆氣之生,因言名”,此“恆氣”似相當於文獻中的“元氣”。《論衡·談天篇》“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混沌為一’”,《恆先》上文“虛靜為一”即是元氣未分的狀態;《說文》“地,元气初分,清輕陽者為天,濁重陰者為地,萬物所陳列也”,《恆先》下文講氣的最初運行狀態,也有“濁氣生地,清氣生天”的話,可以證明“恆氣”相當於“元氣”。
《恆先》這一段定義了“恆氣之生”的“生”為“派生”,是要與下文“復生之生”的“生”區分開來。
昏=(昏昏)不寍(寧),求其所生。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非=(非,非)生韋, 生 。求慾自復=(復,“復)【3】生之生”行。宔(濁)氣生墬(地),清氣生天。氣信神哉,云=(云云)相生,信浧(盈)天墬(地),同出而異生(性),因生其所欲。
“昏昏不寧,求其所生”承上文省略了主語“氣”或“恆氣”,代詞“其”即指代“氣”。“昏昏”跟上文訓為“昏亂貌”的“夢夢”義近。“寧”訓為“安”。“昏昏不寧”是說“氣”的狀態不安定。
因爲前文說“氣是自生自作”,所以“求其所生”是“氣”與“氣”相求。《易·文言》引孔子語釋乾卦九五爻辭“飛龍在田,利見大人”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應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春秋繁露》第五十七章題為《同類相動》,謂“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類之相應而起也”;“同氣”之說亦見於《論衡·說日篇》:“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必殊;如誠同氣,宜合為一,無爲十也”;又《論衡·譴告篇》“凡物能相裁割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必同氣者也”。據此,“同氣”則相匹配、聚合,與“求”同聲系的“逑”字可訓為“聚合”、“匹配”,這兩個詞義都可以看作“求”的引伸義,也可以幫助理解。所以,“昏昏不寧,求其所生”是說“氣”不安定而產生自身的運動,它不斷同類相聚相配。
李學勤先生認爲“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非=(非,非)生韋,生”有錯倒之文,本應作“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韋,非生非, 生 ”。茲從之。“ ”字還見于《甲骨文合集》第27959號卜辭:“壬戌卜:馬咼…… 弗乍王乎……”,其字象重衣之形,《說文》云:“褺,重衣也”(文獻或作“襲”,參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又“複,重衣也”、“ ,重衣皃”。“ ”字可能與此三字中的某一個字有關,其音義待考。
繼續承《恆先》上文,“異”、“鬼”、“韋”、“非”、“ ”似乎都說的是“氣”的不同性質或狀態,也許可以分別稱爲“異氣”、“鬼氣”、“韋氣”、“非氣”、“ 氣”。大家知道,中國古代哲學常對舉“陰”“陽”二氣,《莊子·雜篇·則陽》“陰、陽者,氣之大者也”,但陰、陽二氣並不“同氣”,《鶡冠子·環流》“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合同也”。《越絕書·外傳·枕中第十六》“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也是說陰、陽二氣各自同氣相求從而產生萬物,可資參考。此處所見五種“氣”的性質,尚待考查。據上文所說的“同氣相求”,“異生異”等句之“生”字義近“感應”,含義跟“恆氣之生”的“生”不同。
“求欲”詞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求欲無厭”、《呂氏春秋·為欲》“(晉)文公可謂知求欲矣”、《申鑑·政體》“賤求欲而崇克濟”,此是“求”、“欲”義近連用作名詞的例子;《風俗通義》卷三“故御史大夫胡毋季皮獨過相侯,求欲作衰,曰:‘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此“求欲”為動詞。《左傳》僖公八年“予取予求”,裘錫圭先生解釋為“我只取我所要求的”[xii],“求”義也跟“欲”接近。《恆先》“求欲自復”謂“求欲”反于“求欲”,例如所生出之“異”反于原生之“異”。
“同出而異生(性)”是說同出於恆氣而有“異”、“鬼”、“韋”、“非”、“ ”之類的性質差別,“因生其所欲”則是概括“異生異”等五類運動的結果。
“濁氣生地,清氣生天”這類的話常見于古書講天地的生成,如《淮南子·天文》:“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易緯·乾鑿度》:“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
“氣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是說:氣誠然很神奇啊!自我相聚而生,誠然充斥了天地。“信”是副詞,可訓為“實”、“誠然”、“真”(《爾雅·釋詁上》“允,信也”郝懿行《疏》;又參看劉淇《助字辨略》卷四“信”字下的按語“誠也,實也,允也,果也”,舉例有《史記·田齊世家》:“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楊樹達《詞詮》“按:今語言‘真’”,舉例有《左傳》昭公元年“子皙信美矣。”、《孟子·公孫丑下》“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xiii]同類用法的“信”見於包山楚簡文書類第121號訊獄記錄“小人不信竊馬,小人信……殺舒睪”(又136簡:“不信殺某人”、137簡“信察問知”、144簡“信以刀自傷”、90簡“某地信有某人”),作爲副詞的“信”在戰國時的楚地可能是比較口語化的詞彙。
概括説來,此段是講因爲“氣”有往復不已的“同氣相求”運動,最終產生天地萬物。雖然同出于“氣”,卻有不同的稟性,因為五氣各自產生它們自己所欲求的同類,即所求不同,因而求得的結果也相異。
=(業業)天墬(地),焚=(紛紛)而【4】“復”其所慾。明=(明明)天行,隹(唯)“復”以不灋(廢)。
對“ =”字,李銳先生指出該字下有“=”符,其字形與上博竹書《孔子詩論》簡5“業”字近,可以視“=”爲合文讀爲“察察”,也可以視爲重文讀爲“業業”,並引《詩·大雅·常武》:“赫赫明明……赫赫業業”,毛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最後他認爲“似當讀為‘業業’”。今按:釋為“業業”是對的。
“紛紛”,《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尚書帝命驗》“東南紛紛”鄭玄注“紛紛,動擾之貌”。
“明明”,《爾雅·釋訓》“明明,察也”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天行,天道運行。“唯復以不廢”即“唯復不廢”,其“以”字用法略同于“而”。
很顯然,這裡強調的是“復”。聯係上文,“復”具體過程為“求其所生”、“因生其所欲”、“求欲自復”、“復其所欲”,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據此來看,“求”也可以視爲“往復”之“往”的動作,也就是“有始焉又往者”的“往”。所謂“天行”,是天之運行,《恆先》認爲“復”是天之運行的最根本原理和動力所在,唯有“復”的存在,“天”才能得以正常運行而不廢止。
智(知) (既—幾)而巟(無)思不 (天)。
“智而巟思不(天)”,李零先生讀作“知既而荒思不殄”,廖名春先生從之;李銳先生釋文作“知幾而亡思不天”,並引馬王堆帛書《五行》“經”文“幾而知之,天也。”及《五行》“說”文“‘聖之思也輕(經)’,思也者,思天也”為例。
今按:李銳釋讀正確,但語焉不詳。下面試為補充解釋。
“既”讀為“幾”,《易·歸妹》、《中孚》二卦爻辭均有“月幾望”,《釋文》也都說“荀作‘既’”,二字為見母雙聲,物、微二部對轉。《說文》“幾”字一訓“微也”,典籍“幾”字或作“機”,《說文》云:“機,主發謂之機”,此義是從“幾”字訓“微”義引申而來。《莊子外篇·至樂》“萬物皆出於機”,成玄英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
“智(知)既(幾、機)”見於《易·繫辭下》: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孔穎達《疏》:
“‘知幾其神乎’者,神道微妙,寂然不測,人若能豫知事之幾微,則能與其神道合會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上’謂道也,‘下’謂器也,若聖人知幾窮理,冥於道,絕於器,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王弼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說:
“幾者,去無入有,理而無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睹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昭,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於毫末;吉凶之彰,始於微兆,故爲吉之先見也。”
由此來看,《繫辭》所謂的“知幾”似可理解為:知道事物發展的最初徵兆及其普遍規律,就可以預先知道事情的發展,這種狀態通于神明。《恆先》“知既(幾)而無思不 (天)”的“既(幾)”當承上文指“復”而言(補記:這個理解似嫌狹窄),“復”是“天”運行的規律,所以“知幾”即知“天道”。
《恆先》“天”、“ ”並見,“ ”以“天”為聲符,該字也見於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戰國行氣玉銘,玉銘云:
行氣: 則畜,畜則神(申),神(申)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長,長則復,復則天。天其本在上,地其本在下,巡(順)則生,逆則死。
其中“天”跟“ ”也同時出現。陳邦懷先生認爲玉銘“ ”字从“天”聲而讀為“吞”,“復則天”的“天”則訓為“顛”。[xiv]但《恆先》“ ”字顯然跟玉銘“ ”字義不同,應另有其特殊的含義。
《鶡冠子·天則》“天者,捐物任事,故能莫宰而不天”,《度萬》“天者神也,地者形也……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王鈇》“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觀其下文,是說成鳩氏得道,可與天齊等,所以用“天”來形容;《天權》“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比利時學者戴卡琳認爲,上引《鶡冠子》諸例的“天”,可看作是對“天”的重新定義。[xv]于此可見,《恆先》“亡思不 ”的“ ”字用法與上舉《鶡冠子》各例“天”字類似,也應該表示一種等同於“天”的極致狀態,是“極高明”、“極其神明”的意思。
據此,“知幾而無思不天”是說:知道了天之道(“復”),則無有思而不明的事物(所思皆極其神明,也就同於“天”),語義跟《易·繫辭下》“知幾其神乎”相近,實際說的都是“不思而得”(語出《禮記·中庸》)。
郭店竹簡本及馬王堆帛書本《五行》之“經”文先說“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三者都是“謂之進之”;最後說“幾而知之,天也”(帛書本《五行》此處經文殘缺,據與之相對應的“說”文,應與竹簡本“經”相同),此“幾”當據《易·繫辭下》“知幾其神乎”解釋,“天”字的用法與“無思不”之“”同。
至於李銳先生所引帛書本《五行》“說”文“‘聖之思也輕(經)’,思也者,思天也”一句,並不是“幾而知之,天也”的經說,跟“知幾而無思不”能否對應以及該如何對應,尚需研究。
“有”出於“或”,“生”出於“有”,“音”出於“生”,“言”出於“音”,“名”出於【5】“言”,“事”出於“名”。“或”非“或”,無謂“或”;“有”非“有”,無謂“有”;“生”非“生”,無謂“生”;“音”非“音”,無謂“音”;“言”非“言”,無謂“言”;“名”非【6】“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恙宜利 (丂?主?)。
此節前半部分可與《鶡冠子·環流》篇開始的文字對看: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
《恆先》此處可據前文“……或作。有或焉有氣,有氣焉有有……”及後文“恆氣之生,因言名”等加以補充,並與《鶡冠子·環流》比較(所缺以“□”表示):
《鶡冠子》:一、□、氣、□、□、意、圖、名、形、事、約、時、物
《恆 先》:道、或、氣、有、生、音、言、名、□、事、□、□、綵物
二者雖然論述方式不同,但其聯係是顯而易見的。“一”即是“道”,也即“恆先無有”之“道”的簡稱“恆”。
後半部分雖是承上“或(域)”、“有”、“生”、“音”、“言”、“名”、“事”而言,但是所要表達的意思有個轉折。以“或非或,無謂或”為例,可以説明這類的句子的邏輯為:前一個“或”是“名”(“所以謂”),後一個“或”是“實”(“所謂”),“無謂”是“無‘所謂’”的簡省,沒有所謂的“或”,即沒有被稱爲“或”的“實”。前六個小分句順次為後者的條件:因爲“或”本是屬於“無”的範疇,所以“出於或”的“有”(即“無中生有”)也是無其所指之實;同理可以推知,“有”、“生”、“音”、“言”、“名”、“事”這些“名”都是虛名無實。
“恙宜利 ”一句不懂,待考。
綜上,此節先從“無”說到“有”,再據“無”而說所有的“有”都是虛指之“無”。以此處為轉折,《恆先》大概可以分爲前後兩部分,此前都是講“道”的運行而生天地萬“有”及“名”,下文則都是破除“名”和“有”。
采勿(物)出於作=(作,作)焉有事,不作無事。舉天之事,自作爲事,甬(庸)以不可賡也?
“采物”可如廖名春先生讀為“綵物”(見馬王堆帛書《二三子問》、《左傳》文公六年),典籍或作“物綵”(《左傳》隱公五年)。《左傳》文公六年孔颖达《疏》:“綵物,谓綵章物色,旌旗衣服,尊卑不同,名位髙下,各有品制。”《左傳》隱公五年孔《疏》:“取鸟兽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饰,谓之为物。章明物綵,即取材以饰军国之器是也。”從構詞方式上看,二字是“采(綵)”、“物”義近而連用。但文獻所見“綵物”或“物綵”的詞義内涵較小,專指象徵等級制度的旗章服飾之屬,這個意思用在《恆先》這裡是不合适的。
《荀子·正名》“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萬物利於器用者,也被專稱爲“綵物”。“采(綵)物”在《恆先》中的意思,似偏指“物”,就是萬物。“綵物出於作”的“作”,可訓為“用”。細繹文義,“綵物出於作,作焉有事,不作無事”之“綵物”似專指萬物之名而言。這是說人欲應用萬物,而分辨萬物進而給萬物命名,於是天下有事(《恆先》前文“事出於名”)。如果人不利用萬物,則無名無事。
“舉天之事,自作爲事,甬(庸)以不可賡也?”似省略了“人在天下,人事即天事”的前題,若此,舉凡“天之事”,都是“天”的自我作為,難道是不可繼續的麽?此是說從“天”的角度來看,天下的任何事物都是“天”自我作為的“天之事”,事物發展呈無終無始、無先無後的循環往復狀態,因此在任何一個時刻上都是承續前事和繼續天事。
“甬”讀為“庸”,楊樹達《詞詮》謂“反詰副詞,豈也”,研究虛詞的學者訓此種“庸”為“豈”、“何”、“安”、“詎”、“寧”,其所在的句子都是反詰語氣的疑問句。[xvi]下文“甬(庸)”多次出現,皆同此。
古書“賡”字皆訓為“續”,《說文》以“賡”為古文“續”字;《爾雅·釋詁》“賡、揚,續也”;《書·益稷》“乃賡載歌”,偽孔《傳》:“賡,續也”;《詩·小雅·大東》“西有長庚”,毛傳“庚,續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謂“庚”、“賡”同義,“庚”有“續”義,故古文“續”字取之以會意。《管子·國蓄》“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通典·食貨十二》引《管子》並注為“賡,猶償也”,其“賡”字亦可訓為“續”。
凡【7】多采勿(物),先者有善,有 (治)無亂。有人焉有不善,亂出於人。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少(小),焉有大;先有矛(柔),焉【8】有剛;先有囩(圓),焉有枋(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耑(短),焉有長。
“先者”參比下文“先者,‘有’待‘無’言之,後者校比焉”,是表示一種陳述的語氣,“有人焉有不善”之前省略了“後者”。
在萬物產生以後、未有人類以前,最初一切都是挺好的,天地萬物遵循自然規律(也就是“道”)而處於自然狀態,無所謂善惡,所以是“有治無亂”。後來,有了人,事情才開始變壞,所以“亂”出於人爲。這是因爲,人為規定了制度以後,萬物被劃分類別,有對立和比較。因此,“治”與“亂”、“善”與“不善”這些價值判斷都出於人為,而非自然。《老子》“故失道而後德,……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即指此。
天地萬物原本是統一體,並無中外、小大、柔剛、圓方、晦明、短長之分,這些分別,是人爲地區分和對立,看起來好像是“治”,實則是“亂”,因此是“不善”;而未分狀態的眾多綵物,遵循自然之道而一體無別,才是真正的“治”,因此是“善”。由此可見《恆先》作者反對人爲,主張無為而萬物因循其自然。《老子》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先〉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成功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跟《恆先》思想一致。
天道既載,隹(唯)一以猶一,隹(唯)復以猶復。
《恆先》論“道”,而“道”字只出現一次,其前尚有“天”字以爲修飾。自《恆先》的作者看來,“天道”是從屬於“道”的,這與“作”從屬於“大作”的邏輯相同。所謂“天道”,似可理解為“恆先無有”之“道”的運動表現,或理解為天地之間自然規律的運行。
“載”訓為“行”(《書·臯陶謨》“載采采”孔穎達疏“載者,運行之義,故為行也”、《淮南子·俶真》“日月無所載”高誘注“載,行也”)、訓為“始”(《書·益稷》“乃賡載歌”鄭玄注、《禹貢》“冀州既載”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引《詩·秦風·駟驖》“載獫歇驕”毛《傳》“載,始也”),“既載”是說天道已經開始運行,古書也說 “天道已行矣”(見《莊子·雜篇·庚桑楚》)。
“唯一以猶一,唯復以猶復”以及“唯復以不廢”中的“以”都是助詞,可訓為“而”,去掉以後對理解文義基本沒有影響。這三個短句是說天道在運行之後,其本體還是“一”,其動力還是“復”,這兩個屬性仍然不變,與“恆先無有”之“道”相同。
這裡的“一”和“復”都是重要概念。前文所見“道”在運行之前“虛靜為一”,而先秦哲學常見以“一”來譬喻道,此不贅引;“復”是往復循環,關於“復”的闡釋,詳見後文。
http://www.confucius2000.com/qhjb/sbcczshxjs.htm。
[ii] http://www.confucius2000.com/qhjb/sbcczshxjsxdg.htm。
[iii] http://www.confucius2000.com/qhjb/hengxianqs.htm。
[iv] http://www.confucius2000.com/qhjb/yudxsxyiyi.htm。
[v] http://www.confucius2000.com/qhjb/cjhxszsy.htm。
[vi] 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169。
[vii] 李學勤:《帛書〈道原〉研究》,收入《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viii] 朱謙之《老子校釋》案:“前”,敦煌本作“先”,遂州碑本、顧歡本、強思齊本亦作“先”。蔣錫昌曰:“按顧本成疏‘何先何後’,是成‘前’作‘先’。強本嚴君平注:‘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是嚴亦作‘先’。老子本書‘先’、‘後’連言,不應於此獨異。如七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六十六章‘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六十七章‘舍後且先’,皆其證也。”中華書局,1984年版,10頁。
[ix] 參看李守奎《楚文字編》46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x]參看謝紀鋒編纂:《虛詞詁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541頁。
[xi] 關於上古判斷動詞“是”的討論,參看唐鈺明:《上古判斷句的變換考察》及其“補正”、《上古判斷句辨析》,兩文都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唐鈺明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xii] 參看裘錫圭:《一句至少被誤解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常用的話——“予取予求”》,原載《古漢語研究》1993年2期,又收入《裘錫圭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本文引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273~275頁。
[xiii] 參看《虛詞詁林》411頁。
[xiv] 陳邦懷:《戰國行氣玉銘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年。
[xv] 戴卡琳著、楊民譯:《解讀鶡冠子——從論辯學的角度》,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56頁。
[xvi] 參看《虛詞詁林》498、499頁。
恆氣之生,因【9】言名。先者,“有”(待)“ (無)”言之,後者學(校)比焉,舉天下之名虛 (屬),習以不可改也。
“”以“知幾而巟(無)思不天”之“巟”字為聲符,“巟”讀為“無”,因此“”也可讀為“無”。“”,包山楚簡之文書簡中習見“”字都讀為“屬”。
“恆氣之生因言名”位于第8和第9號兩簡聯接之處,如何理解這一句,關係到是否需要像龐樸先生那樣調整簡序。
據《恆先》前文,“恆先無有”之“道”是絕對的“無”,“或(域)”跟“氣”這一對概念都是屬於“無”的範疇。“或(域)”是相對的“無”,而“氣”是相對的“有”,是處於“無”跟“有”之間的特殊角色。“有氣焉有有”的“有”才是絕對的“有”(實有)。綜合上下文來看,《恆先》作者認爲,“名”如果相對於“實有”而言,應該是可以不斷追溯到某個“實有”上,但是“實有”來自“氣”,“氣”卻是相對的“有”而非“實有”,所以“名”就不能落到“實有”上,更不能據“名”以説明這個相對的“有(“氣”)。相反,必須以屬於“無”的範疇的相對之“有”——“氣”來説明“實有”進而為“實有”命“名”。據此分析,“恆氣之生因言名”一句可理解為:在“恆氣”得以定義之後才能説明“有”和“名”。接下來的“先者有待無言之,後者校比焉”和“舉天下之名虛屬,習以不可改也”都是對“恆氣之生因言名”這一句的闡發。基於這樣的理解,原簡序是可以講得通的,也合乎《恆先》上下文的脈絡。
體會文義層次,“先者,……”跟“後者……”這種結構,是表示前後兩個陳述句的次第關係,前者為後者鋪陳條件,相當於“先是如何如何……之後就……”。
先是“有”需要借助“ (無)”才能證明有“有”,之後萬物才能“校比”於“有”而存在。從《恆先》作者看來,因爲“名”暨“有”本來都是“無”,這個“無”可以追溯到絕對的“無”,所以,舉凡天下之名都是虛無所屬,只是習慣成自然而不可更改。“虛屬”之名就是“廢名”,據此,下文“舉天下之名無有廢者”應該表示一種假設的情況。“習以不可改也”可參看《荀子·正名》:“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關於“‘有’待‘無’言之”的解釋,還可以參看《墨經下》:“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及《經說下》“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後無;無無焉,則無之而無”,伍非百先生釋曰:
此破“有無相生”之說也。“有無相生”見《老子》,相生,即相待之意。“無”之名,待有而有。“無”之實,離有而無。……《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又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耶?”又曰:“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有適有乎?”又《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庚桑楚》篇曰:“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又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此皆善談“無”之二相(原注:“有之無”與“無之無”,即相對之無與絕對之無,是為無之二相),與《墨經》對諍。蓋有無之說,墨家主有,道家主無。主有,故承認有“有之無”,而不承認有“無之無”。主無,則將“有之無”與“無之無”合竝為一,而歸於“無有”。主無者,以“天下萬物皆生於有,有生於無”,故言“有無相生”,主有者以“有無焉,則有之後無,無無焉,則無之而無。”故言“無不必待有。”二義為墨、道兩家物之辨所自出。[1]
據此,《恆先》“‘有’待‘無’言之”正是跟《墨經下》“無不必待有”相對而言。
李零先生讀“學比”為“校比”,引《周禮·地官·黨正》“以歲時立校比”文,未多做解釋。這裡補說一下“校比”的含義。
“校比”見於上海博物館藏攸戒鼎銘文“用校于比”[2],或稱“比(《左傳》作“庀”)”,《周禮·春官·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鄭玄注“比,校次其人在否。玄謂版,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周禮·地官·小司徒》職“九比”、“乃頒比法”“及三年,則大比”《疏》“凡言比者,是校比之言”。或稱“校”:《周禮·地官·黨正》“以邦比之法,率四閭之吏,以時屬民以校”。《國語·齊語》稱爲“比校”:“比校民之有道者”,韋昭解:“比,比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管子·小匡》略同《齊語》)。《周禮·春官·樂師》鄭玄注“比猶校也”,孫詒讓《周禮正義》解釋說:“案凡考校,必比方之而後差等見,故引申之,考校亦得為比”。
“校”是循名考實,“比”是等差次序。前文所講“中外”、“小大”之類的“名”是等差次序,可以理解為據有等差次序之名來考校萬物之實,簡單地説,就是循其類名而責其實有。《恆先》使用的是“校比”的較抽象含義,似更偏重於“比”,“校比焉”就是“比於有”,義近“天下萬物生於有”。《老子》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也可以作為“先者,‘有’待‘無’言之,後者校比焉”的注腳。
舉天下之作, (剛—強)者果;天下【10】之大作-,其 (敦)尨(厖)不自若-(若;若)作-(作,“作”)甬(庸)有果與不果?兩者不廢。
原簡“若”、“作”二字下都有“-”符號,是重文號兼句讀。“作”字下的“-”號也可以只理解為句讀號,因爲去掉重文的“作”對文義理解並無影響。
這段中的前兩個分句是對比關係,為下文“若……庸有……”結構的假設反詰疑問句提供鋪墊,問句之後“兩者不廢”是對上文做總結,兼有承上啓下的作用。我們先來討論句中的“ 尨”一詞。
“”字以“炅”為聲符,“炅”跟《說文》“慎”字古文“昚”是同一個字,該字據劉樂賢先生分析,是从“火”、从“日”、“日”亦聲的會意兼形聲字,它在出土秦漢文字材料中常用為“熱”字(馬王堆帛書《老子》“寒勝炅(熱)”);楚帛書“熱氣寒氣”之“熱”寫作从“宀”、“炅”聲;秦公簋(《殷周金文集成》04315)、秦公鎛(同上00270)銘文“鎮靜不庭”的“鎮”字寫作从金从“炅”而讀作“鎮”。[3]
“ ”跟我們習見的“尨”字寫法略有不同,是“尨”之變體。可以參看曾侯乙墓竹簡第170號簡“尨馬”之“尨”寫作“ ”(另請參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821頁下从雨从尨之字的偏旁,李守奎《楚文字編》473頁所舉天星觀簡、望山簡也有此字)。
“ 尨”可讀為“敦厖”,詞或作“純厖”(《楚辭·九章·惜往日》“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王逸注:“純厖,素性敦厚,慎言語也”)、“純龎”、“敦庬”(《國語·周語上》“夫民之大事在農。……敦庬純固,於是乎成”、《論衡·自紀》“存敦庬之樸”)、“敦懞”(《管子·五輔》“敦懞純固”、“敦懞以固”)、“敦龐”(《淮南子·俶真》“復反于敦龐”)。從聲紐上說,“炅”跟“敦”、“純”都是舌音;從韻部上看,“炅”从“日”聲當為質部字,“炅”可讀為月部字“熱”或真部字“鎮”或“昚(慎)”,而“敦”或“純”都是文部字。上古音真、文二部語音關係很密切,例如,古文字所見的真部字“鄰”可以“文”作為聲符;又例如,天星觀卜筮祭禱簡“歸玉玩車馬於悲(窆?)中”及“□車二乘”(見《楚簡帛文字編》919頁引)的“車”前之字同是从“炅”為聲,在簡文中可讀為“蜃”,“蜃車”是喪葬中所用的載柩之車,而“蜃”是文部字,此是“ ”可讀如文部字而“敦”、“”可以相通之證。據此,把“ 尨”讀為“敦厖”,從語音上說是沒問題的。
“敦厖”的意思是“厚大”或“純樸敦厚”,《左傳》成公十六年:“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杜預注:“敦,厚也;厖,大也”;《詩·商頌·長發》:“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鄭玄箋“厖,厚也”,《荀子·榮辱》引此《詩》作“駿蒙”,楊倞注“蒙”讀為“厖”訓為“厚”,王先謙《集解》謂:“厖作蒙,魯《詩》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厖。”
把“敦厖”訓為“厚大”,在《恆先》簡文中也可以講得通。“舉天下之作,強者果”是說如果舉凡天下之“作”,有強、弱之分,其中“強”者能夠成就;但是天下之“大作”,它厚大得已經不像自己了,如果要作為,“作”哪有成與不成之分?這也就是下文所說的“無不得其極而果遂”。可見,“敦厖”是就“大作”之“大”字而言,是形容其厚大的樣子。
從上下文看所謂“大作”,其性質是近於“道”的,因其至大而包含了“舉天下之作之強者”,所以“強者”之成就,也就是“大作”自己的成就了。《列子·黃帝》說:
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曰柔,常不胜之道曰强。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强,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则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
據此,“天下之作”出於“天下之大作”,這個“大作”當然要比“出於己”的“作”更強,其至弱也是至強。這是說,弱與強本來是一而非二。“兩者不廢”是承前文指“果與不果”,即“果與不果”都是“果”、都不廢。據此來看,《恆先》作者認爲成敗並無二致,因此主張無為。
從《恆先》全篇看,“舉天下之作,強者果”是作者的假設之辭,而非其正面觀點。郭店竹簡《老子》甲本說:“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強於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果而弗伐,果而弗驕,果而弗矜。是謂果而不強,其事好長。”其中的“善者果而已”、“果而不強”似跟《恆先》的立場相近。
(補記:原釋文或可以重新標點為:“舉天下之作,強者果天下之大作,其敦厖不自作,若‘作’庸有果與不果?”其中“大作” 下原簡有句讀“-”號,似提示“強者果天下之大作”應作一句讀。這段話是說:“強者”成就了“天下之大作”,那些厚大的“大作”不自我作爲,而以其中“強者”之成就作爲自己成就,因此無需自我作爲,如此,“作”豈有成就與不成就之分別?照此理解,“其”指代“天下之作”,“敦厖”後面省略“者”,“若”字需要倒文,“若”在此是指代前文的“代名副詞”,相當於“若然”。這種讀法的好處,是可以照顧到“大作”下“-”對文義層次的提示,讀下來似更順暢;壞處是“若”字需要倒文。權衡利弊,不能定于一。因此二說暫且並存,供讀者選擇。)
舉天下之為也,無夜(舍)也,無與也,而能自爲也;【11】舉天下之生,同也,其事無不復天下之作也,無許(所) (極),無非其所;舉天下之作也,無不得其 (極)而果述(遂):甬(庸)或【12】得之?甬(庸)或失之?
李零先生讀“夜”為“舍”,訓“許”字為“處所”,今按:“許”當讀為“所”字結構的“所”,《詩·小雅·伐木》“伐木許許”,《說文》“所”字下引《詩》作“伐木所所”,段玉裁以爲是許慎引三家《詩》。“”,李零先生認為从“亙”从“止”而讀為“恆”,李銳則指出,此字寫法與“恆”字不同,因此疑當釋“(極)”。今據字形,“”及“”字所从聲旁就是“亟”,並當讀為“極”。
這段文字可以分析為四個短句構成的複句。前面的三個含有“舉天下之”的句子有一些遞進關係,也是為兩個“庸或”問句的發問鋪陳條件。
因爲有“小”和“大”、“柔”和“剛”這類比較而言的理念存在,所以舉凡天下事物的活動,雖然從一個小的範圍來説是有“與”有“舍”,但相對於更大的“為”來説,則還是“自為”,仍是“大為”的内部運動;舉凡天下所生的事物,都是相同的事物,因爲事物的運行規律是“復”,次生的事物沒有不復歸于原生的“天下之作”,沒有終極的(處所),也無處不是它的處所(參看《荀子·不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所以,舉凡天下的作為,沒有不達到它的終極而果遂:因此,哪里有什麽得?又哪里有什麽失?
“舉天下之生,同也,其事無不復天下之作也”即《老子》所說的“復歸於無物”;“無所極,無非其所”、“無不得其極而果遂”即《老子》所說的“復歸於無極”。
《恆先》此處的意思,是所為皆得,而“得”也就是“失”,因此,“得之”和“失之”是等同的。郭店竹簡《老子》甲本:“為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臨事之紀:慎終如始,此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之所過,是故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這是強調無為、無執故無成敗、得失之分,跟《恆先》此處上下文的宗旨相通。
《恆先》此段是從事物的封閉性循環發展論證虛無的思想,進而引出無為的思想。
舉天下之名無有灋(廢)者,與(舉)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甬(庸)有求而不 ( —予)?◥【13】
“ ”字上所从為“呂”旁,兩“口”形中間有一豎筆貫穿,其寫法可以跟上博竹書《容成氏》“六類(律)六 ( 郘)”之“郘(呂)”旁相比較。[4]此字應如李銳所說,在此讀為“予”。《韓非子·揚權》“彼求我予”,也以“求”、“予”對文。
馬王堆帛書《經法·論》“二曰倚名,法(廢)而亂”,此即言“名之廢者”。[5]據《恆先》前文“舉天下之名虛屬,習以不可改也”知道,“舉天下之名無有廢者”也是《恆先》作者的假設之辭。
這兩個短句構成一個假設條件疑問複句:若舉凡天下之名,沒有廢的(即沒有“有名無實”的情況),那麽天下的明王、明君和明士,怎麽會有“有所求”而“無所予”的情況呢?
《恆先》的終章,歸結為對“因名責實”的評論。“庸有求而不予?”的表面意思是說“所求皆得”,但是聯係前文來看,“舉天下之名虛(屬),習以不可改也”,則所求不得也是正常的;又因爲“‘有’待‘無’言之”,即“名”源自虛無,所以即使有所得,也還會有所失,終究也是虛無。因此,《恆先》最後這個反詰問句的意思是:“求而不得”跟“所求皆得”也是等同的,這也是主張無為。此即《莊子·雜篇·徐無鬼》所謂: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上文以“天地”為“大備”,“知大備”則“無求、無失、無棄”,類似的話還見於《文子·自然》:“天地之道無為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可以參看。
“明王”、“明君”都是習見於戰國諸子文獻的詞彙,二者散言或可以通用無別,但是與“明王”相對的“明君”應該指封君而言,同樣也可以知道“明王”也不會只有一個;“明士”不見於其它載籍,應相當於文獻常見的“賢士”,賢士不會是普通有才德的士人,而是可以做君王輔相的人物。據上述可以知道,“明王”、“明君”、“明士”雖然無關《恆先》精義,但他們所暗示的是列國稱王、封君林立、士人登庸的戰國中晚期社會,這正是《恆先》寫作的時代背景。
綜合全文來看,我們認爲《恆先》所持的是一種很徹底的虛無主義觀點。
綜括以上的理解,我們可以將《恆先》的内容再分爲以下幾個層次:
1、 自“恆先無有”至“或(有)恆焉生或者同焉”是講“道”和“氣”的最初狀態;
2、 自“昏昏不寧”至“知幾而無思不天”是講氣的運動誕生了天地,並強調這個運動是“復”;
3、 自“有出於或”至“舉天下之名虛屬,習以不可改也”是辨析“名”與“事”。“名”與“事”出於人爲;但從天道的“一”和“復”的觀點來看,“名”、“事”皆源於虛無,歸于虛無;
4、 自“舉天下之作強者果”至“庸有求而不予”是用三個反詰複句來説明無成無敗、無得無失,各種結果都是同歸于虛無之“道”,其反復説明的都是“無為”觀點。
三、思想和學派初探
根據上面對《恆先》原文的理解,本文認爲《恆先》是一篇帶有濃厚的名辨學色彩的先秦楚地老、莊一派道家的理論文獻。
《恆先》所涉及的道家理論概念,最可以引起注意的是“道”和“天道”、“氣”和“復”。
裘錫圭先生曾稱《管子》中《心術》上下、《内業》、《白心》四篇作者所代表的道家學派為“稷下道家”,他認爲稷下道家所說的“道”是一種“精氣”,這種“道”是位于“天之下”的“天道”,而老、莊所說的“道”是位于“天之上”的,是宇宙根源性質的“道”,二者不同。[6]
根據裘先生的這個意見,《恆先》所見的“道”,既有成爲宇宙根源的“恆先無有”之“道”,也有位于天下的“天道”。《恆先》首章所見“恆先無有”之“道”的境界是很高的,可以說是將對“道”形容推到了一個極致的狀態,這合於《老子》所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的“道”,也合於《莊子·内篇·大宗師》所說“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的“道”,這種“道”的境界是稷下道家所未曾有。據此來看,《恆先》對“道”的理解合于老、莊。
《恆先》談“天道”說“天道既載”。從《恆先》作者看來,“天道”乃是“恆先無有”之“道”的派生。因爲一度曾有“未有天地、未有出生作行,虛靜爲一,若寂寂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狀態的存在,未有天地當然也談不上“天道”。《老子》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莊子·外篇·在宥》“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老、莊所謂的“天道”,指天地閒的自然規律而言。《恆先》的“天道”意義也是如此,而跟稷下道家“道即精氣說”沒有任何聯係。所以,僅從這一點來看,《恆先》也似乎是比較純粹的老、莊這一派道家的作品。
關於“復”是天道之運行(“天行”)的動力,先秦文獻有很多闡釋。例如:《易·復卦·彖傳》“‘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蠱卦·彖傳》“‘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正義》“終則復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易·剝卦·彖傳》“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在老、莊一派道家文獻,尤其是《老子》中,多次提到“復”,“復”又常訓為“反(返)”、“歸”,因此或以“反(返)”來代替“復”,或稱“復歸”,例如:
1、《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夫物云云,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郭店簡本《老子》作“萬物方作,居以須復;天道員員,各復其堇(根)”);
2、《老子》“政復為奇、善復為妖”;
3、《文子·上德》“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參看《莊子·外篇·天道》“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行”跟“物化”都是“復”)
4、郭店簡本《老子》“返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5、《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6、《老子》“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常德乃足,復歸于樸”,
可見,“復”是歸于事物的本來狀態“虛”和“靜”,其終極就是“無物”、“無極”之“無”。“復”又是終而復始,循環不已,這就是天道之運動。《恆先》論述了“復”的具體過程為:“求其所生”、“因生其所欲”、“求欲自復”、“復其所欲”,又極力強調“復”:“明明天行,唯復以不廢”、“天道既載,唯一以猶一,唯復以猶復”,“舉天下之生,同也,其事無不復”,而篇中所謂的“知幾而無思不 (天)”就是“知復”。通觀《恆先》,幾乎是用“復”的理論解釋了一切所要説明的觀點。“復”的實質是一種循環運動理論。《恆先》規定了運動的起點是“道”,所以循環往復的結果都歸于“道”。可以說,是這種宇宙循環論——“復”最終導致了老、莊一派道家的虛無主義思想,進而有清靜無為的主張。據此來看,《恆先》是發揮了老、莊一派道家關於“復”的理論。
《老子》、《莊子》罕言“氣”,即便談到“氣”,也常跟稷下道家所說的“精氣”說之“氣”相近。《莊子·内篇·人間世》“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大概是老、莊所言“氣”的較高境界。但《恆先》作者極力推崇“氣”:
1、 有“或”有“氣”,有“氣”焉有“有”。
2、 “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生”不獨,有與也。“或(有)恆焉生或”者同焉。
3、 (氣)昏昏不寧,求其所生。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韋,非生非, 生 。求慾自復,“復生之生”行。濁氣生地,清氣生天。氣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異生(性),因生其所欲。業業天地,紛紛而復其所慾。明明天行,唯復以不廢。
4、 恆氣之生,因言名。
自《恆先》作者看來,“氣”是自生自作,我認爲“恆氣”之“恆”是“恆先無有”之“道”的省稱;“‘恆’莫生氣”是說“恆先無有”之“道”並不是產生“氣”,“氣”可理解為“道”的派生屬性。“氣”又被稱爲“恆氣”,似乎就是“元氣”。因爲“氣”的運動才產生了天地萬物,所以作者由此感嘆“氣信神哉!” 由此看來,《恆先》里“氣”的地位非常重要。《恆先》所見宇宙萬物起源於“恆氣”的説法,或許可以稱爲“恆氣說”。本文認爲“恆氣”或跟“元氣”有關,是在目前的研究階段作出的一個初步判斷,此說是否合適,仍然有待討論。
《恆先》關於“氣”的敍述也看不到任何稷下道家“精氣說”的影子。《恆先》談氣的最初“求其所生”列舉了“異生異,鬼生鬼,韋生韋,非生非, 生 ”五種狀態,又說“濁氣生地,清氣生天”,據此,《恆先》的“恆氣說”可能跟陰陽、五行學説有些關係,但關係不大。
《恆先》所見的“恆氣說”可能是繼續闡發了老、莊一派道家推崇極致的“道”的理論,從而能夠更好地解釋宇宙的本源也是來自“道”。相比之下,郭店竹簡中的《太一生水》篇則是從“水”的角度來解釋宇宙生成,其與《管子·水地篇》“水者何也,萬物之本源也”相近,而跟《恆先》的“恆氣說”不同。《越絕書·外傳·枕中第十六》記載范蠡說:
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
此與《太一生水》所見的宇宙生成次序可以比較,其中的“道生氣”不同於“太一生水”,而跟《恆先》所說有近似處。前文曾引《越絕書》此篇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亦可資參考。
據本文所理解,《恆先》後半段所主張的是老、莊一派的“無為”學説,是很徹底的虛無主義學説。從戰國時代諸子爭鳴的角度考慮,《恆先》多用反詰的方式來説明自己的論點,不會是沒有論敵的自說自話。《恆先》所假設的論敵,似乎是受“名辨學”思想方法影響的學派中主“有”的一派。這一派的學者,例如墨子、商鞅、荀子、韓非等,都注重“審合形名”,“循名責實”,但《恆先》則將“有”和“無”統一為絕對的“無”,認爲“恆氣”屬於“無”,而“名”源自“無”,“有”需要“無”才能得到説明,又說“有非有,無謂有;……名非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舉天下之名虛屬,習以不可改也”,所以循名責實而實不可得。“舉天下之名無有廢者,舉天下之明君、明王、明士庸有求而不予?”也正是針對“循名責實”作出的反問。形名學所影響的大多數學派,如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韓非、儒家的荀子等,他們討論“有”、“無”、“名”、“實”的目的都是主張有爲,而《恆先》篇主張無為,二者可以相互為論敵。
裘錫圭先生稱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為“道法家”(即司馬談《六家要指》所謂的“道家”)的作品,其中的《順道》篇有“欲知得失,請必審名察刑(形)。”道法家大量出現在戰國末期,也大都講刑名,帛書《順道》主張“審名察形”以知得失,這跟《恆先》後半段主張無成敗、無得失的無為立場也是很對立的。因此,《恆先》的論敵也有可能包括這一派道法家的形名學說。
《恆先》論點雖然跟主張有爲的那些學派對立,但是《恆先》的論述方法也顯然深受名辨之學的影響。《恆先》篇中大量排比“有某焉有某”、“某生(於)某”、“某出於某”、“先有某、後有某”這類句式,應可以看作是名辨學影響下常見的邏輯推論方式。郭店楚簡中今題爲《語叢》一、二、三的三種簡書是儒家文獻,除少數内容可以看作是摘錄其它古書,多數内容都是上述那類句式的大量排比,似乎也是在用名辨學的方法來分析儒家的範疇和命題。由此可見,先秦名辨學影響當世,大概百家諸子概莫能外。在傳世的老、莊一派道家文獻中,《莊子·内篇·齊物論》也是運用名辨學來辨難百家的著名篇章。伍非百先生說《齊物論》:“今觀其篇中一名一辭,莫非取資於當時之辨者。則莊子以其人之術,破其人之學。其深通名辨,入據之,出擊之,方且駕儒墨百家之上,其造詣可知矣。”[7]因此,《恆先》所用的的思想方法,在老、莊一派道家的内部,跟莊子可能更爲接近。
有關《恆先》的名辨學色彩,仍有待今後結合其他先秦名家文獻作深入研究。
呂思勉先生曾談老、莊之別,曰:“老子之主清虛,主卑弱,仍係為應事起見,所談者多處世之術;莊周則意在破執,專談玄理,故曰其學相似而不同。然其宗旨,則究與老子為近。”[8]二者大概微有“術”、“理”之別。《恆先》通篇論理,也是近於莊子。
今傳郭象注本《莊子》分内、外、雜篇,一般認爲内篇是莊周本人的作品,外篇和雜篇的性質,還沒有定論。不過近年在江陵張家山136號墓發現了屬於《莊子》外篇的《盜跖》的殘簡,又在阜陽雙古堆一號墓發現的同屬《莊子》雜篇的《則陽》、《讓王》、《外物》的殘簡[9],據此來看,外篇、雜篇也都可以看作是戰國末年老、莊一派道家作品的匯集,似不會晚到漢初。[10]《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莊子》為五十二篇,今傳郭象注本只有三十三篇。據保存在日本的鐮倉本《莊子·雜篇·天下》篇末郭象的一段文字,說“一曲之士”往往“妄竄奇說”于《莊子》書中,“或牽之令近,或迂之令誕,或似山海經,或似占夢書,或出淮南,或辨形名”,“凡諸巧雜十分有三”,郭象把這些内容都刪掉了。[11]裘錫圭先生懷疑郭象所刪去“辨形名”的“奇說”,可能屬於道法家一類。[12]從《恆先》的思想和論辨方法都近於莊子來考慮,該篇會不會也曾被編入《莊子》外、雜篇,而屬於被郭象刪掉的“辨形名”一類?
《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可能跟老、莊一派關系密切、今又失傳的作品,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徐氏經說》、《老子傅氏經說》以及《蜎子》、《關尹子》(今本或偽)、《長盧子》等,上述某部古書原來會不會包含《恆先》,這也不是不可以考慮,但目前都很難稽考。考慮到《恆先》篇用楚文字寫成,因此暫且較爲謹慎地認爲《恆先》是先秦楚地老、莊這一派道家後學的作品,可能是比較合适的。但《恆先》論説性太強,所用的詞彙可能跟古書常見義有所不同,我們對其背景知識了解又不足,因此其文本的難讀自是不待言的;其思想方法和思想本身的傳承流變,更有待學界作長期的討論才能有基本的認識。本文僅僅是對《恆先》做些初步探索,肯定有許多不妥之處,希望有關專家學者能不吝批評賜教。
[1]伍非百:《墨辯解故》,收入《中國古名家言》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164-165頁。
[2]鼎銘見陳佩芬:《釋焂戒鼎》,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化研究所編《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吳振武:《焂戒鼎補釋》釋出“校”字,見《史學集刊》1998年第1期;李學勤:《韐伯慶鼎續釋》指出“于”為連詞,訓為與,並重點講了“比法”,見四川聯合大學歷史系《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巴蜀書社,1998年。
[3]參看劉樂賢:《釋〈說文〉古文“慎”字》,《考古與文物》1993年4期,94-95頁。
[4]參看陳劍:《上博简〈容成氏〉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簡帛研究網站,2003/1/9,http://www.jianbo.org/Wssf/2003/chenjian02.htm 。
[5] “法”讀為“廢”是裘錫圭先生的意見,見其著《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古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慎道田駢學派作品》,收入《文史叢稿——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70頁。
[6]裘錫圭:《稷下道家精氣說研究》及“補正”,收入《文史叢稿——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16-58頁。
[7]伍非百:《齊物論新義》序,收入《中國古名家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632頁。
[8]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35頁。
[9]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92年9期;韓自強:《阜陽漢簡〈莊子〉》,《文物研究》第六輯,黃山書社,1990年;韓自強、韓朝:《阜陽出土的〈莊子·雜篇〉漢簡》,《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10-14頁,三聯書店,2000年。
[10] 參看:廖名春:《竹簡本〈盜跖〉篇管窺》,《中國哲學》第十九輯,岳麓書社,1998年;李學勤:《〈莊子雜篇〉竹簡及有關問題》,《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五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許學仁:《戰國楚簡文字研究的幾個問題——讀戰國楚簡〈語叢四〉所錄〈莊子〉語暨漢墓出土〈莊子〉殘簡瑣記》,《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中華書局,2002年。
[11] 參看孫道升:《鐮倉本莊子天下篇跋尾》,收入《古史辨》第六冊,19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也引了郭象此語的一部分。
[12] 參看前注20所引裘先生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