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和“富人”概念的复活,使我们重新发现了“阶级”。“阶级”这个概念,如今已鲜有人提及,人们甚至以为“阶级”早已从共和国的地平线上消失,这个曾经如梦随影般的在我们的头脑中和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存活了很长时间的关键词,似乎已被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驱逐出去乃至寿终正寝。岂料却在21世纪的新语境中再度现身。原以为既然大家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大家都一心一意搞经济,团结和谐奔小康,何必再提“阶级”这个带斗争色彩的字眼。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阶级”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其间的矛盾冲突有时表现得相当激烈,比如劳资纠纷,比如老板欠薪,比如底层的受剥削、压迫。虽然性质有些改变,但阶级的客观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是再没有人这样叫罢了。阶级这个概念的复活,勾起了我们诸多的记忆。而打工文学的日渐勃兴,某种意义上,也表征着社会矛盾的无时无刻的存在。论及打工文学,使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一个如今非常流行的词汇:“底层”。“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在曹雷雨等译的《狱中札记》中,被翻译成“下层阶级”、“下层集团”。但是,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通过论述底层在各种统治中的作用而论及底层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取得霸权的问题,就是说,葛兰西的“底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而底层的其它方面是被置后的。
从全球化视阈观察,底层研究已经日见深入,学界对底层也有了学术的定义。在美国,黑人作为一个外来民族,一个作为低等民族存在的民族,它本身有自己的文化,由于本身的受压迫地位,他们会有强烈的反抗欲望,反抗手段之一就是要竭力保存自己的文化,不使自己被强势种族同化。这样,他们就有一个保存自己文化的强大动力,他们的优秀文化也就得以保存。但是,中国绝大多数是汉族,底层的绝大多数也是汉族,这些同族的底层,由于文化的同一,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他们的文化都是来自主流上层的灌输,很难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底层叙事的打工文学的萌芽与勃兴,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思想意义与文化价值,它使21世纪的中国文化能够真正地走进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底层人民。本文专论的对象主体王十月,在我看来,可以看作是“底层”的代言者,是以文学的形式/作家的名义,为千百万、上亿底层打工阶层争取话语权的一名打工作家。这样说来,一位真正的打工作家,他肩上的使命委实重大和神圣。他的身后,簇拥着一个庞大的进城务工的农民阶级。
打工文学无疑属于底层话语范畴。而打工者是打工文学的源头活水,打工文学是打工者的精神归依。打工作家王十月把异乡、流浪、梦想作为叙事资源,以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和表现形式,真实地记录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变化,塑造了一批背井离乡、为特区经济挥汗奉献、时代烙印鲜明的打工者形象,为数以亿计的打工者提供了精神食粮,为日渐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开启了新的话语资源和阅读市场,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了正极性元素。中国当代文学史因为有了一个个鲜活的打工者形象、一篇篇饱蘸血泪的打工文学作品而变得更加生动和真实。王十月笔下的“打工文学”,彰显打工者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与其他打工文学作家一样,他也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卷入城市化进程以后,生存状态堪忧,情感无处寄托,于是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在精神结构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写作欲望。王十月用笔在生活的夹缝里书写自己的血与泪、思与梦。从作品层面理解,打工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的“悯农”文学的自然延伸,是全球语境下世界移民文学的中国样本。王十月的许多作品,以真挚的情感表达对底层命运的关注,对生活原生态进行动态书写,它们反映了打工群体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困顿、困窘和困惑,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十月的文学写作的意义在于,它始终关怀弱势群体,而且这种关怀不是呈俯视的态势,而是一种零距离的平视,因为他自己就是底层打工群体的一员。在王十月看来,自己如何对待打工兄妹,打工兄妹就如何对待世界,自己如何关心打工兄妹,打工兄妹就如何关心中国未来。一个公平和谐社会,应该尊重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打工文学是中国一亿多打工者争取他们的话语权和文化表达的最佳渠道之一。王十月的打工文学文本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产生的某种精神现象和心灵矛盾,展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轨迹以及城市打工群体的心路历程,它是研究20世纪末叶以降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鲜活文化标本。
二
王十月以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及报告文学等文本,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他栖身于深圳宝安31区,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给贫血的主流文坛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读王十月的小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笔下的人物痛苦与其说来自物质的贫困,毋宁说是来自精神的压抑,诸如身份命名的歧视、城市霸权的挤迫等等。小说中居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渴望成为强者,过一种有自尊的生活。《纹身》中的那名少年把纹一条龙看成是强者的符号/象征,可又事与愿违地为自己招致许多麻烦。作者从现实中提炼出的意象性细节,颇具象征意味,隐喻着底层的精神诉求共性。小说对性格的刻画,也多有可圈点之处。他写小说可能还不是为了编故事,而是为一种生活代言,为他的乡党同伴开拓一条文化表达的通道。因此,王十月的文本是主流作家们不能越俎代庖的生命体验,这种“我写我”的写作形态具有强烈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底层特征。它是不可置换的。
打工作家带有难以克服的文化意义上的命名困窘。以王十月小说为例,它们分为两个系列:“打工系列”和“湖乡纪事系列”。仅从这样的命名便知,作者的情感横跨城乡两地。在“打工系列”小说《寻亲记》里,王十月借小说人物之口抒发难以抑制的思乡情怀。这些打工作家因“失地”而产生心理惆怅;同时,他们又因“失城”而产生身份焦虑。这种矛盾心态,在王十月小说中有着真实的再现。他所描绘的栖身《烂尾楼》的打工者们,对此有着生动举止和言语,小说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异质性的新鲜元素。他的“湖乡纪事系列”自觉不自觉地在向主流文学皈依。这里,诱惑与陷阱同在,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也正在此。打工作家们既要求主流文学认可,同时这种认可又意味着打工作家的自我放弃,这个两难问题值得理论批评界去研究。
打工文学是具有先锋性质的文化类种,它对于中国当下文坛不啻是一场革命。打工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某种天然内在的联系,对资本的批判同样强烈。这可能成为打工文学的思想资源,从而重新形成一种当下写作的有效话语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工文学可以借鉴左翼文学传统和艺术经验,执守自己的写作意愿而不必急于向主流文学皈依,以祛除命名的焦虑。倒是一个现象应该引起警惕,来自底层的作家一旦进入主流文学界,便不再讲述底层。仿佛一位来自乡村的农民歌手,一旦为主流歌坛所接纳,便急于完成向现代和后现代音乐的华丽转身,演唱起流行歌曲。如今王十月已经拿到“主流文学”的入场券,他的作品不断出现在国家各大权威纯文学刊物。价值在差异性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十月目前要做的,可能是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不要陶醉于进入“主流”的巨大喜悦之中,不要让自己的原生态元素被成功所冲淡,继续扮演好他为底层争取文化权利的角色。王十月笔下的文字像手术刀,无情地剖开都市社会的灰色地带。他的文本记录下挣扎于底层的人们与生活艰难的对抗的特殊过程,让我们由此更清楚地发见底层情状。他那些刺入人们心灵敏感穴位的文本,有时甚至具有一种震撼的力量。王十月的创作主要可分成两大板块,一为来自于他多年的漂泊经历。它们是现实的反映。作者以在场的身份书写底层的无奈与呼叫,如《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纹身》等。 另一板块则来自其对故乡童年记忆的重构,它们带有某种浪漫色彩。故乡荆山楚水间的那片土地巫风盛行,自幼在巫鬼文化中长大的他,熟稔那里的风俗传说,因此他的楚州系列小说是天马行空,是荒诞荒唐,与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距离。这些以长篇为主。王十月力图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字王国,他给它命名为“楚州”,由农村/小镇/城市三个单元构成,这是一个文学的符码。长篇《31区》写的是楚州一个城乡结合部小镇,长篇《活物》写的是楚州农村。而第三部《蛇街》则是书写都市的。一部名为《姑娘,你弄疼了我》的小说,生动描绘了一些打工妹的生活际遇。她们纯洁真诚的心感动了作者,作者又以小说文本感动了我们。王十月模仿诗人艾青的口吻说,“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她们爱得深沉。”这不是底层异性之间的一般情爱,它应该理解为一种对抗生活、不屈命运的底层人们的心灵挣扎与搏斗。细节生动有趣。这是一部具有人文内涵的作品。它所抵达的不是情绪和语言,而是人生之叹、命运之痛,它是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
长篇小说《烦躁不安》以打工生活为背景,以一场打工官司为经,以打工者的情感纠葛、命运坎坷为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底层生活画卷。小说中的记者、律师、打工妹、政府官员、治安员、道士、画家、三陪女、同性恋者,林林总总,三十来人,各具特色。它一气呵成,可读性强,既有打工生活场面真实再现,又有对人性的剖析和哲学思考,被誉为“打工文学有史以来最有特色、最具文学品质的一部长篇,是打工一族的《废都》”。这部书是一部对人生有着深刻领悟的长篇。它的故事不太复杂,篇章结构上颇见功力。飞碟是小说中的一个颇可玩味的意象,也是破译小说的一个密码。小说的另一重要意象是蝴蝶。飞碟和蝴蝶的设置,是作家的立意关键。它们与《废都》有些类似,或者说有所借鉴和延伸。
小说《民工李小末的梦想生活》表现着作家丰富的想像力,它巧妙的构思,幽默的语言,激活了我的阅读兴致。李小末是一个平凡的民工,他有着平凡的梦想,但这个人也有他的毛病。梦想加毛病,便造就了“这一个”有意思的人物。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动能在这篇小说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文学是对生活的解构与重构,对此作者有着深刻的颖悟。所以他的小说有一种虚构的真实,真实得让人觉得这虚构的故事比真的还过瘾。李小末的故事既搞笑又耐嚼,读之不难感悟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小说反映出打工群体存在的几个带共性的现实问题:诸如人性冷漠的危机,法律意识的淡薄,拜金主义的作祟,猎奇心理的蠢动,自省意识的缺席等等。小说注重细节描写和人物性格刻画,故事结局巧妙,其间采用怪诞的手法描写民工李小末由人变鸟的系列遭遇比较出彩,这当然是借鉴西方作家卡夫卡的创作手法。作品笔调冷峻,叙述客观。初读忍俊不禁,再读发人深思。打工者在城市用血汗浇铸脆弱的希望,承受着生命之轻,生存环境恶劣,生存空间狭窄,心理生理受损,是这个底层群体的挥之不去的梦魇。作者抓住这些关键性内容,塑造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底层小人物形象。小说所写的人事,虽然未必完全符合生活常理,甚至有天马行空之虞,但它的语境却是真实的,读起来煞有介事。感悟于此,作者无论是写一个乡村老头因怀念过去那开满鲜花的湖泊而离开了家,去寻找梦境中的湖泊的故事,还是写一个农民突发奇想教自己的牛跳舞,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故事,抑或是写一头驴要听人叫他爹才肯干活,因此惹出许多啼笑皆非的事,都表现了某种虚构、夸张、变形的艺术建构色彩,这种变形当然不属于生活的赐予,而归功于审美创造的神奇。
王十月的底层写作多有原型。他在选择原型时,只对那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坚守者情有独钟。王十月底层写作的成就的取得,也得益于他对文学前辈的学习和效法。他看书较杂,文学书自不必说,中医、占卜、历史类的书也在“吃进”之列。读二十四史,他加深了对人生的领悟。而读占卜志怪类的书籍,使得他的创作手法更为自由、诡秘。小说《活物》中人物个个像是梦游者;《31区》中那位名叫玻璃的小女孩以及那些猫,也是有点邪怪的。王十月喜欢给作品设定一些特定的氛围,这种氛围令读者一经接触便如鬼神附身,欲罢不能。也许读者会认为他的小说有些假,但很快便会忘掉这个“假”,进而享受阅读的快感。
三
《红楼梦》有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王十月底层写作的声名鹊起,也让人们对其所依托并表现的宝安31区刮目相看。所谓爱屋及乌。31区其实就是王十月的写作“根据地”。以《太平狗》、《马嘶岭血案》、《豹子的最后舞蹈》等神农架系列小说名震文坛的湖北作家陈应松认为,作家确实需要有一块能彰显其才华和思想的地方。王十月的成功也与陈应松不谋而合。“根据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开掘根据地的资源,如何进行审美概括,后者显得尤为突出。现在不少论者都对“底层文学”的艺术性表示质疑,这不是空穴来风。我读王十月的文本,与读有的打工者的作品感觉不太一样。前者深得小说写作之三昧,后者可能只是一个有着诉说要求的文学爱好者的作文,两者的悬殊是显然的。
深圳以及广东珠三角是打工文学的滥觞地。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打工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现象不可遏止地萌芽着和生长着,然而由于作者的写作水准参差不齐,造成了打工文学的影响和高度与理论界对其命名和期待的严重错位。整体上看,打工文学还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高度,它仍处于自发无序状态。虽然这些年文学批评界一直在为打工文学张目,但打工文学作为一个特殊文学现象,其所抵达的美学水准却不如人意,理论研究界对打工文学的支持呼吁也显得不够。一些评论家为打工文学的命名讨论不休。打工文学与“海派文学”、“军旅文学”、“湘军”、“陕军”相较,它还是一只正在生长期的“丑小鸭”,但让我们看到一线希望的是,广东出现了王十月、郑小琼这样的打工作家,他们正以自己扎实的创作实绩向世人宣告,“打工文学”正在向相对高度的文学纪录冲刺。现在,王十月的小说写作已经进入一个喷发期。他的小说虽然也还带有比较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但它们正在打破“自满自足”的狭隘意识状态,打破那种止于哭诉、止于苦难的低层次叙事。我相信,具有文学自觉的王十月会注意优化自身知识结构,拓宽生活视野,加强与文学界的交流,深刻体悟和反思当下的生活的。我看到,王十月的打工文学写作,将小我与大我的距离逐步地拉近了。有一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底层文学”写作者和倡导者强调题材或立场较多,而对打工文学的美学品质、艺术水准持过于宽容的态度。如何将现实关怀与美学水准结合起来,这将是“打工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王十月等打工文学作家所从事的“打工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性写作,它不仅在思想探索上具有先锋性,而且在审美原创上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王十月的底层写作是深圳打工文学逐步走强的一个红色信号。当然,打工文学自身必须加强自省意识,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提升的地方。打工文学需要在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上提升自己,迫于生存困境和压力,很多打工文学作者急于摆脱打工身份,以获取“主流”的关注和认可,也有人为了生存而媚俗,用低俗文字迎合市场口味。不少打工文学作品不痛不痒,或胡编乱造所谓底层爱情,读来很是没劲,打工文学需要补钙。市场经济时代,打工文学难免被商业化、庸俗化思潮冲击,有些打工文学杂志在市场压迫与诱惑下,从文学期刊向大众读物转变,纯朴的打工妹被有意无意贬损、污染,打工生活场景变成充满刺激的低俗故事的孽生地。打工文学虽是一个庞大创作群体,但总体看作品质量不高,更多是走庸俗化路子,以迎合地摊文学、下半身写作、二奶文学等市场化需求。有评论家认为,打工文学作家群缺乏思想性和艺术储备,打工文学缺乏积累和升华。打工作家普遍生活阅历较浅、知识面不宽、功底不够,导致思想褊狭、内蕴不深。相对于“主流”文学作家来说,他们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而且繁重冗长的底层劳作使他们不可能对作品进行深度加工。应该说,王十月是打工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和成功人士。但他的作品也还残留着一般打工作家身上的某些局限,要攀登上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他还需在“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两方面多下功夫。作家陈应松说,将来中国文学真正能“走向世界”的,必将会是底层文学。此言不无道理。重要的是,“打工文学”应该在思想和审美的两个向度上尽快成熟起来。
(作者单位:深圳报业集团)
牛bb文章网欢迎您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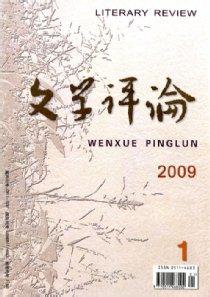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