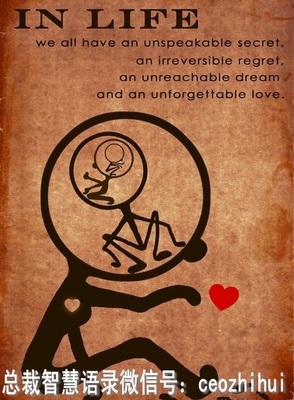Nilgun Kara
●●●一周前,我们在呐喊疫苗恐慌,我们呼吁彻查真相;两周前,我们在人肉领养泰迪狗喂蟒蛇的“人渣”;三周前,我们在当心人工智能超越人类……
现在呢?我们还记得什么?
这些不久前甚嚣尘上的热点都已经冷却,更不要说去年年底引起公愤的火车盒饭定价事件,去年九月被媒体刷屏的康师傅馊水油事件,八月天津震荡全国的爆炸事件……
是不是都忘了?
不仅仅是当下,几千年来,“健忘”的基因早已烙印在每一个国人的骨髓里——往前推一百年,辛亥革命中被要求剪辫子的男人死活不肯,好像他们都忘了曾经“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信誓旦旦,好像他们一直都留着辫子似的;往前推两百年,朝鲜使者为乾隆贺岁,他们居然成了街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就连太常寺少卿也好奇的问“贵处衣服,是尊何代之制?”,那些使节穿的,其实是才亡了一百多年的明朝衣冠啊!
深入骨髓的健忘,蚕食着我们的热情,蚕食着我们的恐慌,蚕食着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被历史的车轮碾成齑粉。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么健忘?
Nilgun Kara
| 我们把懦弱吹捧为美德 |
禅宗有一则广为人知的公案——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
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这种“变态”的宽容被无数大师学者称赞,甚至成为一种处世美学。但所谓“宽容”不过是懦弱的遮羞布。
对“宽容”与“知足”的诠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和中国人媲美,这种极端的知足与忍耐锻造了中国人的“健忘”,知足常乐,已经演化成乐极生悲的恶习。
我们已经忍耐了太多其他民族无法忍耐的苦难,但我们除了私底下小声的咒骂,再也没有其他反抗,没有反抗,无关痛痒,就会渐渐遗忘。我们一代人遗忘还不够,我们会把这种极端的美德编织成诗句、谚语、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唱,“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小不忍则乱大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们对自己的权益毫不在乎,只是一再退让,等退无可退时,我们又会告诉自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于是,我们越来越懦弱无能,知足的底线被一次次刷新,我们也一次次遗忘。
Nilgun Kara
| 我们把麻木伪装为超脱 |
在一本英文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布朗的母亲在他临行时嘱咐他要“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与儿子分别时通常的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这恐怕是再明显不过的对比了。
超脱老猾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任何理想与热情之花一旦接触这种智慧,只能瞬间凋零。超脱老猾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它徒劳无益,它使中国人散失理想,甚至麻木不仁。
那些越超脱的人,越会受到人们的膜拜称颂,比如“竹林七贤”,在那样一个乱世,七贤归隐山野,纵情清谈,没有任何变革的热情,没有任何担当与抱负。当然,你可以辩解说是因为那个乱世已经腐朽之极,无可救药。
奇怪的是,我们也崇拜敢于斗争的勇士,比如邵飘萍和林白水,他们死后,报业都纷纷纪念,“一样飘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成为千古名句。
但从那以后,每一个报社都学“聪明”了,那种狡猾的“聪明”居然延续至今。当今报业,爬得最高的记者就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他们喜欢处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讨论一般而非具体的问题,看看奴颜媚骨的报纸,卑躬屈膝的喉舌,谨小慎微的舆论,邀宠献媚的措辞,实在狡猾之极。
我们羡慕敢于斗争的人,但我们在羡慕的同时,看着斗争者的凄惨下场,我们也越来越超脱,因为活着就是我们最大的信仰。超脱避世,就像毒品一样麻醉着每个人神经,如何指望一个瘾君子有正常的记忆?
Nilgun Kara
| 我们不过是在权利的惯性下思考 |
当然,健忘也不全是我们的过错,除了知足与超脱,两千年来封建制度下的中央集权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马未都先生总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我们的历史是后人所评,所以历史的构建需要依靠人们的记忆,而记忆却是权力的产物。
纣王并没有那么荒淫,但在周朝的历史里,纣王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暴君;隋炀帝也并没有那么暴虐,但在唐朝的历史里,隋炀帝就成了昏君的代名词,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是最终的胜者,谁就是历史的化妆师。
就像《1984》里奥威尔的名言“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
《1984》里大洋国的真理部就是负责对社会记忆的消除和篡改,各种报刊不断的重写修改,只为创造统一正确的思想。而既知足又狡猾的我们就在这样的“大洋国”依靠惯性苟活下来。由此可见,自由思想与独立思考是何等重要。
Nilgun Kara
| 我们毁于我们所热爱的娱乐 |
曾经有时评家批评中国人脸上没有笑容,总是愁眉苦脸。但是现在随处可见开怀大笑的国人,但那样的笑是空虚的,是愚昧的。
疫苗事件仅出现在微博热搜一周不到,而“A4腰”的拼瘦风潮却挂在微博热搜榜两周有余,随后又出现了匪夷所思的“iPhone6腿”。
吴奇隆与刘诗诗的浪漫婚礼也同样排挤了疫苗事件,就像当初黄晓明与baby的婚礼让屠呦呦的诺奖喝彩转瞬即逝一样。
娱乐的浪潮前仆后继,热点层出不穷,疯狂的真人秀上演着真实的《楚门的世界》,我们还来不及记忆这个热点,它就会被另一个热点吞没在信息洪流之中。
我们厌倦悲伤,只想在网络上寻找笑点,就像中国最卖座的电影永远是喜剧片一样,我们看不懂悲剧的厚重,看不透悲剧背后的反思,只想莫名的笑着,笑的手舞足蹈,宛如一只只提线木偶。
我们用笑声打造出一个个迷幻的乌托邦,构建出一个个美丽新世界,讽刺的是,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当我们狂热追逐一件东西时,我们就会散失批判和筛选的能力。
娱乐至死,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精神的枯萎,一个精神枯萎的民族怎么会不健忘?
Nilgun Kara
| 我们原来是一只乌龟 |
我们层层解剖,挖掘出让我们健忘的“真凶”。
如果再往前追溯,我们会发现真凶背后还有真凶——是什么让我们不断的忍耐与宽容?是什么让我们超脱避世?是什么让我们打扮历史?是什么让我们娱乐至死?是由于两千年来集权制度下法律的缺失,当个人自由没有法律的保障和宪法的维护并且统治者高度集权时,知足与避世是最安全的避风港,是自卫的一种方式。
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

一只历经沧桑的乌龟,苦难让他的龟壳越来越硬,而我们芸芸众生,也只是一群正在修炼的龟。于是,我们就像乌龟一样的生活着,极少斗争,也极少反抗,这种防御策略比进攻还要可怕。
记忆,是思想的源泉,如果一个社会的群体没有记忆,思想的河流就会干涸。自然也就不会有反思,不会有质疑,不会有批判,群众就会变成真正的行走的干尸,直到为时代陪葬。
▼更多精彩内容:
日本女优为什么爱读书
中国人的恶发展到极限了吗
扬之水:袅袅馥郁妙香内,与您共醉一春风
俳句之美:那么短的句子,那么长的情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