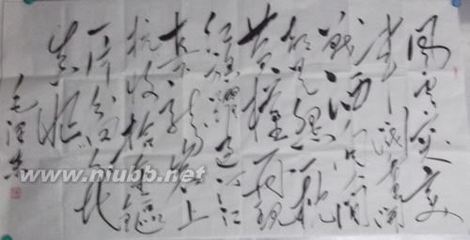《南海十三郎》一戏风行二十三年,数次复排,几乎都是全院满座,然而屈指可数的是,二十三年总共一百再过半百的场次,平均下来一年不足七场,也确实是令许多观众望“剧”兴叹。所幸电影版和舞台剧录像的传播解了观众的一些渴意,我就是其中一个。近来《南海十三郎》再次重演,我无法安坐书斋,于是偷来浮生半日闲,赴上海会“十三郎”。一戏下来,有感于此戏的成长与不足,更有感于东方剧场与现世的强烈互文关系,遂有此文。
一
《南海十三郎》是一个具有强烈东方剧场色彩的戏剧作品。这一点,见于戏剧结构,见于叙述方式,也见于复排的思路。
在我国古典戏曲的叙事结构传统中,多采用“点线式结构”,“线”多为时间线,显现出东方戏剧强烈的“时间情结”,“点”则是撷取时间线中主人公生命中关键的时间点。《南海十三郎》正是一个明显的“点线式结构”的戏剧。它完整地、基本顺应事件发展自然时间顺序地、从头到尾地进行叙述了南海十三郎的一生。纵观戏剧中南海十三郎的一生,除却开场与结尾,主要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懵懂期(少年十三郎-十三郎与太史公下棋论情)、风光期(十三郎度曲初露锋芒-十三郎唐涤生论戏)、转折期(日本入侵-十三郎怒砸任惜花)、失势期(十三郎写“猩猩戏”-十三郎跳火车)、疯癫期(十三郎与太史公疯癫下棋-十三郎死于街头)。这五个时期层次分明,且存在一种“轮回式”的对称:南海十三郎在其人生“懵懂期”与“风光期”所亲近之人,无论父亲、Lily、薛觉先、梅仙与唐涤生,在其“失势期”与“疯癫期”都一一重遇。南海十三郎的一生以“转折期”为界分为前半生的“热闹”与后半生的“悲凉”,前半生所亲近之人到了后半生,都试图帮助十三郎走出人生的困境:然而父亲门庭败落,唯能与十三郎下棋;薛觉先不解十三郎心意,“吓”走了他;梅仙报恩却触犯了十三郎底线,终也遁入宗教;知音唐涤生看似一道最猛烈的希望,却因急病去世而终成一叹。这样的“轮回式”对称结构让十三郎人生的悲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直至遁世不成下山,赤足死于街头,世上再无十三郎。
武汉大学郑传寅先生认为,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不同,西方戏剧有“空间情结”,时间服从于空间,以人物活动的空间为轴心,是一种“团块式结构”,如《俄狄浦斯王》;而东方戏剧则有“时间情结”,空间服从于时间,以人物活动的时间为轴心来结构剧情,时间跨度较大,是一种“点线式结构”,如《赵氏孤儿》。[①]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从根本上,这反映了东西方时空观以及思维方式的一种差异。《南海十三郎》除了东方剧场“点线式结构”的运用,还运用了“轮回式”的对称结构,二者相加运用,既成就绵长生命时间线中的故事讲述,也成就人生中“悲”与“喜”的奇异对照,同时,也令《南海十三郎》成为一个东方式的剧场作品。
《南海十三郎》是一个具有强烈故事性的戏剧,其叙述的方式也呈现出浓重的东方剧场色彩。在《南海十三郎》中,最突出的一种叙事方式就是“说书人”的运用。在戏的开场,这些“说书人”正如中国明清传奇中的“副末开场”,虽然不像“副末”般直接点明故事来龙去脉,但也像“副末”一样为观众导入了戏剧的情境;在戏的进程中,他们点明时代背景、串接剧情,他们嬉笑怒骂、点染戏剧气氛;在戏的收束处,他们照应前后,首尾相承,令故事有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说书人”承担起了《南海十三郎》中十分重要的叙述任务。在电影版《南海十三郎》中,担任起“说书人”这个角色的是一个落魄编剧,电影中的“说书人”又唱又说,恰如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深深地吸引着围观的民众。与戏剧中的“说书人”有别的是,电影中的“说书人”还承担起评论的任务,道出了“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天才,因为真正的天才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早死,要么疯掉”的劝世之言。“说书人”(叙述体)的运用在大多数戏剧里是被警惕的,因为它容易破坏戏剧惯常使用的“代言体”的叙述方式,且过度的使用容易导致过度“间离”,从而使观众无法入戏,现实中确实也存在不少因不恰当使用“叙述体”而导致剧情零散而情感中断的戏剧作品。这对于《南海十三郎》这样有强烈故事和情感色彩的戏剧而言似乎是不利的,但“说书人”在《南海十三郎》中却达到了一种完美的融合,这种融合有两个原因:一是“说书人”出现的时机是恰当的,基本仅在过场叙述中出现,而不随意干涉剧情发展;二是“说书人”拥有身份转换的能力,前一刻还是叙述者,后一刻就成为了剧中角色。实际上,“说书人”在《南海十三郎》中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存在,因为故事所讲述的是十三郎漫长的一生,存在有太多的历史情境与其他具体情境,如果没有“说书人”在其中进行介绍与衔接,剧情之间的时空转换较难完成。中国古典戏曲中,时空的转换更多依靠的是剧中人的自述与行动,他们可以直接成为自己的“说书人”,自报情境;当代戏剧中相似的的运用,可以在台湾《宝岛一村》一戏中发现,《宝岛一村》与《南海十三郎》的相似处,正是时间跨度的漫长。
先前1997年舞台剧版本的《南海十三郎》(以下简称“97版《南海十三郎》”)与现如今的版本的《南海十三郎》(以下简称“新版”)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舞台的呈现上:97版偏重写实,则无论太史府第、舞厅、戏台,都布置以较为写实的布景;新版则偏重写意,借用投影显现戏剧场景的象征物,舞台上基本布置以简单的桌椅,在本质上更契合于戏曲的“一桌二椅”精神。这一思路使得《南海十三郎》在舞台呈现上进一步表现出东方剧场色彩。97版在舞台呈现上存在换场不够流畅的问题,得益于演后与新版导演黄树辉先生交流的机会,得知黄树辉先生新版的导演思路,有一部分正是为了实现场次之间的“无缝连接”,而实际上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97版中对于竹子的运用是我较为欣赏的,竹子搭建的戏台,竹子搭建的“碌架床”,我对于广东大戏的深刻印象,有一部分来自广东唱大戏时常见的“竹子戏棚”,褪去了绿色的竹子虽然有某种粗粝之感,但却有一种质朴之气,十分适用于《南海十三郎》的舞台呈现。新版在装潢一新的剧场演出,则无论道具、投影,虽然简单,但也显现出崭新与精致,这在破败的太史府、在疯癫十三郎居住的“碌架床”,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另外,尽管我们应该赞赏导演在应用投影上的克制,但投影也仍然呈现出一些“异质”的成分,尤其是十三郎赤足死于街头,投影上一缕白烟升腾,雪山白凤凰飞走了,这一处令人有过于直白的感觉。还有一处令我感到不满足的,在于表演的节奏。可能是我多次观看97版录像,习惯了97版的节奏的缘故,此处仅当做我的一处吹毛求疵:十三郎收徒一段,唐涤生唱出“露湿双玉凫”,未等十三郎反应,就说出“也算挺押韵的吧”的心虚之言,此处唐涤生显然过于心急,于是在十三郎反应过来之后,只好用“后退一步”的方式表示心虚。我认为,在97版中,这段的节奏优于新版:唐涤生唱出“露湿双玉凫”,二人同时抬头望向对方,十三郎看着唐涤生,唐涤生自己感到心虚,支吾地说出“也算挺押韵的吧”。“也算挺押韵的吧”这话需要十三郎的停顿作为支点才有道出的必要,否则,这句话就应当是唐涤生用较为得意的语气说出,然后发现十三郎未有反应,才心虚后退。
二
《南海十三郎》是一个具有强烈东方戏剧意蕴的作品。这一点,见于《南海十三郎》悲喜交叠、苦乐相错、亦庄亦谐的情感表达。
西方戏剧中的“悲剧”和“喜剧”概念,向来难以完全套用在中国古典戏曲作品上,即使是王国维先生认为“列于世界大悲剧之林亦无愧色”的《赵氏孤儿》与《窦娥冤》,也常有争议与讨论,更惶谈更多的悲喜交叠的中国明清传奇作品:《西厢记》全剧生动有趣,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崔莺莺的“扭捏作态”何尝不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无奈之举,且如果《西厢记》真以“草桥惊梦”收束,何尝不可以看做某种悲剧;《牡丹亭》有悲剧的内核,但在剧情中绝不乏插科打诨。中国古典戏曲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大多没有一个绝对的情感定性,受儒学精神影响,更多的是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呈现出悲喜交叠、苦乐相错的“中和”之美,《南海十三郎》就是如此。
《南海十三郎》的开场与收束,“说书人”皆以一种超脱物外的态度向观众叙述,在开场词中,有“你喜欢这个故事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你会泪汪汪”、“今日你看人,他日人看你,慨叹无端哭笑又岂寻常”等句子,在收束词中,更有“人生如一梦,转眼又散场”、“祝君乐安康”等句子。可以看出,《南海十三郎》的开场与收束,都呈现出明显的“间离”意图,这个戏不愿意观众沉浸在悲或者喜的情感中无法自拔,而是借“说书人”之口,为将要开始的故事铺垫一重“间离”,也为刚刚过去的故事找到一个来自凡间的“出口”,当观众在剧场中看完《南海十三郎》,开怀大笑过,也默默哭泣过,最终在收束时被“说书人”拉回现实,走出剧场时,心中有一种“中和”的心境。
《南海十三郎》剧情中悲喜交叠、苦乐相错的“中和”之美也相当明显,主要体现在戏的后半场。后半场甫一开场,就是一场令人捧腹的“猩猩粤剧”,闹剧之后,就是十三郎的剧本被扔于地上,继而一个令人唏嘘的停顿,一个令人见怜的弯腰,这是一喜一悲;继茶楼中“死仔包”、“神憎鬼厌南海十三郎”、“机会就摆在你面前,错过你就后悔莫及了”的逗趣之后,就是看片场十三郎因不满剧本被改而被人打翻在地的惨状,这是一喜一悲;仍然是茶楼,先有“港督掩口费”的逗乐,后有“师徒对唱”的悲凉,再有“师徒相认”的欢喜,这是一喜一悲一喜;寺庙中,先有令人忍俊不禁的精通多国外语的十三郎当导游,后有太史公去世的噩耗,这也是一喜一悲。以上可见,在《南海十三郎》中,处处可见喜与悲的交叠,也处处可见苦与乐的相错。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喜”的部分,也常常伴随着某种“悲”,比如“神憎鬼厌南海十三郎”,就是十三郎的自我嘲弄。在戏的后半场,这些“喜”的成分不停地中和着剧情大走向中的“悲”,可见剧作者无意让《南海十三郎》的后半场成为绝对的悲凉,他用“喜”与“悲”的交叠与相错拨弄着观众的情感,最终达到了一种“中和”之美。
《南海十三郎》编剧杜国威先生曾经说过:“……我没有受过西方丝毫感染,它根本也不能感染我。”[②]杜国威先生对于西方戏剧观念的这种态度,恰恰反证了其对于东方戏剧观念的接受,而正是东方戏剧“中和”的创作观念,令《南海十三郎》实现了悲喜交叠、苦乐相错、亦庄亦谐的情感表达,最终使得《南海十三郎》具有强烈的东方戏剧意蕴。东方戏剧意蕴的审美,加上外在东方剧场的戏剧结构与叙述方式,辅以新版导演对剧本中东方剧场色彩的理解,最终共同指向了《南海十三郎》中强烈的东方文人精神。
三
时代从未停止它前进的巨轮,负担着思考天职的中国文人的精神该何处安放?这似乎是《南海十三郎》在深层次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天问,当这样的天问放在一身傲骨的天才编剧十三郎身上,一场传奇一出戏,就此生发。在戏的收束处,“说书人”告诉我们,“你们无需用脑去费思量,须知用脑用得多,会变成痴呆相”,我们自然大可将《南海十三郎》仅仅当做一个美妙的传奇故事看待,在其中大笑,落泪,最终中和,最终归于平静。但是,当时代的巨轮更加速度地滚向未来,全中国甚至全人类都不知道未来去向,更不知传统的精神应当如何安放,就已经被层出不穷的变化撕裂得矛盾丛生时,我们似乎也有必要好好地思量一下这个天问。有感于十三郎,有感于《南海十三郎》,我感受到了东方剧场作品与现世的强烈互文。
笔名为阿子儿的剧评人在《你真的读懂南海十三郎了吗》一文中将十三郎描述成一个“顶天立地”的传统文化遗子,认为“中国传统士人文化,到了这个时代已经走投无路,并不在于十三郎失端着或是不端着的问题,而是格局已变。”[③]这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十三郎在戏中体现出来的其痴、其傲、其风骨,其情、其义,其节,都十分清晰明显。但我更在意的是,如果我们仅将十三郎作为一个传统文化遗子的符号来看待,并借此指向中国传统士人文化的走向时,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抹灭了十三郎更多的个性,看不清他在其间真正的挣扎。
我们可以承认戏中的十三郎骨子里流淌的是中国传统旧式文人的精神,但他绝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士人:少年十三郎受“五四”精神熏陶,烧过校长蚊帐以反抗;香港大学读医科时期的十三郎,他仍然一袭旧式衣服,但其用英文编唱粤曲向Lily示爱,西方语言乃至文化对其的影响,绝不可忽略;成名之后的十三郎,并不局限于粤剧编剧,同时也投身于“时髦”的电影编剧;在教导唐涤生时,他清醒地看到粤剧的未来走向,绝不是一味通俗就可以俘获观众的心,可见十三郎并不是绝对“守旧”的人。但疯癫报警的十三郎,清醒地看到中国人的鞋(传统文化的出路),被两个贼(英国佬与日本仔)所盗,导致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无路可行,反应了其反殖民与侵略的思想。我们惊叹于十三郎这份惊人的历史洞察力,同时我们也明了,现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的博弈,早在十三郎这里,就已经展开了“殊死搏斗”。
十三郎固然有执念,在势必捍卫自己剧本的质量,不容他们随意篡改自己的剧本;也在捍卫演出的质量,誓不与“乞丐腔”的老马合作;更在于捍卫中国大仁大义、有情有义的传统文化精神。执念体现在冲突中,当没有异质文化强势侵略时,十三郎作为一个融会中西的中国旧式文人,并没有那么激烈与偏执,他更像是不停地在尝试突破,无论是写电影剧本,还是教导唐涤生目光要长远。可是当战争结束,娱乐至死的商业文化兴起,十三郎无法容忍的恰恰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全面抛弃,这促使他走向了时代的反面,致使十三郎在屡次的“妥协”之后,疯癫后半生。
值得注意的是,十三郎跳火车的直接动因,是Lily的重新出现,这朵“清丽脱俗的水中莲”,是十三郎心中不可侵犯的东西。Lily所象征的,正是十三郎骨子深处所守护的传统文化精神——这是十三郎幻想中的Lily,但同时Lily外在呈现的,恰恰又是新时代的形象与风貌。因此,当Lily再次出现,十三郎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那份可以守护的纯净不见了,他跳了火车。有趣的是,十三郎在与Lily跳舞时,幻想出来的自己,竟也是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新时代男人。不得不讲,十三郎对于时代本没有太多抵触,他是愿意融入的。但当这种冲突水火不容,沉淀在他骨子里对传统文化精神的那份深情,终于令他偏执,令他背时代而行,令他半世癫狂。
因此,我更愿意将十三郎看成一个复杂的矛盾个体。他的矛盾,不是他一个人的,在现世并不罕见,它存在于当我们说出“这都什么时代了”时长辈脸上的表情;它存在于我们在面对道德难题时的挣扎;它存在于我们淡漠又渴望温情的矛盾内心。《南海十三郎》这样一个具备强烈东方剧场色彩与东方戏剧意蕴的话剧作品,最终指向的是被我们忽略但又不时浮现的传统文化精神,它用一个戏告诉我们——回头看看吧,这里有你的先人,有你的祖辈,有你血脉中不可磨灭的东西。
剧评人任十一在《南海十三郎:八分好戏,尚未十分经典》一文中指出,“若说《南海十三郎》何处有缺,或许就是那一点少少自省。”[④]诚然,自省是必要的,但却是我们无法期待十三郎可以独力去完成的,这原本就不是十三郎一力所能承担的。十三郎自身的悲剧,大多数人总愿意归结于时代的原因,但我认为,十三郎自身的性情,也绝逃脱不了干系。我们为十三郎之才情所倾倒,为十三郎之傲骨所折服,为十三郎之痴心所感动,但十三郎之天才、傲骨与痴心,恰又是酿成其一生悲剧的另一个原因。以现世眼光去看,他的纵世天才,是他“不宽容他人”的根源;他的铮铮傲骨,是他无法向世俗妥协的心结;他的“痴心赢得是凄凉”,是强人所难的爱情。在十三郎疯癫的岁月里,唐涤生崛起了,《再世红梅记》同样盛演,那么十三郎的悲剧,还真的就只是时代的原因么?十三郎有一颗灼热的赤子之心,这样的一个人如若活在现世,或许不会如此悲剧,但也总有怀才不遇的可能,他是这么理想化的一个人,以至十三郎最好的归宿,竟是在戏中为我们所遥望。
然而我们还是被“雪山白凤凰”感动了,这样一颗灼热的赤子之心,这样爱恨都毫无保留的文人,始终在我们的精神深处,勾起一种来自已逝时代的心灵颤动。十三郎的出世与入世,他的“壮怀如我更何人”和“生就是死,死就是生”都令我们叹息。现世与《南海十三郎》这样一个东方剧场作品,就这样呈现出了强烈的互文关系。正是这种强烈的互文关系,令《南海十三郎》风行二十三年,经久不衰。这里有精彩的故事,有惊艳的人物,有令人捧腹与心有戚戚的情感,也有默默道出的盘亘在所有人心头的时代精神困惑,因此,它的全院满座也就可以理解了。它有东方剧场的结构与叙述方式,有返璞归真的舞台呈现,有东方戏剧悲喜交叠、亦庄亦谐的意蕴与风格,最终,它有勾连起所有观众情感与困惑的互文。那么,它日日夜夜在观众心中的回响与传世,也是可期的。

四
十三郎已绝代,谢君豪正风华,杜国威先生的笔触温润,导演们深谙戏曲三味。电影版《南海十三郎》在片尾打出了“献给全港编剧共勉”的字样,《南海十三郎》是一个编剧写给另外一个编剧的情书,也是一个编剧写给一个时代的祭文,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挽歌,因为在现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没有死去,它与时代的博弈仍然在继续。杜国威先生以温润的笔触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打动了观众。他期望着更多的编剧回头看一眼,这些温暖而残忍的过去入了戏,是不是同样可以令观众热泪盈眶,思量再三?他期望着现世人回头看一眼,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是否在现世真无一丝可留恋之处?未来从过去而来,未来纵然万分扑朔迷离,但我们的未来,永远无法建构在对过去的忽视之上。此文,同样献给我们的戏剧创作者们,献给现世里被时代撕裂而精神矛盾的人们,共勉。
[①]郑传寅:《东方智慧——中国古典戏曲结构艺术论》[J].戏剧,1999(4):83-90.
[②]方梓动.香港话剧访谈录[M].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 2000.
[③]见微信公众号“好戏”4月24号推送.
[④]任十一.南海十三郎:八分好戏,尚未十分经典[N].北京青年报,2016-4-26(B04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