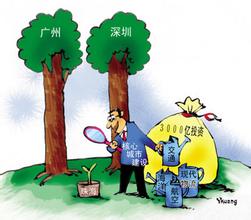“慢”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坏,而慢生活让我们有足够的耐性去关心粮食和蔬菜,去关心种子什么时候发出一颗芽,而秋天又是从哪一片落叶开始的。
16年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写了一本小说《缓慢》,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快慢”的时空交错的连环故事。
一天,米兰·昆德拉和妻子薇拉开车前往法国一个宾馆参加学术晚会,这个宾馆是由一个古老的城堡改建而成。来参加当天学术晚会的人群中,有一个来自捷克的昆虫学家,因为政治原因20年前被罢黜为一个建筑工人。此外,还有一个整日钻研如何在电视上“舞蹈”的政治家,一个企图靠勾引政治家完成自己舞蹈的女电视制作人,一个年轻的学生文森特和一个女招待员。他们匆匆聚在一起,觥筹交错,看上去好不热闹。但最后这些人都极为不堪:捷克昆虫学家受到嘲笑,被人打;文森特在泳池边和女招待交媾,居然阳痿。结果,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尽快紧遗忘这些不堪经历。
与此同时,米兰·昆德拉还描述了发生在该城堡的另一个18世纪的故事。
该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骑士被一个“T夫人”勾引,在夜晚与T夫人于花园中散步、做爱、再做爱。T夫人很享受与骑士相处的时光,她把与骑士的良宵尽量放慢,而她确实做到了,她把这个夜晚深深烙印到骑士的记忆中,而骑士则带着一份抹不去、也不愿抹去的回忆慢慢地离去。
夜晚过去,清晨悄悄来临。此时,最精彩的时刻到来了,米兰·昆德拉居然让18世纪和20世纪碰了面:“慢”的时代和“快”的时代的两个年轻人在即将离开城堡时站在了一起。一个是文森特,他希望赶紧忘掉昨夜自己在游泳池边阳痿的狼狈状态;一个是年轻骑士,他则希望在回家的路上慢慢回味昨夜的偷情。后来,两个年轻人交谈了几句,但发现都很讨厌对方,都不愿意到对方的时代去生活。
急躁的中国人
在米兰·昆德拉笔下,“慢”是指没有汽车电话的18世纪,出门要靠笃笃悠悠的马车,消息要靠磨磨蹭蹭的信件,那时候还有“游手好闲的英雄”。而这些到了“快”的20世纪,乡间小道、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在机器革命后,生活被装置上发动机,开足了马力,于是我们开始了转瞬即逝的生活,再也慢不下来。
虽然米兰·昆德拉要批评的是20世纪的法国社会,但书中描述的那些人和事、场景和故事、急躁和不耐烦,仿若是当下中国活生生的写照。
当下国人,都赶时间。吃饭要快餐,寄信要快递,坐车要高速公路或者高速铁路,坐飞机要直航。能坐电梯绝不爬楼梯,能加塞儿绝不排队,能走后门解决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
不仅如此,整个国家也在赶时间。五年计划,十年经济总量翻翻,增长率不能低于8%,城市房屋寿命只有30年,5年的教育压缩到3年完成,门前的道路一年中要被挖3次。
英国文化协会日前做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调查,每个城市随机抽取1000名成年市民,测量市民在随意情况下走过60步所需的时间。结果显示:香港人走完60步平均只需要10.8秒,上海人需要12.3秒,北京人需要12.6秒,重庆人最慢,需要27.3秒。与此相对应的是,罗马人需要30.7秒,而巴黎人需要37.4秒。
我们都患了“不耐烦症”,不能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似乎都在赶一场盛大的约会,但那盛大约会究竟是什么呢?
对,那约会就是死亡。
当代表中国速度的和谐号动车,在温州将40条鲜活的生命匆匆送走后,有人呼吁,“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其实,那只是无力的呼吁,我们根本等不了。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和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联合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仅有一成多受访者自认为健康。最常见的慢性疾病有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颈腰椎病、高血压、高血糖、痔疮、超重肥胖等。觉得自己“很糟糕,有慢性病”的比例达到了13.72%。在所有受访者中,七成受访者睡眠存在障碍,超过五成的受访者特别容易疲劳。
复旦癌症女教师于娟没能够让中国人慢下来,她用生命和血泪写作的博文虽然成为网络经典语,但那只是别人的故事,我们都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什么让中国人慢不下来?
1984年,柏杨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他这样讲中国人不喜欢排队的性格:“台北排队只算半截排队,上车排队,本来排得好好的,可是车子一到,却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立刻土崩瓦解,争先恐后。英雄人物杀开血路,跳上去先抢座位,老弱残兵在后面跌跌撞撞,头肿脸青。”
后来柏杨在其著作《丑陋的中国人》里进一步质疑了国人不排队的习惯,他说“火车汽车对号入座,座位是铁定了的,真不知道为啥还要猛抢。”
可惜柏杨没有给出自己的解释,所以后人帮他完成了,最被接受的版本是:国人习惯从众,认为越多人抢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由于缺乏独立思考,导致盲目跟从。
但真的如此吗?
或许这些人只说对了一小部分。国人爱抢,盖因供需不均、社会结构不稳定和现代科技所致。
试想,假如房子低到一个月工资就可以买一平米,那么还用得着彻夜排队吗?试想,假如每所学校的师资都一样,还用得着削尖脑袋将自己的子女送进名校吗?
庞大的人口基数,而可供分配的资源又少,这种严重的供需不均衡直接导致了国人凡事喜欢抢,从出生抢床位,到临终抢坟地,从头抢到尾。
供需不均导致的急躁可以通过扩大供给、减少需求来均衡,但是社会结构不稳定导致的急躁却无从改变。
因为社会结构不稳定,导致分配机制不完善和不公平,或者有分配机制却根本无法执行,这个时候权力上位成为唯一的王道,所以往往形成的局面是:权力通吃。因而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打尖。所以我们一定急躁,不顾规则。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规则和公平,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
除了供需矛盾和社会结构不稳定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元素使我们慢不下来,这就是科技。
想想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发明都在解决速度问题。以前交通主要依靠驴车和马车,现代社会则发明了汽车、火车,进而又发明了飞机、火箭;以前我们用一个月来等一封信,现在我们用10分钟来写一封电子邮件;以前我们用十天来抄写一本书,现在用10分钟来复印一本书。速度似乎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宝。
从“快乐”到“慢乐”的生活哲学
现代社会通过流程的标准化和管理的科学化,使得追求速度成为了可能,所以在现代语境中,标准化往往意味着快,而快的就是好的。
但这导致了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主义危机。米兰·昆德拉将之归结为一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也就是说,“快”是反记忆的,而“慢”才是记忆的亲密伙伴。所以,人们往往愿意记住愉悦和欢乐的东西,而非痛苦和苦难。从这个层面上说,“快”其实也是反愉悦和反欢乐的。
所以,当人们饱尝现代社会的速度之苦时,一股慢生活的风潮开始在欧美流行开行。20世纪80年代末,意大利开始兴起了“慢城运动”,一个名叫奥维亚托的小城拒绝快餐店、霓虹灯、汽车等现代文明的象征,倡导返璞归真的传统生活方式,以慢慢品味生活的乐趣。后来奥维亚托成为“慢城”的“范本”。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个城市加入“慢城运动”。
除了“慢城运动”外,“慢游”、“慢餐”、“慢爱”、“慢读书”、“慢设计”等生活方式也在全球流行开来。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慢”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坏,而慢生活让我们有足够的耐性去关心粮食和蔬菜,去关心种子什么时候发出一颗芽,而秋天又是从哪一片落叶开始的。
要慢下来,其实很简单,只需摈弃那些社会强加给你的价值观,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你最在乎和最乐意做的事情,然后以你的节奏去做。仅此而已,别无他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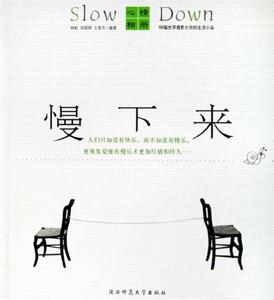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