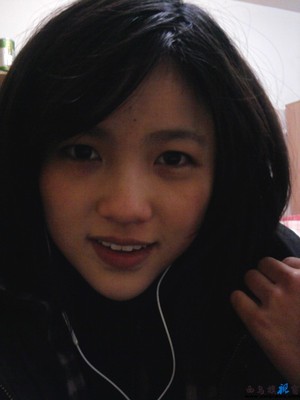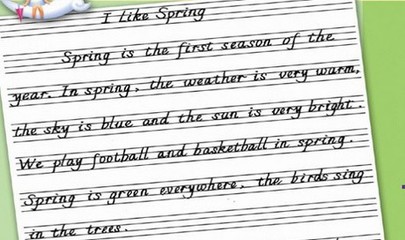Mia Liu
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的学校开始开设英语课,我也迎来了上学以来的第一位家教:一位长发披肩,笑盈盈的北大英语系学生。
第一节课,我和家教老师并肩坐在写字台前,父母坐在一旁读报看电视。家教俯着身子,一字一顿地向我示范英文发音。“Thank you,谢谢。Thank you。”
“Sank you。”我重复道。
“不对,是th—ank you。舌尖伸出来,”她探过头,上下牙轻咬舌尖,发出“嘶嘶”的声音。“Th—ank you。”
“Th—sank you,th—sank you。”我盯着她的舌尖,尽力模仿着。可不知为什么,我的舌头如同滑溜的泥鳅,刚一伸出来便不由自主地自己缩了进来。
“Th—th—ank you。”家教姐姐夸张地做出口型。
“Th—sank you。”在她热切的注视下,我脸部的肌肉仿佛变成了石头,不听大脑的指挥。一小时的课程在反复纠正这一个发音中,在我的困惑与自责中,一分一秒地渡过了。
***
在我的各种学习经历中,没有哪个比学英语更适合用“万事开头难”来形容。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经历过小学中学的无数节英语课,参加过托福GRE考试,习惯了在日日与英语为伴的外国生活,而当我回忆起自己的第一堂英文家教课,却仿佛仍然能感觉到当时湿漉漉的手心和僵硬的唇舌。
这样的感觉或许对大部分语言学习者都不会陌生:在奇怪的发音和陌生的句型前,我们的口齿和大脑如同生了锈的机器,需要靠时间和练习来慢慢润滑后才能运转。对于英文不同于中文的文法和规定——例如时态和第三人称单数——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对每一个动词都不敢掉以轻心,在遣词造句的同时,还忙着拿着放大镜给自己挑错。如此状态下,语言表达便没有原本的即兴畅快,而变得如履薄冰。希望传达的词句如同急于奔腾的激流,却被语言障碍这道大坝挡住,在脑海中不耐烦地冲撞、回环。
然而这样的状态不会无限地持续。在一切学习经历中,最能印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条信仰的,也恰恰是语言学习。在最初的阶段,语言学习基本上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在中国课堂里老师孜孜不倦的督促下,我们通过勤奋的练习,慢慢开始疏通最初表达上的阻塞感;在课后参加的英语班和夏令营中,我们在众目睽睽下开口时通红的脸颊也逐渐被从容和大方取代。在对照着中英字幕一集集津津有味地观看《老友记》时,戏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甚至会使我们偶尔忘却语言的隔阂,而慢慢意识到,英语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传情达意的工具。
随着心理上陌生感的淡化,我们的语言技巧也在悄悄提高。从苹果、闹钟和T恤衫到打印机、晾衣架和宇航员,身边的事物逐渐有了名字;抽象的概念更加难以表达,不过配上手势和表情,也可以开始磕磕绊绊地和美国人讨论《哈利·波特》和总统竞选。一点点地,语言开始回归它应有的角色。那曾经阻挡我们言语的大坝,似乎在渐渐松动。
大学一年级的一天傍晚,我和室友们晚饭后逗留在食堂,天南地北地侃大山。大家不知为何开始说起自家的独门菜谱,于是我也向她们介绍起我曾尝试过的一道名叫“凉拌西瓜皮”的凉菜。
“先把瓜皮切成条,然后在一锅热水中燃烧(burn)它们,”我左手比作菜刀,右手比作切板,做出切菜的模样。“粗细要合适,燃烧的时间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等到它们凉下来,再把它们冰箱(fridge)起来……”
坐在桌子对面的两名室友边听变微笑着点头。Julia的笑容越来越深,而Sarai终于忍不住乐出声。“Helen,在热水中‘燃烧’?应该是在热水中‘煮熟’(boil)!”
“哎呀,我知道。一张口就说出来了。”
“还有,‘把它们冰箱起来’的意思是‘把它们放进冰箱’?”
“对呀。”
“‘冰箱’不可以用作动词。你要把食物放进冰箱……”
“说得太快了就忘了,”我哈哈笑道。“你们听得懂不就行了?”
***
能够运用外语自如表达意思的成就感的确令人陶醉。我们感到多年的苦学终于有了回报,于是信手抓来飘浮在脑海中的词汇,抛出句子,让畅快奔流的话语不再被语法和用词所羁绊。对偶尔的疏忽,我们心知肚明却也心安理得。毕竟,英语老师不是一直鼓励我们要敢说敢犯错误吗?
此时,语言学习的未来似乎光明而一览无遗。我们迫不及待地眺望着前景:按照这个速度进步,和同学交流便会毫无障碍,听懂RAP的歌词指日可待,写英文论文时或许也不再会如此抓耳挠腮。语言学习的成功,似乎近在咫尺了。
直到从某一刻开始,我们第一次察觉到埋藏在奔腾的溪水下汹涌的暗流和漩涡。
“Sarai,你可以借我一点‘变化’(changes)吗?”我向正在埋头做作业的室友问道。
Sarai抬起头,一脸困惑地看着我。
“我要用楼下的投币洗衣机,”我举了举洗衣框。
“哦,你是说‘零钱’(change),”她恍然大悟,掏出几个钢蹦递给我。“‘零钱’是不加复数的。”
我愣了一下。“你说得对。”
在楼下的洗衣间里,我在滚筒隆隆的转动声中,思考着刚才看似微不足道的对话。在Sarai的指正下,我立刻意识到了用词方法的错误。然而在此之前,我却从未注意到我在运用这个词的时候和周围的美国同学有任何分别。这不起眼的瑕疵,淹没在繁忙的日常交流之中,让一直以为自己对言语中的错误清楚明了的我不禁自问:到底我的英文中还暗藏着多少如同这样让我尚未察觉的错误?
***
我坐在英文讨论课的圆桌旁,周围的同学安静正思考着老师刚刚提出的关于莎士比亚诗歌的阅读问题。我的课本摊开在桌上,上面布满着圈圈点点和马克笔的标记——老师的问题,我早已在做阅读时便开始斟酌,心中已经草拟出了一个答案。
“有人愿意谈谈吗?”老师对着鸦雀无声的教室问道。
我张了张口,刚要发言。“等等,”一个声音在我心中问道。“我能够阐述清楚我的观点吗?我的措辞是不是合适?或者,我的答案会不会太普通,太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一个同学已经开口陈述他的看法。我半失望半松了口气。我还是等到讨论像列车一样全速前进时,再发表自己的看法好了。在之后的讨论中,我等待着发言的间隙,试图做若无其事状将自己的回答插入其中。然而,每次我总在最后一刻被心中这般那般的疑虑牵制,咽回了已经到嘴边的答案。
在我还没醒过神来时,列车已经呼啸而过。
这是否只是一时的胆怯,或碰巧当天心情不佳?我之后责问自己,却意识到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原来只需十分钟便可写好的例行公事的邮件,如今却要花上半小时,原因是当我开始斟酌每一句话的用词口气时,总能找到似乎略有不得体而需要改进的地方;原本已经让人绞尽脑汁、挑灯夜战的论文写作,现在似乎永远没有了尽头。每一个形容词都好像可以找到更贴切的替代,每一句话都貌似可以换用更加漂亮的句式,每一个我过去烂熟于心的短语现在都要再次对照词典核查:这里需不需要定冠词?那里该用哪个介词?所有的问题概括成一行字,在我脑海中微微闪着红光:字里行间还暗藏着多少我尚未察觉的错误?
“我觉得我得了强迫症,”我向我的朋友们自嘲。“我没法停止改写我的论文。”
每当这样的时刻,我恍惚之间总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那个三年级的小姑娘,在第一节英语课上艰难地学习着英文中最易如反掌的发音。然而,如今牵制住我的舌头、笔杆和思维的不再是家教热切的注视,而是如同我初学英语时一样存在与自己脑海中的放大镜。随着我英文水平的进步,我学会了理解他人的表达,甚至逐渐培养出对语言的鉴赏力,然而自己言语中从前无从察觉的错误也在我眼中变得愈发清晰。
这样的觉悟自然驱动着我更加一丝不苟地提防着这些错误,争取让自己的表达变得更准确地道。然而它也为我的语言运用套上桎梏。小心谨慎取代了从前的大大咧咧。“在热水中燃烧”和“冰箱起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那曾经畅快奔流的话语如今变成一条潺弱的小溪,蜿蜒着避过岩石与坑洼,缓缓前行。
***
我的第一节家教课结束时,家教姐姐已经口干舌燥。她叹了口气,微笑地对我说:“没关系,下次再试试吧。”
我点点头,耷拉着脑袋和父母一起将她送到门口,听着她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
“那么简单的发音,为什么学不会呢?”妈妈口吻和气,其中却带着深深的不解。
为什么呢?我也默默重复着这个问题。
我独自回到写字台前,长长吐了一口气。屋里没有家长的耳朵和家教的注视,只剩下我一人。我用上下牙轻轻咬住舌尖。
“Th—ank you。”

高雨莘是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