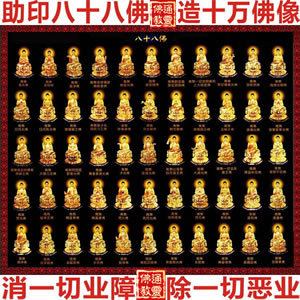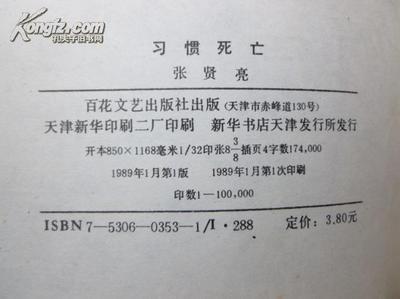众所周知,张贤亮在他的名作《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为我们塑造的是一个性压抑的男主人公章永璘,然而,他在《习惯死亡》中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与章永璘截然相反的男性形象“无名氏”,一个性放纵者。从性压抑到性放纵,张贤亮对于性的描写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也反映出了他创作前后期的不同特点。在《绿化树》里,面对美丽的马樱花,出于道德缘故,章永璘一再克制自己的情欲;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作为合法的丈夫,没有了道德的羁绊,他却失去了男人的特性,后来重振雄风后,他却又再次压抑了欲望,去追求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河的子孙》中的魏天贵对韩玉梅有着强烈的欲望,但他却始终克制着这份本能欲望,不敢接受韩玉梅对他的一份痴情;相反在《习惯死亡》里,主人公却把做爱看得和吃快餐一样的随便,以至《习惯死亡》在一般读者眼里,只会看到做爱与死亡。然而如果我们还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对它进行剖析的话,我们还是会发现它的意义仍在于揭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灵魂堕落的过程和意义。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个系统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起作用的,相互间应保持协调和平衡。约束和控制太强,持续太久,便会让自我十分不适,渐渐地,本我不是在压抑下心理扭曲变态,就是压抑不住而走向爆发,而这种爆发甚至有可能补偿性地走向事情的反面,本我不仅不再压抑,反而表现得更为过分。它冲破了自我和超我的羁绊,遵循快乐享受的原则,以感情、欲望为原动力,随心所欲地散播着盲目的激情而不计后果。最后本我的爱欲太多还会达到不能自制的地步,这时就会出现性上瘾。《习惯死亡》中的男主人公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好图解。他在年轻时曾经拥有过爱情,但是被错划为右派后,一切化为乌有,他虽然得到了平反,却再也没有能过上正常的合乎人性的爱情生活。他感觉幸福的那根神经已经不复存在了,长期以来外界的、人为的和内心本我的压抑已经把原本一个健全人格扭曲了,主人公的身心都发生了畸变。小说中的“我”深受本我的牵引,自我又找不到协调本我和超我的方法,在压抑未果之余,自我开始向本我倾斜。于是他以一种变态的心理到处疯狂地无休止地渔猎女色来麻痹自己那欲火烧心的痛苦。如果你问他喜欢什么,他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什么也不喜欢,除了做爱之外便是爱看狗打架”。他认为“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活力。即使从高昌故址的地下发掘出的千年尸蜡如果是女性也会引发人的遐想”。在他眼里,只有做爱才能证明他还活着,而实际上他这么做只会使超我的控制和自我的理性进一步丧失。肌肤之亲对性冲动巨大的唤起作用,几乎注定了“我”会更频繁地和女人做爱。因为欲火一旦被唤起就几乎没有了其他可转移的方向,乃至一再深陷快感之中,仿佛吸毒上瘾,而性又是个体最原始的本能动力之一,一旦出了问题再想挽回是很困难的。就这样,“他拖着支离破碎的身躯和灵魂全世界乱跑,到处寻找幸福的感觉,而在别人看来已经寻找到了幸福时,他却只感受到痛苦”。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他的幸福也是虚假的,痛苦也是虚假的,他的破碎已无可救药”。“不正常的社会进程造成了众多命运的不正常。他的不幸在于丧失了对幸福的感觉。”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文本的深层意义:“在假心假肺假胃假肢最后连人都能做假”的时代,什么恋爱冲动、真挚爱情都销声匿迹了,剩下的只有原始本我的冲动。如果说在《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男主人公章永璘身上除了具有本我的性质外,同时还体现出自我和超我的因素,而本书的主人公体现的则是地地道道的、赤裸裸的力比多精神。
我们通过文本可以归纳出主人公的人生模式:“出生,做爱,死亡”。在这个模式中包含着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推理:“出生”是生命的起点,“死亡”是生命的终点,因此,只有和女人做爱才是现实生活的意义。也就是说,“做爱”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只有不断地和女人做爱,他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做爱”对于他既是目的,同时也是意义,或者像叔本华所说的那样,性冲动是最后的目的,是生命的最高目标。确实,在男主人公思维模式和生活准则的背后,我们是不难看到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底蕴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投影的。主人公那盲目的,不可遏制的性欲是最接近于叔本华的所谓“生殖意志”,也类似于柏格森的“生命冲动”。但是在叔本华那里,性冲动或生殖意志是对生命的强烈的肯定,是繁殖后代,战胜死亡。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更是充满了创造的力量。但这儿主人公的“做爱”,只是一种毁灭的冲动,是直接导向死亡的,它表明死亡就在生活之中,死亡就在生命之中并且他习惯了“死亡”。张贤亮的《习惯死亡》展示给我们的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在那儿,人们信仰丧失,道德沦丧,充斥着无数像主人公那样行尸走肉般的男男女女。他们精神空虚,生活无聊,像主人公那样纵情声色地生活,葬身欲海或者如主人公般地习惯死亡。总之,看不见任何美好的事物,一切都“完了”。
在张贤亮的前期创作的小说中,总是弥漫着压抑的气息,本我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处处受到自我和超我的约束。而他的后期作品却总是充盈着一股反叛、放纵的暗流,不难看出《习惯死亡》就是一部字里行间充斥着赤裸裸的“情欲”的小说,难怪有学者认为“《习惯死亡》就是一部性放纵史,把一切问题都用做爱来处理,以性的游戏态度蔑视或无视其他物质的存在”。张贤亮在小说中对于男主人公的塑造套用的是“政治+女人”的小说模式。在他看来,“一个是女人,一个是政治。这两样东西给男人提供了生活的意义、乐趣和灾难。”张贤亮的作品中大都有性和政治两根轴线,往往是写性为辅,反映政治为主。同样,在《习惯死亡》中也是如此,正如主人公多年以后才认识到的那样,毁灭他的不是什么冤假错案,不是什么饥饿和上杀场陪绑,而是政治家给他开的玩笑。“只要有政党,那个政党便会犯错误,因为政党实际上就是一伙人。伟大的政党就是不断地犯伟大的错误和能够不断伟大地改正错误的政党。历史在这种循环中诞生和死亡。”“经过20多年的批判斗争坦白交代反复检查大会小会游街示众即席答辩”的主人公“懂得了如何投合听众的口味和掌握说话的分寸”,并且说得恰到好处,因为不会说话的人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都死了。“他虽然活了下来,但从此他便善于欺骗自己和善于欺骗别人。”然而,“语言之外的真实的现实常常搞得他痛不欲生”。他想反抗,却又无能为力,于是,主人公终日处于一种无奈、惆怅、麻木之中,落得只对性感兴趣,以肉欲的释放来掩饰他精神的失落和麻木。他一个靠思想和靠精神生活为生、以写作为生的人,只有在纵欲中才能激发一点写作的灵感,就这样无任何精神可言了,对人情世事陷入彻底的麻木和空虚之中了。由此可以看出,小说是通过主人公的性放纵、性堕落来表示对现实政治压迫的不满和反抗的。“完了”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在书中重复出现了11次,并且总是出现在主人公做爱前后。“完了”是主人公最真实的内心自白。显然,他说的“完了”,不是指生命的结束,而是指精神上的终结。他感到自己是不可救药了,对于“那些有恩于我(指主人公)的蹂躏过我的人都无力顾及了,报恩和报仇我都没有力气。在这个世界上我玩得太累!”正因如此,“他经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他的习惯”。虽然“数次死亡没有杀死他的肉体,但已杀死了他感觉幸福的那根神经”。就像是“生,对于一些人来说仅仅是一种习惯,一种惰性”一样,他已无力去死,“习惯”了受苦受难,“习惯”了“死亡”。这里作者想说明的是这些恶性循环的“习惯”把主人公推向了虽生犹死的深渊。
“生命”有两种含义: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我们通常说一个人“虽死犹生”,是指他自然的生命死了,然而他的精神却还活在人们的心中;而“死亡”也包括肉体上的死亡和精神上的死亡,一个肉体上死亡的人,在精神上可能依然栩栩如生,而一个精神上死亡的人,虽然活着却不过一具行尸走肉。《习惯死亡》中的“我”就是这样一个虽生犹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生命”和“死亡”能成为永恒的艺术主题和哲学主题的缘故。
张贤亮通过《习惯死亡》这部小说无情地剖析了人的灵魂堕落的过程,他通过“性”这一最能代表人的特征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这一“人的过程”。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承受其生活的庸俗和虚伪,想要反抗又明知无路可走,就甘愿以堕落来表示反抗,寻求解脱,渴望再生。正是在这一点上张贤亮对堕落人性的揭露超越了他以前的作品,使他又一次成为当代作家中的先行者。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WR004)
作者简介:田鹰,天津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 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张贤亮:《张贤亮选集(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周政保:《重读张贤亮的〈习惯死亡〉》,《小说评论》,第3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