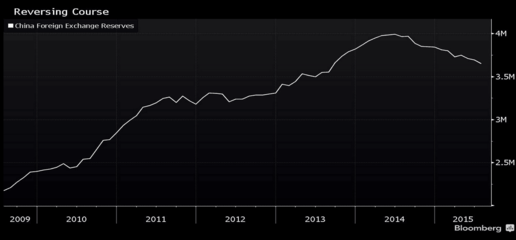120《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
“诗言志”补辩
王以宪
提 要 关于“诗言志”问题,已有众多论述,本文补析,主要从礼仪制度的层面来立论,内容涉及三点,一是志有“标识”之义,即是说,所谓“以诗言志”,就是将“诗三百”当成一种标志来看待,是将其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中区分等级的标记徽帜用以规范人们的礼仪行为。二是“志”作“情志、怀抱”解时,应用在各诸侯国及大夫间的交往中要区分所表达的是群志还是己志、是公志还是私志。三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它还要受到某种规则的制约和限制,尤其是在表达公志之时,更必须遵守“歌诗必类”的原则。但“歌诗必类”除示“恩好”之义外还有另一层含义,的规定,要与主人或宾客的地位身份相符合,不可越礼僭行,不可分。

关键词 标志 私志 越礼僭行
关于“诗言志”问题,,,,颇为详尽。本文再辩,意在补缺拾遗,细大不捐,,庶几能使其意义更加明晰周 。
一 志有标识之义。
关于“志”的解释,闻一多《歌与诗》曾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然后,他对其中两个意义进行了论述“:(其)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故《荀子‘解蔽篇》曰‘志也者臧(藏)也’”;文字产生以后“,记忆之记又孳乳为记载之
①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注》,云“:志,古书也”。朱
自清《诗言志》认为到了“诗言志”、“诗以言志”时,志已经多指怀抱(当然也包括情意、趣味)了。《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赵简子问子太叔“何谓礼”,子太叔转用子产的话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正义》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人又以‘意’为‘志’,又说志是‘心所念虑’,‘心意所趣向’”。(自注:分见《孟子・公孙丑》篇“夫志,气之帅也”赵岐注《礼记・,学记》“一
)②。他们所言,自然无差。笔年视离经辩志”
郑玄注《孟子・,万章》上“不以辞害志”赵注”
者认为“,志”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即“标志”,则所言者甚少。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周礼・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识,识,记也”,引《礼记・哀公问》注曰“志,读为识,识,知也”。所以“志”就有“识记”、“知识”之义。“惠定宇曰《:论语》‘贤者识其大者’,蔡邕《石经》作‘志’‘;多见而识之’《白虎通》,作‘志’”“,又旗帜亦即用识字,则亦可用志字”。可见“,志”作为标志、标记,其起源是识记,它也是一种记载,但目的是为了使人对所记之事之物的形态、内涵、类别、品级等有明确的认识、了解,并知晓对其所应持有的态度。因此,从记而识
①
②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诗言志”补辩121
之、认而知之的角度上说,所谓“以诗言志”,就是将“诗三百”当成一种标志来看待,换言之,就是将其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中区分等级的标记徽帜,用以规范人们的礼仪行为。应该说这是在礼乐文化的行为层面进行的一种新解释,它是在朱自清《诗言志》所归纳的四个层面(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①之外的第五个层面。
周代在举行典礼仪式时,常常要演奏诗乐。《仪礼・乡饮酒礼》“设席于堂廉,东上:
……乐正先升,立于西阶东。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 。工告于乐正,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仪礼・燕礼》亦有类似记载。这一段文字清楚地描绘了士大夫阶层在乡饮酒礼上用乐的情况。正乐乃是典礼上所规定演奏的乐章,多用 皇典丽的篇章,不出二雅、二南之外。
礼仪上的诗乐演奏,是有等级规定的,在何种礼仪上使用哪些诗篇哪段乐章,是与礼仪的性质、规格及参加者的身份、地位、等级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换言之,不同的阶层在不同的典礼上要采用不同的诗乐,而那些已经进入仪典的“诗”篇,会地位和等级的标志。一般情况下,大夫与士采用《、《小雅》《、二南》,如上文所引《乡饮酒礼》及《燕礼》。,:“《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或用《颂》,“:升歌《清庙》,示德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 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故有等级之分,不。《左传・襄公四年》“:(鲁)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
),不拜;工歌聘也。,金奏《肆夏》之三(即《周颂・时迈》《文王》之三,又不拜。歌
《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这是一段人们所熟知的话语,它正说明了典礼仪式上演奏“诗乐”的严肃性、严格性。本来,晋侯为了表示与鲁国的亲善和对使臣的慰劳,特别以演奏“重乐”来招待之,这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大约也是常事。但对于礼仪之邦的使臣来说,这可属于“僭越”的行为,当然他也明白晋侯的厚意,虽然不以为然,但也不好指责什么,只是采取不作为的“不拜”来表示。
而当对方问及之时,才明白地告知这种演奏“诗乐”是不符合礼制规范的。
《左传・文公四年》“:卫甯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肆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正义》“:诸自赋诗以表己志者,断章以取义,意不限诗之尊卑。若使工人作乐,则有常礼,穆叔所云《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礼也;燕礼者,诸侯燕其群臣及燕聘
①同上。
122《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
问之宾礼也,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如彼所云,盖尊卑之常礼也。自赋者,或全取一篇,或止歌一章,未有顿赋两篇者也。其使工人歌乐各以二篇为断,此其所以异也。此时武子来聘,鲁公燕之,于法当赋《鹿鸣》之三,今赋《湛露》、《彤弓》,非是礼之常法。《传》特云‘为赋’,知公特命乐人歌此二篇以示意也。此二篇,天子燕诸侯之诗,公非天子,宾非诸侯,不知歌此欲示何意?盖以武子有令名,歌此疑是试之耳。”。可见,典礼仪式上的用诗,有两种情况,一是按礼制规定奏唱《诗》,篇内容应切合人物的身分,亦即是说,《诗》之篇章已成为区别尊卑的的标志,不能逾越,否则,便不为人们所接受。二是赋诗,断章所取之义必须足以表达赋诗者的思想情感或要求,但同时也要注意不得随便取用那些明显带有礼仪标志的诗篇,如诸侯相见不能赋《清庙》,诸侯宴飨大夫不能赋《文王》《、湛露》等。上述两例,晋侯、鲁公凭一时高兴而提高礼遇等级,虽属好意,实质上还是越礼、违礼,故依然不为穆叔、甯武子所肯定。所以说“诗言志”,,从礼仪的角度来看,确实可以解释为《诗》是显示等级、尊卑的标志。
再从“观志”角度看,赋诗者“称诗以谕其志”,他人则可通过其所赋之诗来观其人之贤不肖及盛衰。其中亦可见出某些诗篇的等级观念与尊卑标志。《左传・“:令尹(楚公子围)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对曰‘:王弱,令尹强,!《诗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于下,。”“《小宛》《诗小雅》,。,,不可复还,以戒令尹。”按礼制规定,,已自露篡权夺位的野心;。叔向认为,公子围以强克弱,虽能逞其所欲,但“不义而强,由此可见,有些诗篇确实是明显具有礼制标志的,且为人所共知,在。
另外,有些诗篇,如“二南”,在聘问之礼上可以用来赋诗言志,而在另一种礼仪上却又成了区别尊卑的标志。《周礼・春官》“: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
《狸首》,大夫奏《采 》,士奏《采蘩》”。《礼记・射义》“: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其节,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 》为节,士以《采蘩》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 》;者,乐循法也《采蘩》;者,乐不失职也。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性立。”。射礼在古代也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是天子选拔诸侯卿大夫士的礼仪,目的是使之“尽志于射,以习礼
(同上)。乐”《驺虞》《、采 》《、采蘩》皆乐章名,在《国风・召南》,惟《狸首》在《乐记》。《驺虞》,先儒认为是天子之乐“,乐得贤者众多,叹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节也。而用之者,方有乐贤之志,取其宜也。其它宾客卿大夫则歌《采 》”。可见“,诗三百”的某些篇章,确带有很明显的礼仪等级标志而为时人所熟知,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 志分群己、公私。
就“志”最常见的解释为“怀抱”“、情志”这一角度来说,有的只代表个人的情感、看法和态度,所谓自抒胸臆,这可称之为“己志”、“私志”;有的代表群体的情感和看法,虽表达者是个人,但其“我”非“自我”,而是他“我”或是“我们”,故其志当属“群志”;有些情志的表
“诗言志”补辩123
达者虽是大夫士,但明显代表了某诸侯或“国家之志”,则应当算是“公志”了。或许有人认为如此区分并不规范乃至繁赘其事、毫无必要,但等后文言及“断章取义”的原则之时,自会明了其作用。
在献诗陈志、作诗言志这一层面上,其所表达的当然主要是己志、私志,如《国风》与
(陈风・“二雅”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如此《诗》,本身也多所言及“:夫也不良,歌以讯之”《
)“是用作歌(小雅・)“(大雅・墓门》,,将母来谂”《四牡》,吉甫作诵,……以赠申伯”《嵩)。但有相当的诗篇同时还表达了群志、高》公志,尤其是讽谏诗、怨刺诗,如“家父作诵,以
(小雅・)“(大雅・),还有究王 ”《节南山》,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民 》《魏风・硕鼠》《、秦风・黄鸟》《、邶风・新台》等。故《毛诗序》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孔颖达疏“: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者一国之事”“雅亦天下之事系一人”,,并且还将其总结为“诗述民志,乐歌民诗”。
在赋诗言志的层面上,用在私室典礼上的,所言之志自然是私志,如《国语・鲁语》所载“: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而为赋《绿衣》
之三章。”又如年》,齐庆封聘鲁,叔孙与庆封食,不敬。。虽然行聘礼是代表国家而来,但叔孙私人款待他,,,与鲁对齐的态度无涉。而当直接用,时,其所表达之志只能是公志了,“郑伯会公于 ,一请平于晋公”,,实际上是代诸侯表述,所言之意当然是“。
“?我们知道,有“言志”,同时就有“观志”。天子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派行人赴各国采诗,目的是知风俗之薄厚,考王政之得失。在诸侯国交往的聘享礼仪上卿大夫“称诗以谕其志”,实际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表示与其国之间的盟好亲善的交谊(公志),同时也表达了个人对来使的称美之情(私志)。而来使也正是通过所赋诗的不同以观赋诗者人品的贤不肖与其家族的盛衰
。这就有必要区分“志”的公私以避免误会。《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等七大夫作陪。赵孟说:“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由此可以看出,从礼仪角度上讲,只要按一定的规范演奏诗乐即可,而勿须所有陪宴之臣人人“皆赋”,众大夫的赋诗言志只不过是为满足赵孟的请求而临时增加的节目。赵孟提出要“观七子之志”,这明显的是观私家之志,所以当伯有赋《鹑之贲贲》时,赵氏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以“人之无良”来讥刺郑伯,既不表示他对自己的态度,更与郑国的诸侯之志了无干涉。《左传・襄公十四年》:卫献公招待孙文子之子孙蒯饮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讥刺孙文子“无拳无勇,职为乱阶”。大师知道这是献公在发泄私愤,故虽是公之命令,也敢于推辞。而师曹自告奋勇地“请为之”,实际上也是为了报被献公鞭打三百的私仇,所以不歌而“诵之”以怒孙蒯,使其矛盾更为激化,最终导致孙文子作乱。应当说,献公的赋诗显示了他的狭隘偏执,大师的推辞是以国家安定的“公志”为准则,而师曹挟私仇的举动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论歌诗必类。
众所周知,赋诗言志的方法是所谓“断章取义”,语源来自《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所载卢蒲癸的比喻“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即是说,用诗者不必顾及全篇大旨,只是任意截取
124《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秋之卷
某一章乃至某一句诗来表达己意而已。但是“,余取所求”只能用在表达一己之私志时,如《左传・文公四年》《正义》所云“:诸自赋诗以表己志者,断章以取义,意不限诗之尊卑。”不过在表达公志之时,不能或不完全能“随心所欲”。它一是要受到常规礼仪的制约和限制,如《左传・文公四年》《正义》所云“:若使工人作乐,则有常礼。……此时武子来聘,鲁公燕之,于法当赋《鹿鸣》之三,今赋《湛露》《、彤弓》,非是礼之常法。”二是必须遵守“歌诗必类”的原则。“歌诗必类”出自《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杜预注“: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正义》,曰“:歌古诗,各从其恩好之义类。高厚所歌之诗,独不取恩好之义类,故云齐有二心。刘炫云:歌诗不类知有二心者,不服晋,故违其令;违其令,是有二心也。”类,本作 ,据《说文解字》所释为“种类相似”,段玉裁注“:《释》《、毛传》皆曰:类,善也。”故此,所谓“歌诗必类”,是说在典礼仪式上赋诗言志,既要符合聘问宴享的气氛,更要表达美善的情意。高厚所赋之诗究系何篇何章《左传》,虽未录,但肯定与当时的气氛不相符合,与晋侯之令相左。当时,齐、晋两国正争夺中原霸主地位,齐自然不愿听命于晋;罚其侵鲁,更激化了两国间的矛盾,所以高厚言乃表示齐之国家公志,所以才引起晋国的愤怒,外交的正式场合,。前文所引晋、郑“垂陇之会”伯有赋,不过泄的是“私愤”,,也不必遵守这一原则,。此外,由“类”的“种类相似”之义还可以推出“歌诗必类”(主人或宾客)的地位身份相符合相比称,,不可不顾地位身份而越礼僭行。如前文所引《左传・襄公四年》晋侯享鲁穆叔,其所赋《文王》诸诗,想表达的情意可谓是极善极美极恩好的,但与诸侯宴享大夫的场合及各自的身份不相比称,因此并不妥当,也可以说是不相“类”
。
自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礼便成为了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其行礼的范围、规模、程序、仪态、礼器以及行礼者大致的言行,都有了相应的规定和限制而不容违反。虽然春秋之时“,礼崩乐坏”,诸侯士大夫不时有僭越礼制的行为,但亦不乏极力维护者,仅在“赋诗言志”这一点上,鲁穆叔、卫甯武子即是。总体上看,春秋“赋诗言志”基本还是符合礼仪制度的规范的。只是到了战国时代,周礼才彻底崩塌。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曾将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礼制作过一个比对,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左传》记年之终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前468-前334)],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这是后话。
(作者通信地址:(王以宪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330027)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