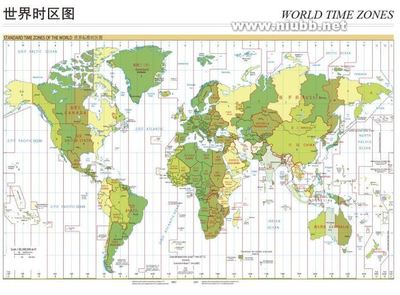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交流。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的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我国古代文化正是在不断博采外域文化中走向雄浑壮大的。自汉代通西域开始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纪元,中外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如果说秦以前是我国本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期,那么从汉代开始,便进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五千年博采众长而形成的深厚的中国文化固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而祖先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吸收外来文化的规律也同样是我们今天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有选择地并加以改造地吸收。因此,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过程(或者说外来文化的传入过程)其规律一般是:选择——实践——改造——创新。这一特点与规律尤其是在汉唐时期吸收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完整。像汉朝、唐朝这样文化灿烂的时期,中国不仅不会采取他国的制度文化,对物质、精神文化也不会没有选择地吸收,不过有的选择很快,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有的选择则经过了一段时期的被接受后又被淘汰。一经选择之后,就开始实践。而外来文化也自然地设法适应本土的文化。比如佛教为了能在中国传播,先是向原始道教靠拢,以至于使人们黄老浮屠难分,把它当作神仙方术的一种;继之又以“空”套“无”,使自己的教义得到传播;佛教徒口说“不敬王者”,实际上力图取得当权者的支持和援助;僧人与各种士人广为结交,通过与他们在一起活动,宣传佛教。总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适应中国国情,而中国却并没有被“佛化”,相反倒是佛教被“华化”。中国人创造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并将其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使其与儒、道并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为各种文化艺术形式注入新鲜血液。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中国对于外来佛教的吸收也堪称我国以我为主,取外来之菁英,创造发展本土文化的典范。本文以汉唐时期中国佛学、中国哲学以及中国的多种文化形式对佛教文化的吸收为例,初步探讨汉唐时期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规律与特点。
佛教传入中国与禅宗的诞生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为古老的,它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与各种文化形态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佛教的出现可以说是对古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和重大变革,是古印度文化的代表。佛教虽和其他宗教一样具有其信仰理论,但在人生观上强调主体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其理论更重视考察人生的现实问题、对人生作出价值判断、寻求人生的真实,而不是只关注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它的理论蕴涵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佛教创立之后,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复杂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主张平等、慈悲的伦理观念;形成了规范信徒的宗教生活、激发信徒宗教情感的礼仪制度;形成了传播和强化佛教思想的文学艺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佛教文化涵盖了整个印度社会生活。尤其是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2世纪时分别得到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的信奉和扶持,在国内外得到空前繁荣和广泛流传。
佛教在古印度的发展有以下几个阶段:最初是原始佛教,其后自公元前4世纪左右形成了部派佛教;至公元一二世纪间,又从部派佛教大众部中产生了大乘佛教;最后其一部分派别又与婆罗门教相调和,产生了大乘密宗。印度本土佛教自公元9世纪渐趋衰微,到了12世纪左右,逐渐溃灭。此后,世界佛教中心东移至中国。然而佛教并不是在12世纪才传入中国,而是在大乘佛教的兴盛期即中国的两汉之际就传入中国,并从此开始了它在中国为求得生存和发展而接受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改造,并最终带上中国色彩的过程;同时中国也开始了有选择地、加以改造地吸收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新文化的过程。
首先,是以恢弘的气魄敞开国门,能够容纳外来佛教——西汉末年,它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缓缓地踏上了古老的中国大地。西汉时期的中国虽已具有在当时来说相当发达的经济文化,但先秦时期延续下来的哲学思想抵制了宗教的发展。从宗教思想看,我国古代没有出现定型的宗教。像佛教这样组织、教义都十分完整的宗教,中国还没有过。它提出的许多宗教观念、宗教理论都是新鲜的。但即使如此,中国也没有对佛教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乘”是梵文的意译,原意为“乘载”或“车辆”、“道路”的意思。它的教义旨在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轮回之此岸到达涅解脱之彼岸,而不坚持原有教义,只求自我解脱。大乘佛经的主要内容都是说佛身常在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且明确了“我”的含义。这些都是和早期佛教相违背的,甚至并没有在印度得到广泛流传或产生很大影响。而大乘佛教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却与中国传统的“人人皆可成尧舜”暗合;大乘佛教“自度度人”的弘通思想,关于入世舍身、普渡众生的主张更适合中国人受自传统的入世精神,更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大乘经典主张的“不离烦恼而得涅”也适合中国人注重现世生活的习性。因此大乘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了中国人的欢迎。相对来说,小乘佛教在中国虽也有一定影响,但远不及大乘佛教的影响那样深远和广泛。显然,中国人选择了大乘佛教是根据固有的传统文化性格所决定的,是体现了以我为主的原则的。再者,大乘佛教的理论观点虽与原始佛教有很大差异,但大乘思想却是对佛陀教法的进一步发挥与完成,特别是在信仰和伦理领域把宗教的世界观发挥得更彻底、更系统化了。它的高度精密的哲学思辩与宗教幻想的巧妙结合,也适合当时中国人文化发展的高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决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在吸收中有选择,采撷外来之精华。这既是在吸收外来文化中所做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直接影响到吸收的结果,决定了吸收是否成功。为了发展本土文化,一定要吸收外域文化,但吸收一种外域文化的哪些方面,怎样吸收却是个难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谁都可以认同,但却不是谁都能找到找准一种外域文化的精华所在的,即找准吸收对象。那么怎样才能找到找准某一种外域文化的精华呢?这就要求吸收者本身要具有一双慧眼,具有一种能正确识别真伪、判断是非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的。中国在吸收外来佛教时之所以能取其精华,以我为主地选择了大乘佛教,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之上的。所以,我们只有在不断提高自己辨别问题的能力,提高自身素质的前提之下,才能真正地做到取他人所长;当我们想广泛吸收外域文化以利于本土文化时,也必须要从加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学习、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上入手,才不会误入歧途。
一旦选择了大乘佛教,中国便开始对它进行实践与改造。这一过程的突出表现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当时流行的老庄学说来说明佛教教理的“格义佛教”。“格义”是梵文的音译,是概念的对等。也就是说“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习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学说(的一种方法)。”这被认为是“中国学者企图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第一种方法”。比如以“无”译“空”,以“生死”译“轮回”,以“无为”译“涅”等等。但是这种只停留在名词和概念上的对比,不可避免地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和曲解,于是中国的思想家们认识到,掌握一种思想体系内涵的深义,远比之于概念、名词或者浮面浅薄的知识更为重要。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言意之辨”。这种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对于佛教的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印度佛教思想在这个时期被越来越多、越来越完整地介绍和阐扬的同时,也被越来越深刻地加以改造。其时译经盛行,且译者态度认真,梵汉兼通,儒释兼修,许多经典一译再译,多达十几次。在这过程中必然又逐渐融入并形成了译者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为以后中国佛教各学派的兴起做了文献和思想的准备,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中国佛教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在隋唐时期以宗派形式表现出来。宗派佛教成为印度佛教在中国土壤上的变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产物。在这方面,中国再一次凭借本身固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凭着前人对佛教的消化与改造,以“六经注我”的精神,另辟蹊径,自造家风,自成系统,以自家的理解对释迦一代说法进行重新编排组合。天台宗、华严宗的糅合百家、兼收并蓄,为以“心”为宗本的禅宗的产生和发展铺平了道路。至禅宗六祖慧能对传统的禅学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后,则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已衍化为中国化佛教,标志着中国在吸收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化佛教——禅宗。“中国禅宗既不像小乘佛教那样宣传出世迷信,也不像大乘佛教那样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偏重在现实人生心理调整上下功夫。”“禅宗的精神,完全是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的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的第一步。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钱穆的这一番话不但指出禅宗的精神,更暗示了中国的禅宗要高明于印度的佛教,以至有“中国佛教特质在禅”之说。中国佛教的这一特色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改造和发展,外来佛教就这样纳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
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中国宗教思想界吸收外来佛教并创造出中国的佛教这一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完成对一种外来文化的吸收并不是吸收者的某一方面或吸收者单方面的努力可以达到的,而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印度佛教被良好地吸收创造,宗教思想界学者们付出的努力自然不可低估,但汉唐时期经济强盛、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文化交流的良好局面的形成;多数帝王统治者的信奉与提倡,老百姓的精神需要与信仰;佛教文化本身的文化价值和佛教徒的传教热忱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反过来说,佛教作为对古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它的传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与启迪。
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曾被概括为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撇开佛教传入前的先秦诸子学和两汉经学不论,自佛学的系统传入便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先是与魏晋玄学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代学风,并引起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形神之争”。然后经过中国六百余年的消化,被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家心性学说以及孟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至隋唐终于被改造为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相继崛起于隋唐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便是代表。隋唐二代佛学成为当时社会势力极大的一个思想潮流,以至许多著名学者都主张在谈隋唐哲学时不能把佛学排除在外(否则隋唐哲学就会变得很单薄);主张把隋唐佛学同儒家哲学同等看待,都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人感到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哲学史基本上是佛学在中国被吸收发展的历史。至于宋明理学,则更是深摄佛教思想。新儒学派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使之与易、老、庄三玄相糅合:如二程宣扬的“理”套自佛教的“真如佛性”,只不过赋予了更多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也有若干内容采自佛教禅宗、华严宗的思辨。宋明理学不但在理论纲骨上吸收佛教哲学之所长,甚至在修行方法上也提倡类似禅宗的明心见性,一悟尽透。乃至近代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称宋明理学为“儒表佛里”或“阳儒阴释”。可见,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终于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不正是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上的创造性转化的又一范例吗?这一范例还进一步形象地揭示了文化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文化交流,决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某一种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均发生变迁,并从中产生出具备双方文化要素的新文化组合。在改造了的儒学与改造了的佛学相糅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宋明理学;改造了的印度佛教与传统的中国思想相糅合产生的中国禅宗,正是这样的新文化组合《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在我国被译成汉文及晋朝以后译文的丰富,数千卷佛教经典中一部分本身就成了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法华经》、《维摩诘经》历来为文人所喜爱,有时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和欣赏。可以说佛经本身的翻译,就是我国翻译文学产生的标志,使之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六朝时代,一般文人吸收了佛教中谈鬼说神的寓言故事及中国古代流行着的神仙传说,开始写作鬼神和怪物的故事,这就产生了我国文学上的新文体——鬼神志怪故事,如《拾遗记》、《搜神记》等。到了唐代其内容更加广泛,写作上更加讲究,于是发展为“传奇小说”。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常说因果报应、入冥转世、南柯黄梁、幻化诙奇,这些多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掺杂着不少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观念,因此文学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调。除此之外,唐代文学中受印度影响的还有“变文”——大多是演唱佛教故事,其内容有些亦取材于佛经,是一种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文体,在我国的敦煌石窟中有大量发现。此后的中国评话、评书、戏曲、通俗文学等都深受其影响。
佛教与诗的渊源也很深。佛教的传入不仅使魏晋的玄言诗死灰复燃,还为诗歌创作丰富了新内容、提供了新的境界,而且随着佛学的盛行,许多诗人涉足佛教。结交名僧、自许询、王羲之与名僧支遁交游开诗人与名僧交游之先声,白居易与鸟窠禅师、苏轼与佛印禅师等的交游都为中国诗坛留下了许多佳话。而历代诗人中崇佛最甚者当推王维。他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并与慧能的嫡传弟子神会有直接的交往,连他的名号都取自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取号“摩诘”二字。而到了晚年,他更是“长斋奉佛,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这也使他的诗常常深含佛理禅趣、含蓄隽永、神韵超然。如他的《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过香积寺》中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等都是字字入禅之作,是以禅喻诗的代表作。他或写田园山水,或写花鸟树木,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他既写山水景物,又不局限于山水景物,而把自己所感受的禅境,所领悟之禅意,与清秀灵异的山水景物融合在一起,没有直接言佛谈禅,但在言表意外却寓有佛理禅意,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悟,难以领略”。而以“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而自诩的苏东坡,其《琴诗》则引《楞严经》“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的经语佛意,引佛理、禅意入诗中,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则是唐宋诗坛上出现的“以禅入诗”的代表。历代名僧也多有佳作,史称其为“诗僧”,其作品更是独具情趣。如王梵志的《吾富有钱时》、寒山的《杳杳寒山道》等。他们的诗平实质朴、自然洒脱,既无华丽精彩的警句,也少艺术描绘,似乎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多指事直说、浅切形象、言近旨远、发人深省。这种诗风对后来的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等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代时据说是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有首既通俗浅近,又深蕴禅理的好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此诗描写农夫插秧的情景,但其“低头见天”、“心地清净”、“退步向前”则深含佛理禅机。且不说“心地清净”是佛家语言,其低头见天,实谓应该低头看世界,反观看自己。至于“退步向前”,则更含有佛家忍辱为上,慈悲为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思。此外,一代诗圣李白虽以耽道著名,但也传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之句;杜甫虽崇儒,却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虽佛道兼修也最终皈依佛教,自号“香山居士”。正如他在《赠杓直》诗中所说:“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
可见,诗与禅的关系,正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所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也就是说,诗的形式使得禅客谈禅不但花样繁多,而且文采飞扬;而禅的方法则使诗别开生面,另具境界。
外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正如历史上的诗歌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与佛教也有不解之缘。且不论历代书法家中,不少高手出自释门,如狂草怀素,“退笔成冢”的智永,唐草无出其右的怀仁,工草隶的贯休等;或书法名家深受佛教影响,如王羲之等,单是佛理便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深刻内在的影响。人们知道,佛法虽广,其要者无出于戒、定、慧三学。夫戒者,主要是收束身心;定者,则在专志凝神;而般若智慧,则使人穷妙极巧。此三者均与书法之道相通。其中,尤以禅定之功与书法之道最为密切。汉蔡邕《笔论》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书圣”王羲之也说:“夫欲书者,先凝神静思,预想字形,令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柳公权则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些议论,都深契佛家禅观之旨,可见佛理与书道实多有相通之处。

与书法相比,画家涉足佛教者更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许多画家染指佛画。最早的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卫协和顾恺之,又如南朝之张僧,北朝之曹仲达。曹画带有域外之风,所画佛像衣服紧窄,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样。他所创立的“曹家样”与吴道子创立的“吴家样”并称,史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评语。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声名最著。他在长安、洛阳两地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且笔迹挥宏磊落,势状雄峻、飘逸,遂有“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之美誉。到了晚唐,出现了专攻佛道人物画的画家,左全便是声名最著的一个。而唐代王维开创了一种别具风格的禅意画,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绘画影响最著者当推壁画,即出现了佛教石窟壁画艺术。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佛教盛行,各朝统治者的扶持与信奉,动用了大批的民工、石匠,开掘了许多石窟,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云岗石窟和河南的龙门石窟等。这些石窟中,有大量的佛教本生故事、菩萨、罗汉、天王、飞天等壁画。在绘画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熔中国传统与外来艺术于一炉的画风——既有粗犷遒劲的西域画风,又有线条飞舞的汉族传统画法;既用苍劲线条表现地狱的阴森可怖,又有用柔和的粉线、朱线表现极乐世界的美丽图景;既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磅礴气势,又有天衣飞扬、树影婆娑的细巧意境,带有明显的汉画风格与域外画风相混合、相融合的特点。而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从凄厉恐怖的佛本生故事画一变而为规模宏大、色彩绚烂的经变画,用浓墨重彩描绘了佛国净土的种种美妙乐趣:佛坐莲台、众圣环绕、天女散花、彩云缭绕、金阁琼楼、玉宇仙山、乐伎列坐、舞女当筵、瑶草奇葩、珠翠绮罗……此时的佛像无不身躯伟岸,面呈喜色,显露出温柔敦厚、关心世情的神态,而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清赢示疾”、苦不堪言的苦行僧形象大不相同。这一倾向由唐而始至宋更明显。这显然是与当时佛教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壁画也无疑是为了迎合当时士大夫与一般佛教信徒对“极乐世界”的憧憬而做的。
壁画是中国古代绘画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不懂得壁画就很难了解中国古代的绘画;而中国古代的壁画自魏晋后,几成佛家之天下,或见诸佛寺,或取材佛教,或出自释门之手。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撇开佛教壁画,中国古代的绘画乃至中国古代美术将顿然失色。
外来佛教文化对汉语言文字的影响
我们以曾被古人喻为“华夏文化之冠冕”的诗、书、画与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可以看到,所谓“不懂禅,不足以言诗;不懂禅,不足以论书画”,并非夸张之辞。如果完全撇开对外来佛教的研究,忽视我国历来对它的改造与吸收,就无法对多种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就连汉语的发展也与佛教的传入、发展关系密切。
我国知识界吸取梵文,由重视汉字的形象意义转向汉语的发音,并从此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定出了“四声”,编定出依照声音分类排列的新字典。而至隋朝,在分析汉语每个字的元音、辅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字所有的读音系统并整理成书《切韵》(后至宋朝有《广韵》)。而恰恰是唐朝的和尚守温,仿照印度梵文字母表制出一套汉语辅音字母表,使汉语语音分析更精密,汉语语音学又有了新发展。就是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亦源于佛教者甚多,仅丁福保的《佛学大词典》中搜集的源自佛经的外来语和专用词语就达三千余条。如“宗教”、“世界”、“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一针见血”、“一尘不染”、“三生有幸”、“百尺竿头”、“天花乱坠”、“心心相印”、“不可思议”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可见,如果我们要完全撇开佛文化的话,恐怕连话也说不全了。”
汉唐盛世是中国文化兴隆昌盛的黄金时期,而这一盛况出现的重要原因,乃是由于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使中国文化系统处于“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在此氛围中,中国文化系统根据本民族特色,对外来文化选择取舍、加工改制,收到了“以石攻玉”之效。“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根据,决不轻易地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统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唾弃。”然而尽管中国文化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如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等,但中国文化却没有成为“四不像”,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文化,这也正体出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之稳定性。而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或融入中国文化成为其一部分,即使像佛教文化这样确实在我国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外域文化的传入,也并不能使我国“全盘佛化”,而是佛教的“华化”,这又恰恰是中国文化强大同化力的表现!而今天,当我们面对世界文化日益繁荣,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汇合点上,而对种种外来思潮无所适从或盲目追随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不能全盘西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疾呼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以古为师,以史为鉴,从传统文化中去汲取经验,寻找出路。五千年来从未中断的、被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之一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的中国文化,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永远会给我们以启迪!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