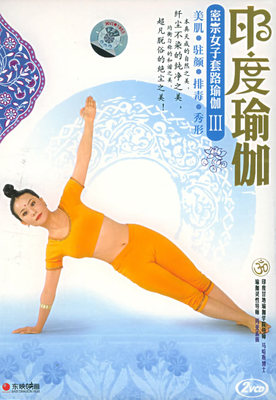2007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很好,我戴了一顶粉红色的毛线帽子,坐在文教大厦8楼的一个办公室,面前是一排正襟危坐的面试官,他们的脸上写着四个大字,齐鲁周刊。
一排正襟危坐中,是抽着烟的女总编,她弹了弹烟灰,镜片后的眼神如同一道x光直射向我:“平时读什么书?”这几乎榨出了我袍子里所有的小,我诺诺道:“女友,读者……”她显然有点不满,皱了皱眉头,“有作品吗?”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士、执行主编由老师一迭连声地说“有有有”,拿着我剪贴下来的几张豆腐块呈了上去。
看着我满纸的风花雪月,女总编的眉头皱的更深了,深的我忍不住想上前拿熨斗熨两下。
接下来的审讯已经不记得具体内容,只记得女总编一连串咄咄逼人的反问极大激起了我的斗志,遇到挑衅了?那就微笑。反正媒体这个神秘的行业本来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做做也就罢了――梦想不成真不才是生活的常态么?
没想到,我竟然被留下了。
吸烟的女总编,我的张总后来说,当时留下我的主要原因是“漂亮、不卑不亢”――嗯,听起来很美。当然,背后的潜台词我还是明白的,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熏陶的我,距离一个称职的媒体从业者,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之所以连篇累牍地描绘这个场景,是因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女总编把我变成了一个叛徒。
这之前,我有近5年的时间在一所地方大学当德育老师,那个世界里,好诗永远比假话少,好酒永远比白开水少,心里有灵,贴地飞行的时候永远比坐着开会的时候少。当我在一群为了评职称大打出手的老头子们中看到我一眼看得到底的一辈子时,对于一个满腔情怀的女少年来说,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绝望。
在周刊,我提报的第一个选题叫《中国解禁电影的前世今生》,一个宿命般的标题。我体内的一种岩浆似乎也被周刊解了禁。比如熬夜和酒――从文教大厦到贡院墙根街,当我们把“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选题进行思辨、思考和梳理后,定稿、设计版面、签付印……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往往已是凌晨,我们总能在街头找到一个没打烊的烧烤摊,蘸着贾平凹与萨拉沃特斯、博尔赫斯与杜拉斯的双拼火锅,呼儿将出换美酒,但愿长醉不复醒。
在周刊,我执笔的第一个封面故事叫《放下色情,立地成佛》,这一年,我刚刚拿到驾照,便带着同事吴永强、杨百会驾车上了高速,打开车窗,风呼啸着鱼贯而入,恐高的我一阵眩晕,百会还在身边叫嚣“超车,快超车”。至今也没想明白,这个来自大冠县、当过民工扛过水泥的乡野少年是如何在“二”的道路上奇迹般存活至今的?
整整四天,我们奔波在聊城、临清、阳谷的大街小巷寻找大运河和金瓶梅的历史,晚上则在有雨没肉的地摊上,没头没尾分一瓶酒。每一段扬起烟尘的行程,永强和百会都拿着地图瞪大眼睛,丝毫不敢在我这个菜鸟的车里打瞌睡。
最后一天晚上,我喝醉了,嚎啕大哭。因为太多的疲惫和压力,也因为我们在这段旅程中找到了彼此共有的痛苦。我们都是不成器的东西。心里一撮小火,身体离地半尺,不做蝼蚁不做神,却做了新闻记者。
人生而具有两个世界,有的人是外界环境的顺民,在这个鲜花盛开的时代,谋生而不谋爱方为正道沧桑,他们永远政治正确,永远不为自己之外的任何事物热泪盈眶。他们如此强大,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在文化和世相下纠结、矛盾、困惑、痛苦、与自己不和解。
当我们兴高采烈于某个牛逼的选题,激情澎湃于某种文化与偏见的激辩,我们也会在房子、车子、孩子、票子的现实困境前蹉跎大恨――但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我们无法不在每个周三的夜晚摊开纸笔,静观另一种暗香;无法不选题凶猛、激烈辩论到杀气四伏。
我们到底是庸常生活的弱者,还是与生活死磕到底的强者?
或许,人很多时候比拼的不是强,是弱,是弱弱的真,是短暂的真,是嚣张的真。所以,大酒之后,我们看到月亮而不是看到灯泡,看到花朵而不是看到女人,想起你而不是想起其他比你完美太多的人。
我们都曾经是大多数,我们也曾经是这样一小撮。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