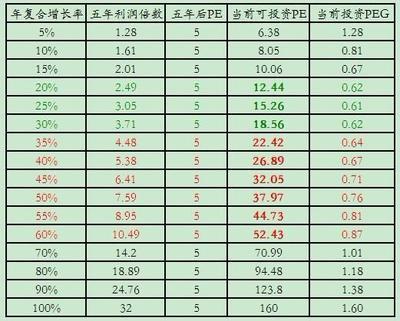文│卜正民(Timothy Brook)
节选自《哈佛中国史》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感谢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图片来自网络
元代可汗
塔尼斯特里令元代皇位继承之争趋于白热化。1260年,忽必烈汗赢得了“蒙古大汗”的称号;1271年,他宣布建立一个中原王朝规格的国家—元,并按“汉法”用“至元”年号;至元三十一年(1294),他逝世后也被赋予了一个中原帝王的庙号—世祖。他的长寿意味着皇位的继承跳过了一个世代。
承袭皇位的是他的孙子铁穆耳(1265—1307)。铁穆耳并非长孙,却在忽邻勒台选举中打败了自己的兄长甘麻剌(Kammala,1263—1302)和答剌麻八剌(Darmabala,1264—1292)。铁穆耳死后,皇位旁落至答剌麻八剌一系,由其子海山(Khaishan,1281—1311)即位。海山死后,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wada,1285—1320)嗣位,其后又传位其子硕德八剌(Shidebala,303—1323)。至治三年(1323),硕德八剌被刺,帝系上推一代,回到铁穆耳的长兄、硕德八剌的叔祖甘麻剌一系。于是,甘麻剌之子也孙铁木儿(YesünTemür,1293—1328)当了五年的皇帝。
致和元年(1328)秋,也孙铁木儿年幼的儿子阿速吉八(Aragibag)被扶上王座,但他只当了两个月的皇帝,皇位就被答剌麻八剌的后裔抢了去。此后五年中,皇位争夺战在答剌麻八剌的两代后裔中展开。至顺四年(1333),妥帖睦尔(Toghn Temür)终于成了元朝最后一个,也是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从大德十一年(1307),即铁穆耳在位的最后一年,到至顺四年(1333)妥帖睦尔即位,短短27年间,共有10位汗坐过元朝的王座—要是算上图贴睦尔(Tugh Temür)的两次即位,就是11位了。
在皇位继承之争的旋涡下屹立着元政权的华厦,它是由忽必烈及其以汉人为主的近臣们根据中原王朝制度建立起来的。早在元朝建立以前,忽必烈的伯父窝阔台就已开始逐步摆脱由父亲成吉思汗开创的依靠贸易和纳贡获取岁入的国家经营模式。窝阔台看到直接统治和直接征税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忽必烈则更为坚决地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忽必烈逐鹿中原并非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政权成形初级阶段之后的自然发展。巨大的行政成本以及一班只有用赏赐才能换取其支持的永不餍足的蒙古贵族,也迫使其建立一个类似中原王朝的政权。他需要征服宋朝,才能使自己的政权存续下去。
忽必烈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将蒙古国都城从旧址哈拉和林(Karakorum)南迁。蒙古宪宗六年(1256),他派自己的幕僚僧子聪筹建新都,这座新都城后来在汉语中被称为“上都”,在英语中的罗马拼音是“Xanadu”。九年后,他将自己的对手各个击破,随即派给子聪第二件差事,在辽、金两朝南都旧址以南300公里处的北京,修建自己的新都城。自此,除明初50年外,北京成了明朝和清朝的首都。
▲元明清三代古都
忽必烈请来回族建筑师亦黑迭儿丁(Yeheitie' er)为他设计这座新都城,其规模之宏伟是前所未有的,并结合了蒙古的军事部署要素与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其结果是蒙汉杂糅的,与宋代建筑风格迥异,却在后世被逐渐认作典型的“中国式”。迁都之举使忽必烈坚定了既做汗又做皇帝的决心。每年夏天,他回到“夏都”上都,避暑、狩猎。狩猎不仅能获取食物,训练军队,也是一展忽必烈驰骋草原的骑射技术的良机。至元十七年(1280)刘贯道所作《元世祖出猎图》正好捕捉到了忽必烈狩猎时的场景。
▲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1280)。该画绘制时,忽必烈正值64岁,他本人的身形至少像画中一样魁梧。
迁都北京,意味着忽必烈创建的这个国家,必须像都城的建筑那样,将蒙古元素织入中国图案中。中书省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衙署就设在皇城南门外。中书令在政务上给予皇帝建议,起草法令文书,并监督依照传统设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吏部负责官员的铨选、考课和处分议叙。户部职掌田地清丈、户籍登记和赋税征收。礼部职掌朝廷各项繁重的典礼,监察(恢复后的)科举考试,并处理藩属及外国往来事务。兵部是一个文职而非军事部门,它负责军籍管理、俸给发放、军队训练,以及乘载、邮传之制。刑部主管刑罚政令、审核刑名。工部管理从城垣、渠堰到陵寝的各种官用设施的营缮和全国土木、水利工程的兴修。
此外,中央政府还包括职掌兵权的枢密院。忽必烈自信能够对首都发生的大小事情做到心知肚明,但是要保证各省官员不损及蒙古人的利益,就只能在各行省任命蒙古监临——达鲁花赤(darughachi)。
忽必烈唯恐蒙古人掌握的权力落入汉人手中,这也是他在官员铨选时偏好举荐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使臣子有知遇之感,而不像中原王朝惯行的科举制度那样毫无把握,只以优劣论人才。尽管如此,他仍然努力展现出谦和、仁爱的一面,以安抚被征服的臣民。据一份官方报告的孤证显示,他在中统四年到至元六年间(1263—1269),仅下令处死过91人。即便是根据当今的标准,这也称得上是轻刑宽禁之举。这是令人难忘的做法。明初士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盛赞忽必烈当政时是“轻刑薄赋,兵革罕用”。
在中原王朝制度中,人们本以为忽必烈会取消而他并未取消的一项是御史台(the Censorate)。御史的职责是监督官员和皇帝的言行。他们的目的是保证制度本身不被破坏或折损。有时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有时又令人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元朝皇帝拒绝给予御史台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御史台之设,仅仅是为了保证官员执行皇帝的要求。元朝的第五任皇帝硕德八剌是个例外。至治二年十二月(1323年2月),他为了启用更多的汉族官僚来制衡自己的蒙古劲敌,颁布了一系列新制度,敦促御史彻底查处官员贪渎案件。七个月后,他被刺身亡,而幕后主使正是对其拉拢汉人深恶痛绝的蒙古御史大夫。
中亚史家狄宇宙(Nicoladi Cosmo)认为:“忽必烈成功地吞并中原后建起的帝国华厦的地基是有裂缝的。他将种族区隔制度化的做法造成了民族关系上的不和谐。此外,中央政府被过于臃肿的机构设置而拖垮,其中大多数是为皇帝及其随从设立的服务机构。”(我们将会看到,马可·波罗等许多外来者都供职于元代朝廷。)
狄宇宙还注意到,“蒙古人对治理的态度仍然是反复无常、漫不经心的,中亚政治传统中的某些特征,如继承的原则、种族或宗族的特权,中央政府部门与商人组织间的合作关系等,仍然处处有迹可循。”要使大元王朝这座政治大厦长期屹立不倒,其一要依靠汉族官员的坚定支持—但蒙古人从来未能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们;其二是保证权力建立和交接的规则的稳定性—但这一点也从来未能做到。于是,元朝终究要覆亡,不过那是它屹立了整整一个世纪后的事了。
明代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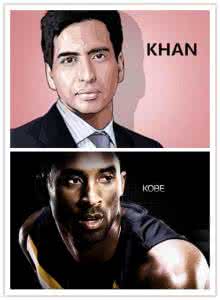
朱元璋是因为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才当上了洪武皇帝,不过,在1368年以前,他的主要精力被用来对付自己在长江中下游的竞争者上面。他称自己的王朝为“明”(光明之意),从宇宙论的角度说,这是一个“火向”的字,正好可以接续“水向”的“元”(乾元之意;物质与人世一样,被认为是周而复始的,即金、木、土、水、火五行)。这个字也表明,他吸收了明教意识形态中关于光明与黑暗两股势力的斗争的宇宙论观点。他在早期揭竿而起的时候与该教派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元璋声称,他的使命是将蒙古势力赶出中华,并恢复宋制。这个传言让他的儒家幕僚十分受用,也可能迎合了民间的民族沙文主义(ethnic chauvinism),然而,他的新政权却更多地复制了他本人熟悉的元朝惯例。结果便产生了一种杂糅了蒙古汗和宋朝皇帝两方面传统的新统治模式。
半个世纪以前,20世纪杰出的明史专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称这种新模式为“专制统治”(despotism)。牟复礼相信,宋代是中国专制统治的滥觞期,但他也指出,他所谓的蒙古的“野蛮化”(brutalization)将帝制中“大部分对皇权的限制都摧毁了”,因此,为明代的专制统治开辟了道路。“元朝野蛮化的世界的重要性在于,她是明朝第一代统治者和臣民成长的世界,正是以这种方式,她参与了明王朝的基调和特征的形塑。”
▲明史专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
牟复礼提出中国专制统治形成于宋元时期的假说,是为了挑战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由魏特夫(Karl Wittfogel)提出的冷战思维模式的汉学观点。魏特夫认为,从久远的过去直到现在,亚洲一直笼罩在一种亘古不变的专制统治之中。这是欧洲知识分子在17世纪发明的、用来描述西亚与南亚政权的概念。18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才被逐步用以描述中国,最终还给中国扣上了专制统治最高阶段的大帽子。这一命名是欧洲为了论证其帝国主义合法性而建构的帝国霸权意识形态的要素之一,结果却一直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和预期。
牟复礼之后一代的明史专家范德(Edward Farmer)将讨论明代政府的语汇由“专制统治”变为“独裁统治”(autocracy),即“帝制中权力的进一步集中”。这一定义把独裁作为各种制度设计中内含的一种政治组织系统提炼了出来。问题的核心不再是忽必烈汗的蒙古习惯,抑或朱元璋的暴戾性格,中国社会的权威本质(the authoritarian nature),而是他们为了维持自己权力所引入的制度。
这个词的好处是能让人立即抓住权力由朝堂上的程序和民众的期待对皇帝的限制转移到皇帝本人手中的变化。但是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皇帝是真正独自统治国家的(“独裁”一词起源于希腊文的“独自统治”)。正如牟复礼所见,即便是明朝最有决断的皇帝,其权力也受到了“现实的限制”。
有一种制度我们可能会把它当作是对独裁的限制,那就是法律。明朝创立者在国家成立之初就颁布了一部律法。其法条旨在约束官员和百姓的行为,对皇帝却不加限制。朱元璋并不认为他本人应受到自己所立律法的束缚。但是他失望地发现,《大明律》尚不足以达到锄奸惩恶,明刑弼教的目的,于是又亲手创制了“法上之法”。14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将这些“法上之法”编成一部《大诰》(Grand Pronouncements),成了第二律法。朱元璋命令官员们谨遵其精神,但他又谨慎地强调,唯他一人可以《大诰》拟罪,而法司拟罪则要比照《大诰》减一等。
朱元璋并非没有意识到,人民觉得新法有处置太过的地方,但他相信,用重典是开国之初惩处时弊的必要手段。朱元璋逝世前一年,有刑部官员请求将大明律的刑罚提高到《大诰》的水平,但朱元璋驳回了。这本是一个可以让可汗的拟罪特权超越约束皇权的法律制度的时刻,但他就这样放过了。即便如此,作为儒家善政核心原则的君臣、君民间的互惠关系,却是朱元璋所强调的规范与制度所缺乏的。他的治国理念刨去了儒家道德传统,留下的只是维持政府健全的惩罚手段。次年,朱元璋去世,这个堪称中国史上最特殊时代之一、几乎实现了专制乃至独裁的时期也随之告终。
尽管他留下遗训:“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但他的子孙并未持守他所致力推行的专制体制。尽管朱元璋所建立的法制应该是金科玉律,他们却不得不篡改他的垂法之意。毕竟,当实际偏离了应然的轨迹,比如,皇帝昏庸无道,在战争中被俘,或无承嗣时,任何政治体制都要进行改弦易辙。此类危机只有通过某种程度的篡改(fudging)和类推(analogical reasoning)才能度过。
然而,也正是因为规则的弹性,每一次危机都会变成继承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要以体制本身应对未来威胁能力的下降为代价。我们与其通过跟踪常规情况下的政治运作来理解明代统治,不如以明王朝的五次重大危机为背景进行考察。明代的第一次重大危机便发生在王朝创立仅12年的时候。
▲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像。这幅作于十六世纪的逼真白描肖像究竟是夸大了还是抓住了明太祖的不凡个性?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