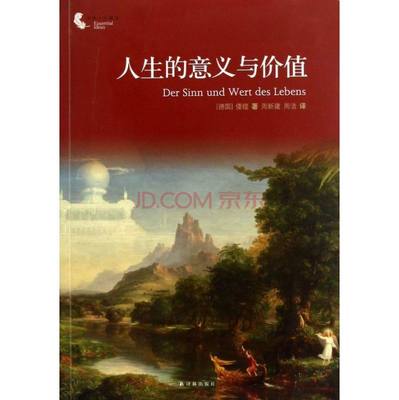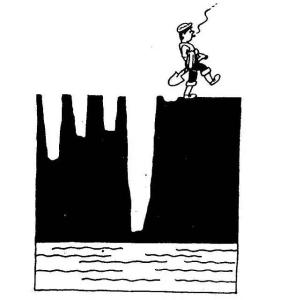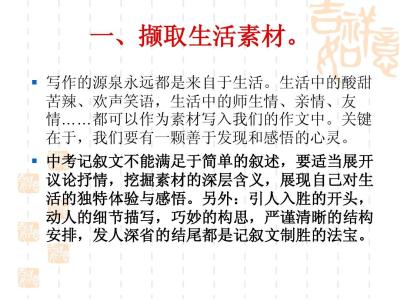高考的公平性涉及千家万户特别是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近年异地高考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日围绕异地高考的争辩随着各地政策的出台也越发激烈。表面上看,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所谓的“门槛”高低上,且所争论的对象则多集中在北上广等地。背后却是在前置条件划定的框范下,“京沪粤籍”和“非京沪粤籍”的利益博弈。
近年来,异地高考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员,对开放异地高考持有迥异的立场,尤其在流入人口多的北京、上海、广东地区,更是如此。这种立场差异,是由我国当前的高考制度决定的,在分省按计划的集中录取制度之下,追求高考公平,对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员来说,成了“零和游戏”:在本地户籍人口看来,开放异地高考,外来人员将侵占本地人的高考利益。
异地高考之所以成为问题,在于那些跟随父母进入“异地”生活,而又不能获得迁入地户籍的学生,至今不能以“非户籍”学生身份在迁入地参加高考和高校录取。虽然,各省市区异地高考政策已经出台,但对收入微薄、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家长来说,这无疑更像是一个“画饼”。更多的农民工家长难以符合条件,他们的子女,也只能成为为高考而迁徙的“候鸟”。异地高考至少直接产生两个负面后果:其一,许多学生随父母在其务工地生活多年,甚至生长于斯,却因为“非户籍”身份而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失去了与当地学生平等获得受教育权的机会,有违教育公平原则;其二,受这一政策制约,部分家长不得不选择将其子女留在家乡上学,导致大量留守儿童或留守少年的产生。而由于长年与父母分离而带来的情感缺失、教育缺失,极易导致留守子女的心理问题或行为失当,长期积累而不能解决,必然成为极大的社会隐患。
然而,异地高考有可能导致高考移民和‘恶意打工现象’,也就是父母为了孩子读书、考试,到教育不发达地区工作,挤占当地稀缺的教育资源,导致新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不少来自发达地区的学生,纷纷以迁户口、开假证明等方式,向落后地区“移民”,挤占了当地稀缺的高考升学资源。还应看到,就算异地高考政策在各地都不折不扣的执行,所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都可以在当地参加中高考,对户籍所在地的孩子也是不公的。其实,很少有人提及这个敏感的话题,如果你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很少是独生子女,他们大多是多胎子女,如果都放开(不设置任何门槛),显然对这些城市的独生子女也欠公平。
我国的高考录取制度,是将高校招生计划分配到各省的,如此一来,招生计划就成为本省户籍人口的蛋糕,与这一制度对应,各地此前都实行按户籍报名的基本规定。很显然,这一制度安排是我国高考录取地区不均衡,以及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的根源所在。比如,北京户口学生上北大的比例是190∶1,而安徽的比率是7826∶1。2012年各省(区、市)北大、清华两校录取总人数可见,北京仍然是两校生源主要来源地之一,共录取661人,比河南、山东两个高考大省的两校录取总和还要多。但异地高考的口子一开,恐怕很多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把孩子送到北京、上海等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地区来学习,包括有钱的、有权的,结果可能导致真正在北京、上海工作和生活的人的孩子没学上了。
开放异地高考,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然而,我国选择推进异地高考的思路,却是在现行高考制度框架范围内,由各省市适当放开高考报名的条件限制。基于此,异地高考这条路很难走通,或者根本没有实际操作性。“京沪粤籍家长”和“非京沪粤籍家长”无休止的争论根本毫无意义。
应该说目前的高考制度,不是最先进的选拔人才制度。然而,高考制度成为当今唯一相对公平、公正的制度,如果轻易废出,后果不堪设想。可现行高考制度的设计存在诸多弊端,严重侵蚀了公平的底线。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失衡才是不公平的关键;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极大地留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让大多数寒门子女与重点高校无缘;允许异地高考不过是纸上谈兵;靠道德约束来堵塞高考漏洞更是痴人说梦。

就高考制度本身而论,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前提下,实行各省、市、区自行命题,设置区域录取线、加分等多道附加规则,让高考录取的分数线不平等的情况凸显。在目前诚信严重缺失、阶层固化、“拼爹”现象愈演愈烈等社会大背景下;在没有行之有效的高考改革方案以前,恢复全国高考统一命题,全国重点高校不再把招生计划配置到各省,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异地高考这一问题就不存在了。
作者:闹市一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