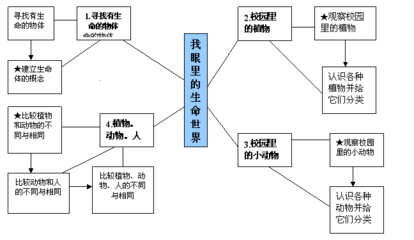我们先看以民间立场为精神谱系的小说创作在欲望叙事方向上的转型。“新时期”伊始,思想解放潮流的涌动催发了欲望的苏醒,长期禁锢于宏大理性框架的情感欲望在对个体化、世俗化、民间化的自由的渴望与幻想中,经由此期小说丰富的创造性叙事得到了血肉丰盈的展现与描摹,并渐渐取得合法性地位。然而,随着商业世俗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渗透于欲望叙事内里的自由伦理观悄然发生着新变,曾经长期被社会压抑的个体由与社会对峙、构成张力的现代个体,走向或者完全漠视社会环境、陷入自恋或者完全顺应社会、融于消费主义思潮的“准个体”,而其所依托的民间精神则退化为完全对立于人性启蒙的“沃土”,很多作家将民间乡土文化等同于没有头脑的“动物凶猛”、混沌状态的欲望泛滥,失却了现代启蒙既将欲望作为生命力的源泉同时又对“精神奴役的创伤”进行批判的张力,成为一种平面化的欲望叙事。
这一点在余华、莫言等人的作品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很多读者对余华近期出版的《兄弟》感到不满甚至不解,这样一部艺术性不强的作品怎么会出于一位大家之手?它的叙事摆出一副地道的民间面孔,很像一篇标准的民间巨著,叙事者本身就是“我们刘镇”——已经民间到彻底的地步。那么这位“叙事者”具有怎样的叙事品格与叙事立场呢?相信读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它对李光头这样一位集愚昧、霸权、荒淫、荒诞于一体的代表人物情欲言行的玩味与展览。还未成年的他便因为偷窥女人屁股尤其是林红的屁股而备受“刘镇人”的青睐,叙事者“刘镇”更是将这一点以及与其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的“磨电线杆”夸大渲染到整个上部最重要的事件,成为塑造人物性格最出彩的环节之一。可见在作家心目中,这种事件就是民间最基本最常见的场景之一,李光头就是最具民间意识的幸运儿。此后,李光头虽然没有马上得到林红的爱,可是凭借着一股闯劲加上无赖和好运发了大财,有机会以各种花样玩弄各种女人,并最终从肉体上得到林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道德感、狡猾、无赖、霸道的人物,叙事者偏要将兄弟深情寄托在他身上,将对女人(林红)执著的爱寄托在他身上,将对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消费物质社会的批判与揭示寄托在他身上,将其打扮成一个披着民间旗帜的怪模怪样的民间英雄。
这种将民间意识等同于本能宣泄、无知愚昧,将滥情纵欲黄袍加身,搞个反思政治、反思现代物质消费社会的名目的欲望叙事在当前长篇小说中可谓不胜枚举。除余华外,莫言的作品也很有典型性。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莫言创作所笑纳的赞谀,除感觉的丰饶、细致、奇异,语言的恣肆澎湃与陌生化,以及儿童视角的有效使用等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常有论者所谓的突破政治、启蒙等等层面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经验呈现与“民间伦理原则”;其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则被视为民间伦理原则的代表作。也许以《红高粱》红透文坛的作者坚信,只要在创作时祭出骠悍不羁、性欲旺盛的男人女人这一叙事法宝,就能抵达甚至超越《红高粱》的思想艺术境界,就能够以“鲜活”的民间精神领军文坛。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就以其被推举为民间叙事集大成之作的《丰乳肥臀》为例。沙月亮、司马库与鸟儿韩等是小说着意塑造的刚性男人,尤其后两位被母亲上官鲁氏视为真正的男子汉。司马库对女人的魅力自不待言,上官家的二女儿招弟勇敢地对抗母亲嫁给他做姨太太;大女儿上官来弟也是靠着其“金刚钻”的威力从失心疯中清醒过来。即使在逃亡的危急关头,还有女人自称母狗,心甘情愿与之在田间地头颠鸾倒凤。鸟儿韩更被塑造为血性十足的民间传奇人物,出场时他就显现出敢于出头、敢于争命的硬汉子作风,此后更被描绘为一个民间传奇英雄。更重要的是,在血性十足的传奇英雄之外,鸟儿韩还被塑造为一个弥足珍贵的情种,与上官家如花似玉、风情万种的女儿们中最为风流的一个,即大姐上官来弟一起承担着营造民间爱情神话的叙事重任。其实他们最初的肉体接触并无新意,延续的仍旧是作者一以贯之的男女之间无需理由、烈火干柴般的叙事套路,缺少必要的铺垫就翻滚在一起。两人的关系如果发展到这一地步也就罢了;这不过是上官来弟风流淫荡的又一例证。可是我们发现,由浑圆的屁股、挤扁了的乳房,一声一声的狂叫接上头之后,两人的关系可谓突飞猛进,很快被拔高为崇高、甜美、庄严的性爱关系的代言人,相关叙事格调也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动物凶猛式的肉欲通奸被装扮成了心灵交融的高尚行为,甚至被“升华”到“为天地献礼”的高度:“月光实在是太美好了,清清冽冽,洋洋洒洒,……鸟儿韩与来弟的这一次欢爱是对高密东北乡广天阔地的献礼,是人类交欢的示范表演,水平之高高过钻天的鸟儿,花样之多多过地上的花朵。”这就是作家心目中的民间世纪“性爱礼赞”,民间自由精神的狂欢。
如同文学叙事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一样,它也不是民间的传声筒,它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演变规律。高潮也好,狂欢也罢,必须从叙事的缝隙中渗透出来。可是我们从小说的整体叙事中无法获得叙事者所大力渲染的这种“天地献礼”与“人类示范”的欢畅与庄严,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严重的牵强附会与人性的断裂鸿沟。相信读者们对所谓“人类示范”的女主人公上官来弟前此的表演还记忆犹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两次。一次是她倚疯卖疯地上演了一出牲畜闹春式的活剧;另一次则是上官来弟与二妹夫司马库的通奸描写。两人没有任何铺垫便直奔主题,“不知羞耻的肆意狂欢,毫无顾忌……浪死了呀,熬死了呀”。就是这样一个欲火攻心、肉欲横流、粗俗放荡、勾引妹夫、通奸杀夫的失心疯患者与欲望至上主义者,转眼之间却摇身一变,成了所谓“天地献礼”与“人类示范”的代言人。
莫言是“作为老百姓写作”(比“为老百姓写作”提高了一个档次)的首倡者,他多次声称《丰乳肥臀》“是写一个母亲并希望她能代表天下的母亲,是歌颂一个母亲并企望能借此歌颂天下的母亲”,“我憋足了劲要在这部书里为母亲歌唱,更狂妄地想为天下的母亲歌唱”。这个“母亲”便是上官鲁氏——一个集乱伦、通奸、杀害婆婆、偏心儿子、教养失败于一体的女人,通过她能达成歌颂天下母亲的愿望吗?这样的母亲能代表“民间精神”吗?再如《檀香刑》中代表胶东民间精神的“猫腔”,小说更是将其描写得怪诞滑稽而愚蠢,民间精神难道就是这样的吗?从号称最有民间精神的作家那里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母亲崇拜,而是乳房崇拜,不是民间精神,而是刽子手伦理。从根本上说,作者极力渲染的上官来弟与鸟儿韩之间的民间“世纪情爱”不过是一个幻相,就像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任凭其怎么大声宣扬,也难以打动人心。以此观之,如果没有真正的民间意识、民间精神,仅仅凭借几个所谓民间传奇人物或浑然冲动的野性女子,并不能创造浩浩荡荡的民间世界。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当下作家往往持有一种偏见,那就是自认为当对性和欲望说“是”的时候,就是对政治说“不”。的确,当政治本身不能够保证将人们的力量全部用于政治目的上的时候,它反而会默许性的自由的存在,因为那样至少可以保证民间没有剩余的精力来充当政治的反面力量,因为他们在性的或者说私人领域内的放纵所造成的虚假的自由幻相之中得到充分的“满足”了,同时也已经无力自拔了。因此,这种文学上消极自由式的性解放恰恰是不仅不能构成对政治的张力以及对社会的批判性,恰恰不是弘扬了文学的启蒙精神。在一种“民间=本能”的公式换算中,不但人的本质被异化,而且人的成长历史也被叙事成抽掉了理性的欲望的历史、愚昧的历史、暴力的历史、碎片化的历史。可以说,在今天我们的“底层文学”是有了,但底层文学意识则缺乏,“民间”文学有了,真正的“民间”文学意识则少有,更多的是种种“伪底层意识”、“伪民间精神”。
如果说上述长篇之反启蒙的恶劣效果与其“伪民间”精神或生活状态息息相关,那么另一类情况则直接导引于“伪民间立场”;如果说上述长篇是对民间丰富的生活情态的低俗化、本能化的曲解,那么另一种情况则是对民间世俗生活真相的刻意过滤与无限拔高,是知识分子因自身思想无力而通过对民间的虚假想象营造出乌托邦,将之作为思想与叙事的资源。张炜是一个非常有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同时也恰恰是一个愤世嫉俗唯独钟情于、融入野地的民间立场的代言人。如果说在《古船》中,作者以其坚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民间进行了冷峻的剖析,《九月寓言》至少比较清醒地告诉人们,高尚或者卑微,它们都来自民间那最为原始的生命冲动,那么到了《能不忆蜀葵》,作者再也没有了对于民间生活与生命的洞见,只有对乡土生活的完美想象和对这种想象的无比怀恋,蜀葵所象征的生命流动,那“夏天的光,夏天的热量,中国乡间的烂漫和美丽”,不像是中国的民间,倒像是一个善于狂想的画家心目中的天堂。
阎连科《受活》也是颇富代表性例子,它彻底告别了政治乌托邦及其宏大叙事,之所以说它“彻底”,是因为它告别政治乌托邦的方式是高高地构架起了一个新的乡土乌托邦——那个受活社,那个受活庄,既是残疾人的天堂,也是现代性社会的“世外桃源”。残疾人与圆全人,受活社会与现代主流社会进程构成了一对格格不入鲜明对立的矛盾。作家在处理这对矛盾时非常有力地批判了充满欺诈与诡计的现代文明,尤其是充满政治乌托邦色彩的革命进程对乡土文化、民间精神的扼杀和毁灭,但这远非小说叙事的主旨,作家深情无比地赞颂着的、痛楚无比地缅想的,是以茅枝婆为代表的受活人和受活世界,这些瞎子、聋子、瘸子、哑巴以其谦卑、内敛、诚朴组构了一个祥和宁静而温馨的福地。然而他们柔弱、短视、愚陋,之所以被圆全人欺骗,也是源于他们的简单,以及在实利面前难以把持,甚至是缺乏操守和自尊,对于这些,作者则几乎视而不见,而是毫无原则地凸显两种世界的对立。如果说作家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写作,那么这里缺乏一种冷静的反思和批判态度;如果他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话,则又毫无抉心自食的忏悔精神,这种反政治乌托邦的民间乌托邦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拒绝个性解放、漠视灵魂强大的反启蒙倾向。有学者评论说,就乡土中国的文学书写而言,有了阎连科,我们才可以说,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沈从文式的“乡土恋歌”,以及《古船》或《白鹿原》式的“文化秘史”,的确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这样的评价从阎连科与前人创作之启蒙精神的不同来说是对的,但显然过于乐观,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里的乡土及其民间精神已经不是活生生的,反倒像概念化的。
当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的民间成为一个诗意的乌托邦,当藏污纳垢同时满孕着生命强力的民间成为真善美的最终象征,一句话,当民间成为神话,成为拯救现代性迷途的唯一的灵丹妙药,一方面民间已经不复是真正的民间,民间精神也不复是真正的民间精神,而是伪民间和伪民间精神;另一方面,伪民间精神进一步解构了长篇小说的自由叙事伦理,走向反自由、反启蒙的深渊。如果说欲望写作以其过度的“媚俗”令人生厌的话,那么这类民间乌托邦叙事不妨称为“媚雅”,同样不啻是对文学精神的一种伤害。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