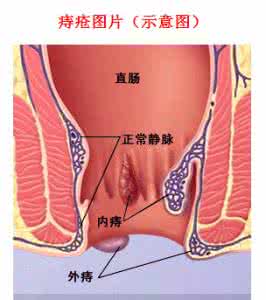文_珍妮·斯科特 编译_凌奥幸
在传记《我父亲的梦想》中,奥巴马将自己的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描述成一个害羞的小镇姑娘,同时又是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但在街头小报和网络上,人们则把她视为一个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曾经抛弃过自己儿子的嬉皮士,甚至还有人认为她在自己儿子的出生地上动了手脚—将奥巴马的出生地写成“夏威夷”。
但是经过两年半的研究以及200多次访谈,我发现在外界为邓纳姆打上诸多标签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故事。
这个有着男孩名字的女孩,在种族通婚仍然不受政府完全肯定的当年,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名非洲人,并在24岁的时候带着儿子搬到局势不稳的印尼雅加达。如同后来奥巴马开玩笑所说,邓纳姆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一个集爱因斯坦、甘地以及哈利·贝拉方提(著名艺术家)于一身的伟人。
相比母亲,奥巴马好像更愿意谈及曾养育过自己的祖父母。但是,正如他承认的那样,是母亲塑造了后来的自己。2004年,在《我父亲的梦想》再版序言中,奥巴马谈及9年前逝世的母亲时说:“如果当年知道母亲将因病去世,我就不会对父亲这个在自己成长中缺失的角色大书特书,而是要好好写一写一直陪在身边的母亲。”
邓纳姆十分爱自己的孩子,奥巴马来自美国的信件常常会让她高兴一整天。对于奥巴马的“父亲情结”,邓纳姆偶尔会对身边的朋友抱怨一下,但是从未向外人过度夸张这个问题。正如她曾对奥巴马说过的冷笑话一样:“我给了你有趣的人生,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带着混血儿子迁往海外
1960年秋,只有17岁的邓纳姆怀上了肯尼亚人、夏威夷大学学生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的孩子,两人随后结婚,邓纳姆退学并生下小奥巴马。但是孩子的出生并未挽救这个短暂的婚姻。离婚后,邓纳姆遇上来自印尼爪哇岛的学生罗洛·苏托罗,并于1964年再婚。1965年9月30日,六名印尼军官在雅加达被人绑架后遇害,包括苏托罗在内的印尼海外留学生,由于受到政府资助很快被召回国。1967年,邓纳姆完成自己的人类学学业,带着6岁的儿子搬到印尼,和丈夫团圆。
此后的四年,正是母子二人关系最亲近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奥巴马常被唤作“巴里”,邓纳姆将自己的价值观教给年幼的奥巴马,为儿子树立榜样,并有意无意地帮助他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美国人伊丽莎白·布莱恩特曾经住在印尼日惹市,她还记得在一次午餐聚会中,邓纳姆穿着由印尼传统布料制成的长裙,教导自己的儿子和每个人握手。客套完毕,奥巴马坐在沙发上,拿起邓纳姆带来的一本英文书安静地看起来。
整个午餐时间里,当时只有9岁的奥巴马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专注听着大人们谈话。他问母亲自己能否离开餐桌,邓纳姆则让他问主人是否答应。得到许可之后,奥巴马离开餐桌坐在地上,和布莱恩特13个月大的儿子玩了起来。午餐结束后,众人走在街上,奥巴马则跑在前面。这时,一群印尼孩子开始用石头砸他,还朝他骂难听的绰号。奥巴马表现得很平静,一一躲了过去。正当布莱恩特想要上前阻止的时候,一直没有反应的邓纳姆拉住她说:“没关系,他已经习惯了。”
“当初她带着一个混血孩子来到印尼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边的人对黑人不太友好。”布莱恩特说,她很敬佩邓纳姆能够教育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得勇敢无畏。邓纳姆还会教育奥巴马去尊敬别人,像其他印尼孩子一样,奥巴马对自己的父母也表现得十分有礼貌。印尼的生活习惯,奥巴马好像全都吸收了进去。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看起来十分Halus(在印尼语中常指礼貌、文雅和谦恭)的原因。”布莱恩特谈到奥巴马时说,“他既有亚洲人的礼貌谦逊,也有美国人的耐心平静,是个好听众。”
当邓纳姆来到印尼时,这个国家还处在动乱之中。邓纳姆和儿子当年住的那个村庄,屋群低矮,周围遍布着树林、稻田和沼泽;漫长的雨季从11月一直延续到来年3月,由于河道积蓄能力不强,过多的雨水常常导致洪灾,汹涌的洪水浸透了那些硬纸板做的棚屋;能够正常使用的电话为数不多,有人开玩笑说,街上飞跑的汽车有一半都是用来传递办公室职员间信息的;当时的印尼很少看见西方人,更别提黑人了。
即便如此,这个城市还是有着自己的魅力。当年曾在雅加达生活的人,都会回忆起从街头小贩手推车里发出的穆斯林呼唤祷告的声音;人们坐在老式酒店的阳台上喝茶,头顶的风扇不知疲倦地为人们驱走午后的酷暑。多年之后,当地很多人再次回想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都会将它看成是一段蜜月期:政府放松了对媒体的管制,青年文化开始蓬勃兴起,文化生活开始繁荣起来。正如后来人评价的那样,这是印尼的布拉格之春。邓纳姆和奥巴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不受世俗制约的母亲
1968年,邓纳姆开始在由美国新闻处资助的一家民族机构工作,她主要负责印尼政府官员的英语学习,并帮助商界人士到美国学习。有时,邓纳姆会带着奥巴马一起工作,而同事们时常还会开奥巴马的玩笑,说他的皮肤颜色真是与众不同。两年后,27岁的邓纳姆换了新工作,受雇于一家非营利性管理培训学校。很快,邓纳姆成了知名老师,她的班级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1970年8月15日,奥巴马刚刚过完9岁生日,邓纳姆的母亲玛德琳便来印尼探望女儿,此时也正逢邓纳姆生下自己第二个孩子—奥巴马的妹妹玛雅·卡桑德拉·苏托罗。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邓纳姆不想女儿和自己一样,有个别扭的男孩名字。
在印尼,邓纳姆衣着简单,从不化妆,长头发由头巾缠到脑后。对于爪哇人来说,作为女人的邓纳姆有点太过健壮了。但她坚持己见,很少为了取悦他人而作出改变。
据好友凯·伊卡娜格拉所说,邓纳姆常常建议她变得更大胆一些。“她会提醒身边的每个人做错了什么,即使是家庭成员也不例外。她十分看不惯印尼社会里对妻子的要求,甚至告诉玛雅以后不要成为那样懦弱无能的人。”
20世纪70年代早期,因为工作的原因,邓纳姆的丈夫苏托罗需要和石油公司的高官及他们的妻子进行交际。在印尼,女人们应该穿上传统服装,陪着自己的丈夫参加这样的活动,还要和其他高官的妻子们大谈育儿经。但对于邓纳姆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是无法接受的,她请求苏托罗别让她参加这种活动。在给朋友考利尔的信中,邓纳姆抱怨那些中年白种美国人谈论的都是些空虚的事情,而自己的丈夫苏托罗也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人。
两人时常为是否参加聚会的事情在卧室里争吵,年幼的奥巴马有时也能听得到。在《我父亲的梦想》一书中,奥巴马写道:“德克萨斯或者路易斯安那来的美国商人,会拍拍苏托罗的背,吹嘘自己怎样贿赂政府拿到新的海上钻井权,而他们的妻子则会跟我的母亲抱怨印尼仆人的水平。苏托罗经常说,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这种活动该有多么不像话,并提醒她这些都是自己人。而我的母亲则会大声叫喊:他们不是我的朋友。”
在奥巴马的描述中,两人关系的恶化可以追溯到苏托罗被召回雅加达的时候,那时两人分开了足足一年。在夏威夷时,苏托罗是个很有趣的人,常常给邓纳姆讲述自己童年时的故事,并深信回国后自己会去大学任教。但后来,两人几乎不怎么交流。有时,苏托罗睡觉时一定要藏一把手枪在枕头下,而邓纳姆有时还会看见他半夜在屋里踱来踱去,拿着杯进口威士忌,思考着自己的小秘密。
逐渐地,邓纳姆开始慢慢了解了真相,苏托罗的一位侄子向邓纳姆讲述了苏托罗从夏威夷回国后所经历的一切:刚抵达雅加达,苏托罗便被带去审讯,并被告知自己已被征召入伍,即将去新几内亚的丛林里服役一年。邓纳姆听完这一切之后,作出的结论是:权力将苏托罗拉回现实中。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逃脱这样的现实,但这种情况的出现让他渐觉权力的巨大力量。正因为此,苏托罗学会了与权力和平相处,进入国家石油公司做高官、拿高薪。

苏托罗让邓纳姆失望,邓纳姆对于社交的反抗也让苏托罗生气。她的朋友任思科·哈林格说:“印尼男人喜欢女人轻松开放,但一旦有父母、家人在场,女人就得扮演一个小妇人的角色。我所认识的邓纳姆是个强势的女人,不关心衣着和首饰,这与大多数印尼女人完全不同。她拒绝做小妇人,我完全理解苏托罗会对这些难以接受。”
萨满曾是邓纳姆和苏托罗家的男仆,在他的记忆中,苏托罗非常严格,邓纳姆十分善良。有时,两人会因为邓纳姆下课后的晚归而吵架。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邓纳姆拿一条毛巾捂着脸,鼻子里还不停流血。很难说年届40的萨满的回忆有多可信,毕竟没有人听说邓纳姆和苏托罗之间出现过家庭暴力。
“无条件的爱”
对于自己的孩子,邓纳姆不从吝惜表达爱意的方式。玛雅说,邓纳姆很喜欢搂搂抱抱,并常说“我爱你”,一天说一百遍也不厌烦。只要是牵涉到自己的孩子,邓纳姆很容易感情用事,跟朋友谈及孩子时,还会掉眼泪。邓纳姆不是个喜欢唠唠叨叨的母亲,她更愿意用幽默来表达情感。但是对于她认为重要的事情,邓纳姆会表现得十分严格。
同事回忆称,邓纳姆曾说过要向儿子灌输公共服务的思想,她希望奥巴马有义务感,心中要有回报社会的想法。“她会谈起怎样训导奥巴马,犯了错误还会打他屁股。”邓纳姆的前同事唐·约翰斯顿说。而萨满也回忆称,如果奥巴马完不成祖父母从夏威夷寄来的作业,邓纳姆会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用苏托罗的军用皮带抽他屁股。但是奥巴马总统曾通过一位发言人表态说,自己的母亲从来没有体罚过他。
在雅加达的公寓,奥巴马和萨满睡在一个屋子里。一天夜里,八九岁大的奥巴马让萨满关上灯,没有得到回应后,奥巴马随即打了一下后者的胸部,见对方没有反应又重重打了一下,这次萨满回击了。奥巴马开始大哭,希望以此引起母亲的注意。根据萨满的回忆,邓纳姆当时没有作任何回应,她好像意识到这次是奥巴马不对。
“母亲不允许我们行为粗鲁,言语刻薄,或者骄傲自大。我们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如果我们说了什么人的坏话,她就会试着从对方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她不允许我们形成自私的习性。这样的教育是长期、一直持续的。”奥巴马的妹妹玛雅说。
在很多人看来,邓纳姆一直相信奥巴马是个天赋异禀的孩子,她常常夸耀儿子的智商、进步和勇气。邓纳姆一位住在夏威夷的朋友说:“有时谈起巴拉克时,她总会说:我儿子很聪明,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甚至是美国的总统。”
根据萨满的回忆,苏托罗有天晚上曾问奥巴马:“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年幼的奥巴马张口便说:“当印尼总理。”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印尼的学校条件普遍不好。奥巴马进过两所学校,分别由天主教和穆斯林创办。在学校里,虽然爪哇人极端强调克己,但戏弄、取笑他人也很盛行,皮肤颜色是攻击他人的主要方面。如果一个孩子被他人嘲笑,随即大怒并有所回应,那么这样的嘲弄还将继续下去;但如果他选择忽视这些并一笑而过,外人的嘲弄很快会停下来。在学校的那段岁月,也被外界认为是奥巴马学会自我平静的一个重要阶段。
随着时间推移,邓纳姆对奥巴马未来的设想出现了变化。“她以前常常鼓励我尽快适应印尼的文化习俗,她教育我不要像其他美国人那样无知傲慢。但是后来她的看法改变了,认为美国人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人生可能。我是一个美国人,正如她所决定的,我的生活应该远在印尼之外。”奥巴马在回忆录中写道。
1971年,邓纳姆告诉奥巴马,他可以返回夏威夷,并进入著名的普纳荷学校就读。当初,只有6岁的奥巴马跟着母亲来到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雅加达,而现在,10岁的奥巴马将再次启程,不过这次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去年七月,奥巴马在聊起这一系列的离别时对我说:“这种事情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简直难以接受。”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奥巴马,谈起自己的母亲时显露出复杂的感情,既有爱意又有一丝距离感。“现在我也成为了一名父亲,回头再看当年,我能感觉到那种事情对一个孩子有多艰难。”
谈起母亲时,奥巴马的语调中还时不时流露出一些宽容之情。或许正是这种语调能让人觉察出,奥巴马在一次次和母亲离别中历练出了耐心;也正是这样的语调让人感觉到,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会以怎样成熟、宽容的视角来看待父母。对于奥巴马来说,母亲给予他最重要的礼物是:“无条件的爱,超越了生活表面的风风雨雨,是维持我的全部力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