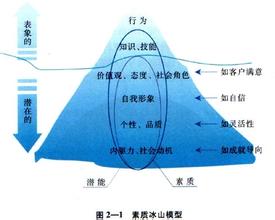张耀翔少年时爱玩七巧板、九连环、围棋。他说,从这些游戏里,可以测知人们智力的差别和学习、办事的能力。并自编了“常识问答”游戏,名为“养脑片”,用以测量人们的反应快慢。
林语堂在20岁前,就知道古犹太国约书亚将军吹倒耶利哥城等故事;可是直到30余岁,才知道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孟姜女哭夫以至泪毁长城的故事。
盛成自从西亚沙漠旅行之后,觉得宇宙间最可读的书,就是自然;后来他到丹麦后,曾爱读安徒生的童话集,觉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时,曾对同学潘光旦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物理学家吴大猷高小时爱读旧小说,第一本是《粉妆楼》,第二本是《说岳全传》。因此他历史、地理成绩最好,而成绩最劣是算术,四则题完全不懂。
林庚称,他由清华大学物理系转读中文系,是受郁达夫小说和丰子恺漫画的影响。
谭其骧在读大学时,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转了三次系才决定了自己的专业。他第一年读的是社会学,第二年读的是中文系,第三年头两个星期读的是外文系,到第三个星期才转入历史系。
熊佛西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每每喜于课堂打瞌睡。一次,地理教员讲罗马尼亚一节,先询问谢冰心的意见。谢尚未答,教员转而问熊。熊因瞌睡,根本不知教员讲的什么,于是情急生智,回答:“我同谢女士的意见完全一致。”弄得满堂大笑。
林汉达有感于蒋梦麟、朱经农说他“连个博士学位也没有,还谈什么教育”,便在37岁时到美国留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得到了“金钥匙”奖。
【沈从文和张兆和】
沈从文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书,第一次上讲台,看见学生挤得满满的,他涨红了脸,好半天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讲堂,看见你们人多,害怕了。”
谛闲和尚在北京讲《楞严经》,袁世凯阴谋复辟,授意寺庙参予劝进,谛闲拒绝,说:“僧人惟知幸持佛法,不知有民主、君主。”
熊佛西平日出门作客,戴毡帽,着长袍,谈起话来声音洪亮,很像一位老法师。赵景深著文写到:“每见到他,我几乎想合十向他念一声‘阿弥陀佛’,作为见面时的敬礼。”

蓝公武在北平中国大学教书,用《资本论》体系讲授经济学;后来他受日本当局迫害,经济窘迫,靠典当维持生计,以至拿金牙托换了苞米面。
陈遵妫说他与张钰哲是“七十载五同老友”:(1)同是福建闽侯人;(2)同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直隶会馆畿辅中学读书;(3)抗战前同在中国天文学会出版的《宇宙》杂志共事;(4)1941年同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工作;(5)在昆明凤凰山天文台时,两人朝夕相处。但是两人性格迥异,在处理问题时常是见仁见智。然而绝无私人芥蒂。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每日出寓至研究院,均要经过颐和园。但他工作完毕即返家,如此3年。他说:“吾自来此处,未窥颐和园。”但他没想到,他最终还是在数年后(1927年)投了颐和园昆明湖自尽。(摘自李子迟等人著《道可道:民国学人大师真闻录》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