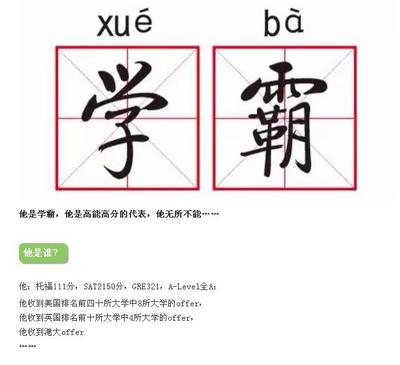三联恋爱婚姻配图
①
我讨厌隔壁的黑妞。
在这个古老的二居室的东卧里,我已经住了三年,西卧的租客换得像快餐店翻台一样频繁,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美有丑,但没有一个像黑妞这么烦人的,她制造的垃圾和噪音以及霸占卫生间的时间都是我的十三倍以上,她凌晨两点还在声嘶力竭地讲电话,她的草莓烂成水了也不扔,每天她喷了香水穿着薄纱黑超咣铛一声打开门高冷地走出来时,都有一群小黑虫欢快地跟着飞出来。
我不擅长指责和吵架,所以只能暗自祈祷她速速搬走,祈祷某天下班回家,发现她扔在客厅的十几双高跟鞋和吊在过道里的内裤文胸长筒袜以及她的全部家当统统都不见了,而我永世不再和此类人种相遇。
可那一天却千呼万唤总不来。我只好采取阿Q式的自我救赎法,每天靠默念“我这点苦难算什么,她未来的老公才真叫惨”强撑着过下去。
问题是这种女人能找到老公吗?我有一天忽然开始怀疑。这怀疑令我的自我拯救失效了,我意识到自己的苦难也许永远不会有人接盘。
于是我不得不考虑离开这个早住惯了的廉价小窝,以每月多付三百块的代价,告别黑妞的蹂躏,尽管我刚刚换了工作,囊中相当羞涩。
不想,我正焦头烂额看房子,黑妞领着男朋友回来了。
看到那个比黑妞还黑的男生的时候,我百感交集。他友好地跟我打招呼,我更友好地回应他,还顺手把正在洗的葡萄分了一半给他们吃——我知道这种嫁祸于人的行为是可耻的,但当传说中的礼义廉耻遇上每月三百块的额外花销时,我还是屈服了。
人穷志短没良心。这是我姥姥说我二表姥姥的。我也没好哪儿去。
好在黑妞和她男朋友没有让我白白背负道德压力,他们看起来相处得非常不错,还在那个小黑虫萦绕的房间里共度了一晚。
看来真的有那种宽厚大度不拘小节、只求温软女人香不在乎满屋垃圾臭的男人啊。我感到欣慰,默默祝福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万没想到,不久之后黑妞居然又带回来一男生。而且比之前那位更高,更瘦,更好看。我太惊诧了,以至于那男生向我点头微笑时,我只“啊”了一声,一点笑都没挤出来。
回房间镇定了一会,我决定弥补。于是又洗了一盘葡萄端过去。
黑妞没在。男生正提着个大塑料袋把她那些长了毛的面包、水果往里装,我端着葡萄找不到地方放,他也找不到,但他很快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两张铺在床上说,放这吧。
这个举动让我知道他是个干净人。
放下葡萄,我礼貌性地问:那谁呢?——我都不知道黑妞的名字。
他笑笑说,去我那边了。
嗯?
今天她住我那边,我住这儿。
嗯?
我是他男朋友的室友。
噢。我恍然大悟。随即邪恶地看了一眼黑妞的单人床,它确实太小了。
②
爱干净的男生越来越频繁地来我们这边住。这是个好现象。更好的现象是,他每次来,都从黑妞房间里弄出许多垃圾,顺带着把客厅走廊厨房都清理一遍。他还爱做饭。所以当我下班回来,打开门闻到菜香,又看到整洁的客厅,就知道他又来了。
可想而知我多么欢迎他的到来。这欢迎直接写在我脸上,每回我们在这小房子里狭路相逢,我都像见了吉祥物一样,笑得很开怀。
这友好想来吉祥物是有感应的。我一见他就笑,他也一见我就乐。有一回我赞他刚炒好的回锅肉“好香”,他立刻说,拿碗来,分你一半!我哪里好意思,赶紧说不用我吃过了。然后钻回房间关上门,狼吞虎咽吃了个面包,把那个小谎言变成现实。
不过虽然没尝到他的回锅肉,那天我们却一起分享了两集《纸牌屋》——其实我们都知道对方在追此剧,因为每次晚饭后,两个房间传出的都是安德伍德那老奸巨猾的独白。
这回吉祥物把笔记本搬到了客厅,招呼我说,一起看啊。
我当然没意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何况跟男生看这种剧,还有个通行的福利:遇到不懂之处,他会暂停下来,给你讲那些晦涩的梗是何隐喻。
在这方面,吉祥物尤其合格。他甚至能指出一些翻译的误差,哪里跑偏了,哪里夸大其词了,哪里流于表面了……我们像看足球比赛一样边看边解说,两集剧足足看了两个半小时。最后还意犹未尽,补充性地加聊了一会儿。聊美剧,聊中国政治,聊房租,聊我们自己。
于是我知道他在一家小公司做翻译,业余给另一些小公司翻译产品说明书,给混日子的研究生翻译毕业论文,给不提气的中学生做家教。
我还知道了他叫苏奇志——从他电脑桌面的文件名上看到的。
第二天,苏奇志直接做了两人份的晚餐。我一回去他就从厨房探出头,隔着一层淡淡的油烟冲我大声说“先别吃饭啊,今儿我宴请你。”我扭捏了一下,接受了。然后换了鞋挤进厨房说,那我来帮你吧。他连连摆着油花花的双手像轰鸟似的往外轰我“出去出去,等着就行。”
厨房太小了,确实不适合两个没有特定关系的单身男女同时容身。我于是退出来,回到卧室,坐下,又坐不住,不时起身往厨房偷瞄。
网上曾有个关于“男人什么时候最美”的讨论,有很多答案我都赞同,比如对着镜子拉一下领带,弯腰轻抚一只哈巴狗,演说前稍作停顿目光扫视全场……现在我想追加一条:捧着肉片站在油锅前,安静地等着葱姜爆出香味儿的男人,也是极美的。
在这个肉香沉醉的傍晚,我有点出神了。
苏奇志的手艺确实不错,他说这得益于大学四年在餐馆打工的苦逼岁月,当时为了多赚点,他在洗碗时偷师学艺,慢慢升级为主厨,于是学费生活费就全搞定了。我表示敬佩。他淡然一笑:穷人家孩子嘛。
他笑得淡泊又明亮,像雨过天晴后山顶的阳光。
不好意思,我又出神了。
后来他洗了碗、收拾了厨房、倒了垃圾,又抱出笔记本,熟练地打开《纸牌屋》,我看着他那只握着鼠标的干净细长的手,忽然有点想握上去。
当然,这太唐突了,我可不敢。
转天,我提早下班,去肉店买了一大堆排骨。礼尚往来,该我请人家了。
可迎接我的,却是黑妞那双久未露面的高跟鞋,和她房间里传出的一声声哀嚎——我不要听你解释!啊啊啊!你倒是说呀!啊啊啊!闭嘴你这个骗子了!啊啊啊……
我胸闷异常。默默回到房间,放下排骨,泡了包方便面,伴着隔壁的哭叫声艰难地往嘴里塞。我塞一口,她骂一声,我再塞一口,她又骂一声。我本来口味就不重,这种佐餐对我的身心实在是巨大的挑战。我数十次想放下筷子走出房间,去敲她的门,对她说,别作了,秀下限风险很大的,你这样的……还是乖乖回到他的怀抱吧,现在就去,撒个娇卖个萌,跟他白头偕老,顺带着,把苏奇志给我换回来。
——呃是的,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最后这句。

晚上八点,新的《纸牌屋》更出来了。我第一时间打开,却看得兴味索然。半集没看完就关了。倒不是因为隔壁哭声的干扰,而是我想到了一句话:好东西要与爱人分享。
我想跟那个人分享。
不知道他怎么想呢?
③
黑妞没有跟她男朋友和好。我一个人把排骨炖了,没精打采地吃了三天。
啃完最后一块骨头,我把垃圾装好,提着出去倒,结果一开门,就见苏奇志和黑妞的男朋友站在外面。
我们,来劝劝她。苏奇志说。
啊,欢迎!我使劲矜持着,音调还是带了点欢呼的意思。
黑妞是何等敏锐,闻声立刻从房里蹿出来,不由分说把他们往外推。
我拼命拉她,嘴上说着不要这样啊,心里想着不要连累我啊。
所幸黑妞以一敌三,不是对手,很快败下阵来,和她男朋友钻进卧室鬼哭狼嚎地去算账了。
我和苏奇志站在客厅,有点无奈,有点尴尬,又还有点意味不明的欢喜。
苏奇志看了看被黑妞摆得不堪入目的客厅,轻轻摇头,小声说,是有点不招人待见哈。
我说何止啊,简直是招人起杀心——到我房间吧,好歹能坐一下。
苏奇志在我唯一的椅子上正襟危坐,比拍一寸照片还规矩。
男人和男人真是天差地别啊。我不禁想起了两个月前刚刚停止交往的那个男人。我们第二次见面,他就把手放在了我的大腿上。这多可恶。更可恶的是,我竟然没有拒绝。这使我至今都无法原谅自己。我为什么不拒绝呢?就算他是我老板,是业界精英,是女人们趋之若鹜的一块大肥肉,可我明明早知道这块肥肉上已经落满了苍蝇,而我根本不是那些同类的对手,竟然还傻不愣登地去尝试了,傻不愣登地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脏兮兮黏糊糊的无脑寄生虫。
那些被他沾染的污腐,我正极力洗脱。而他留给我的大牌包包、首饰、大衣,我还没想好如何处置。它们现在就堆在苏奇志身边的箱子里,他显然注意到了。
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注视它们。而我也在用同样长的时间搜肠刮肚找说得通的解释。
可是就像一个手拿赃物的小偷被逮个正着,用什么谎言才能洗脱嫌疑?
我想不出来,只好发起别的话题,我说,这几天没看《纸牌屋》,不知道安德伍德那老家伙怎么样了。
苏奇志端正地坐着,说,我也没看。
我说那天我买了好些排骨,想回请你呢,可是你没来。
他笑笑。眼睛又落在那堆大牌蠢货上。
气氛僵滞起来,我正绞尽脑汁寻求破解,隔壁忽然传来一记耳光的脆响,接着就是男人忍无可忍的怒吼:打我?我弄死你!然后桌子椅子都噼里啪啦地响起来,黑妞高分贝的尖叫变得异样。
不好!苏奇志倏地站起身夺门而出。我紧随其后跟到了西卧门口,只见那个血脉喷张的男人正死死掐住黑妞的脖子,饿狼一般。
苏奇志冲过去掰他的手。饿狼不放,凶神恶煞地说:她打我!
苏奇志一拳砸在他小腹上:她是女的啊!你打女人算本事?!
饿狼丧失了理智,放开黑妞挥拳回敬苏奇志。黑妞趁机爬起来,嚎叫着冲了出去。饿狼犹豫了几秒,撒腿往外追。
那一对转眼间消失无踪。苏奇志揉着胳膊说,这货真下狠手啊。然后拉起衬衫的袖子,一片淤青。
我没料想这么严重,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他却迅速躲开了。我的手停在半空,好尴尬。
哦不是,我,我没关系,苏奇志有点结巴了,穷人家孩子,被打惯了。
我缩回手,脑子飞速转了几个弯,忽然明白他要说的不是“被打惯了”而是“穷人家孩子”。
我也是穷人家孩子,我说,跟你一伙的。
苏奇志很认真地看我,目光灼灼有力,我要花很大的勇气才能接住。所幸我接住了。我们对视的时间超过了三秒,这三秒让我们心里都有了数。
你说他们还会回来吗?我说。
希望不会。他说。
④
黑妞果然没回来。我和苏奇志坐在我的床上,心神游离地补了三集《纸牌屋》。到第四集广告时,他的眼睛又飘向那堆大牌。
我终于摁下笔记本,毅然说,我跟你说过两个月前刚刚换了工作吧?
他点头。
现在我想告诉你原因,原因是,我跟老板分手了。
苏奇志看着我,目光忧郁。
我没要过他一毛钱,我说,那些东西,我先前以为能代表一些真诚和爱,其实根本不是,那只是一种低级的交换,我换来了才知道,它们毫无意义,也可能是我的能量太有限,换了这些,就换不来一颗真心,我过去高估了自己,以为只要抓住机会用心用力,就什么都能得到,纯粹的鲁莽和无知。
苏奇志起身拿起一个粉色香奈儿山茶花链条包,看了半天,转头问我:没有这个,也能活下去,对吗?
能。我十分肯定地说。
可是我上一个女朋友,就非要买一个这样的包,我买不起,她就找别人去了,现在她有了好几个。
可是她没有了你,她是个傻姑娘。
偏偏我遇到的都是这样的姑娘。所以一看到你这箱子,我真有点怕了。
你刚才英雄救美都没怕。
我能打败活人,但我打不过香奈儿、凯迪拉克、二百平的房子。
那些我都不要。我本来也配不上。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配得上你。
苏奇志笑了,伸出他白净美好的右手,慷慨而认真地,交给了我。
⑤
第二天,我和苏奇志抬着那个大箱子去夜市上摆了个小摊。路过的女人有福了,她们花三百块就能买到原价一万三的包包,虽是二手,也太合算了。
可惜逛夜市的小姑娘,识货的实在太少,没什么人照顾我们的生意。那一堆曾经以晃眼的价格雄踞在专卖店里大牌货,因为失去了标签,又摆在一条破床单上,完全不如旁边五块钱三双的袜子有吸引力。
我替它们感到羞耻。抬回去吧,我对苏奇志说,送给隔壁——
“黑妞”俩字还在喉咙里,苏奇志忽然说起了鸟语,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一外国女人,她已经走过去了,又被苏奇志的鸟语吸了回来,俩人呜里哇啦讲了几句,外国女人蹲下来,饶有兴致地把我们的货翻了一遍,然后,全买下了。
三千块。是我们那晚的收成。也是我那段感情的最后结算。
我们帮外国女人把大箱子拖到她的车上,她很开心,临别时握着苏奇志的手庄重地说了句什么。我以为是“你是个好同志”之类的,但苏奇志告诉我,她说,那是真正的奢侈品。
我拉过苏奇志的胳膊,说,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就在那一刻,我忽然对前男友释怀了。他用一段假冒伪劣的感情,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男人才真的可贵。
男人的种类五花八门,最粗略地分,也有里里外外都很庸常的,有从内到外闪闪发光的,有挂了大牌标签的烂货,还有,摆在地摊上的奢侈品。
这四种男人我都遇到过。第一种我不想要,第二种我够不着,第三种我以为是小棉袄,拿到手才知道是块破抹布,非但不能温暖和保护我,还把我弄脏了,唯一的用处是,他擦亮了我的眼睛,让我能够准确认出第四种男人——真正的Mr. superstar。
对于一个待嫁的女孩来说,运气固不可少,但识货无疑更重要。我很替苏奇志的前女友们惋惜,她们为了追求商场里的假大牌,轻易放掉了地摊上的奢侈品。人生的糊涂有许多种,这是最令人扼腕的一种。
要不要送一首老歌给她们呢?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
哦对了,我姥姥还说过,得了便宜别卖乖,金银财宝要偷着带。
哦,亲爱的苏奇志,如果今夜我在梦里笑得像个傻姑,请别见怪,我只是太得意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