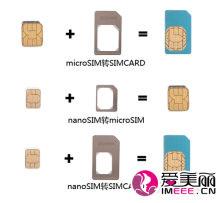在异国小男生眼里,东方女人是神秘的,我在他眼睛里读到了渴望与迷恋。于是,我任由他年轻的手握住我的手指,任由他刚嚼过口香糖的嘴贴在我的嘴上,任由他像山羊一样瘦而机敏的身躯把我抵在墙角暗处…… 去年被公司派到洛杉矶分公司,呆一年的时间。 一年之期快到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趟纳什维尔。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起,这里就成为美国乡村音乐的出版中心。多少我喜欢的乡村音乐手就是从这个地方起步的,现在还有许多音乐小青年来此撞运气。 晚上我在一家叫“枪”的下等酒吧喝酒。这里的墙壁终年脏兮兮的,醉醺醺的游客与浓妆艳抹讨生活的女孩子搂抱在一起。空气里充斥着体味与劣等香水混合的气息。我和这个环境如此不搭调,我的白领气息(尽管我讨厌这说法),我的黄种人身份,我脸上异乡人的好奇让我在黑人白人中显得如此突兀。 我拿起一支烟,想要掩饰自己的不安,在吐出第一口烟雾的时候,我看到了——他。 他怯生生背着吉他站在吧台前,衬衫领口处可见到青筋。他头发柔美,肤色苍白,嘴唇红润,身体的曲线却是硬朗的。他是这里的驻唱歌手,他开始唱了,他的声音笨拙却又温柔,散发着松软的稻草垛与妈妈厨房的味道。 他也注意到了我,嘴角浅浅的笑意是冲我来的。他唱完歌,犹豫再三,终于坐到了我的面前。我打量他,年龄不会超过22岁。他真是柔美得如变成了水仙的希腊美少年纳喀索斯。 几杯酒下肚后,他的慌乱减少了,笨拙却增加了。在他打碎了第三个酒杯的时候,我终于抑制不住母性泛滥,这小孩,可怜的小孩,可爱的小孩,俊美的小孩… 而他呢?在他眼里,我这样的东方女人是神秘的,我的消瘦、忧愁、黄皮肤共同造成了他错误的幻想。我在他眼睛里读到了渴望与迷恋。 于是,我任由他年轻的手握住我的手指,任由他刚嚼过口香糖的嘴贴在我的嘴上,任由他像山羊一样瘦而机敏的身躯把我抵在墙角暗处…… 晚上,我们去了一家汽车旅馆。是的,汽车旅馆比昂贵酒店更符合他的身份,他不过是底层人家里一个渴望成为音乐人的惨绿少年。这里充斥着过路司机与下等妓女混杂起来的大胆情欲。 在N杯烈性酒之后,我性格中的另一面被“砰”一声激发了。我不是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不是名校的MBA,只是一个寂寞到要枯竭的女人。我不再信任男人说的“你是手掌我是掌心”这样的甜言蜜语,却更愿意被单纯的男人的美色打动——在那时刻我理解了王菲多年前之于谢霆锋的选择,找不到好的,就找一个帅的。 这个小男人,啊,在昏昏的灯光下他肤色青白,眼神迷离,他的动作还不纯熟,他的喘息里没有丝毫技术的成分,他偶尔露齿一笑,牙真白,灿烂得要把夜晚都融化掉。这个夜晚,我几乎要像诗人海子一样呐喊出: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只想你。 过了三十岁的男子是腐烂的,只有二十几岁的男子清新欲滴。 我们友好地道别了。大概在清晨的阳光里,他看清楚了我眼角的皱纹,和脸上因岁月而密集起来的沧桑。应他的要求,我写给他在北京的联络电话。这有用吗?他会在我走后把记录号码的纸撕成碎片,而后去和他年轻健壮得如小马驹的女友约会。我有点伤感地想…… 一个月后。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 我是西蒙,还记得吗?“枪”酒吧……我在北京……只为了找你。 他来了。带着比我年轻十二三岁的身体,带着对神秘东方女子的渴望,带着那俊美柔弱得让人心碎的脸庞,来到我的身边了。于是,他开始在北京的酒吧唱他那温柔的乡谣,守着35岁的我。终有一天他会离开我,但那又怎样呢?如今才是唯一。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只爱英雄不爱美男的女人,甚至在看昆曲《牡丹亭》的时候,把那个拿腔拿调的奶油小生柳梦梅骂得什么也不是。“我爱的男人一定是要让我有崇敬之情的,他应该成熟、刚毅、喜怒不形于色甚至可以有点大男子主义。” 这是我一直遵守的寻夫标准,其间一些小白脸、小屁孩我都视若不见,直到我遇见基本符合标准的老公,才咬牙嫁了。 但是婚后不久,我的审美观却有了变化,眼见着一个个漂亮男生,忽然觉得也蛮养眼的。先是跟着老公看世界杯,他看球,我看人。某日偶然发现了一个美男评选的节目,既然人气最高的超女,都走中性路线,不如来欣赏真正的美男呢?虽然里面不乏想扇他大嘴巴的娘娘腔,但是也有不少硬朗英俊的少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