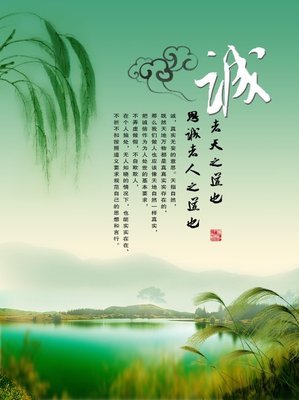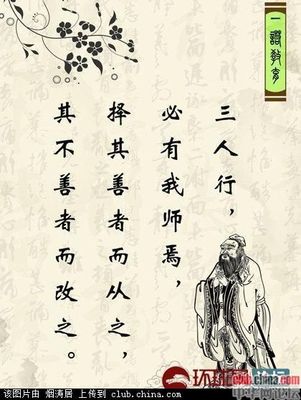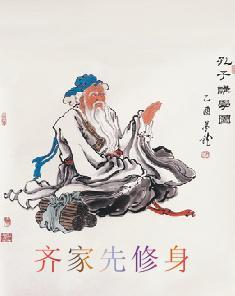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曹玉林
摘要 离开具体的、复杂的、千差万别的人和事,孤立的、抽象的、先入为主的争论人性之善恶是荒诞的,也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因此,性善性恶的争论,只能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伪命题。 争论各方的观点评析人性,究竟是本善还是本恶,这是中国传统思想史上的一大悬案,自其产生之初,两千多来一直争论不休,聚讼不止,其间尽管儒家的性善论乞灵于国家哲学的垄断地位和强势话语,似乎一时占据了上风,然而却也并非定论。实际上这场争论从一开始便迷失了方向,误入了歧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为了理清思路,我们不妨先来梳理一下各方的观点和依据。
历史上围绕人性之善恶,争论各方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
一、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而“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二、性恶论,以荀子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之理亡焉……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三、性无善恶论,以告子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性无善无恶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爵,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告子上》)
四、性有善有恶论,以孔子再传弟子世硕和汉人杨雄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性善,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世硕·养书》)“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杨雄·法言修身》)
除以上四种观点外,西汉董仲舒及唐人韩愈则将人性分为善、中、恶三等,亦为一说。然此种观点不过是对现实情形的简单分类,游离了关于普遍人性善恶的争论焦点,无太多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还有一点须提及的是,作为儒家思想开堂说法的宗主,孔子对于人性善恶并未明确表态,只是喟叹:“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性
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而至于这种“欲”和“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则未予正面置评。
审察以上四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告子的观点和世硕、杨雄的观点较合情理,也较接近于事实。因为他们的观点不是非此即彼的绝对性结论,而是不仅充分考虑到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且对后天的影响和作用也予以高度的重视,故而较为客观,也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相对而言,孟子和荀子的观点则是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显得过于简单和粗糙,难为法音。
不过,如果再进一步分析,荀子的观点较之孟子的观点还是要稍稍合理一些。因为荀子的观点虽然有失单薄,经不起深入探究,如对人的“好利之心”、“疾恶之心”、“耳目之欲”等等,一概引伸出“恶”的结论,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故而有片面绝对之嫌,但缘于人的先天生理欲望所致,在完全排除外部因素的条件下,往往易于为恶,难于向善的特点,荀子的观点多少还是反映了某种客观事实,不是先入为主的强辞夺理,而相比之下,孟子的观点则是罔顾事实,完全是强辞夺理的诡辩了。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便经不起推敲。我们知道,不论中外,也不论是史书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有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者固然是大多数,但绝非是全部,对此视而不见,妄下“人皆有之”的断语,无疑是轻率的。而至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更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所谓“是非”因人的立场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亦即人们所常说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难以定论;其次,由于人的私心所致,当“是非”与利益发生冲突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的,现实中的情形往往正好相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是,所谓“恻隐之心”等等,尽管也许是大多数人所共有,但反之,诸如嫉妒之心、贪利之心、虚荣之心、报复之心等等,又何尝不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因此,仅仅因为大多数人有着“恻隐之心”等等,便凿凿而言人性本善是不慎重的,也是不能成立的。而更经不起推敲的是,孟子将人性与水性相类比,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纯属主观臆断的先验之说。理由是,首先“水之就下”乃地球引力所至,与水性无关,孟子的类比属无知妄说;其次若“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则孟子在论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极力推崇的“舍生取义”就不过是寻常应有之举,又何贵之有?最后,即使再退一步,按照孟子的逻辑,性善论也不能自圆其说。众所周知,依据公认的常识,无疑是优者为上,劣者为下;雅者为上,俗者为下;正者为上,负者为下;清者为上,浊者为下。若依照孟子所谓人性如水性的类比,也只能得出人性恶的结论,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人性善的结论。而至于孟子所谓“水,搏而跃之,可使过巅;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孟子·告子上》)云云,则不但丝毫无助其观点的成立,相反,只能益发表明人性天然的有着向下的趋向,不施之以外力,则不能向上的事实。由此可见,孟子先验的性善论是不正确的,也是缺乏根据的(孟子惯于诡辩,《孟子》一书中像这样随意取比,言不及意,强辞夺理的例子甚多)。然而令人不无困惑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牵强附会,破绽百出的说法,长期以来却被很多人视为金科玉律,不但为后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人士推崇备至,谓“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说》),而且还被当作不容置辩的真理,载入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作为开篇之语,诚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悲哀。
不过,以上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或换言之,问题的更重要之处在于他们各方争论的焦点是人性的善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人性则语焉不详,因
此,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争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更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人性为善抑或为恶,是价值判断;而什么是人性,则是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在事实判断不明确背景下进行价值判断的争论是荒诞的,也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之所以说性善性恶的争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其主要理由即在于此。
何为人性
那么,什么是人性呢?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回答也许并不困难,即人性,指的是人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自然天性。然而若深入下去,结合到现实生活进行解释却绝非易事。在上面的回答中有两个关键词:其一是“固有的”,所谓“固有的”,意思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的,受环境影响或客观因素的作用所造成的;其二是“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意思是人所特有的,其他生物包括任何再“聪明”的动物也决不可能具有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不言自明的要求,也是该定义的题中应有之意:一、这种自然天性须是人所共有的,而不是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的;二、这种自然天性是稳定的,不因外在环境或客观条件的改变而轻易改变。下面我们就以此为坐标,来对照衡量一下前人的说法。
在前人关于人性是什么的论述中,最著名者,也是影响最大者,当属以下两句话:一句是告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另一句是《礼记·礼运》中所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应该说,这两句话意思相同,都是正确的,或者说都是基本正确的,然而,这两句话却又是有着致命缺陷的。其缺陷就在于“食色”,或者说“饮食男女”,固然是人先天就有的自然天性,但可惜的是,这种自然天性却决非人所独有,并不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先天特性,或换言之,并非是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属差”。因为不仅仅是人,而且几乎所有的动物和绝大多数的植物,都具有这一自然天性。动物或者说禽兽一目了然,无须多论,而植物的吸收养份和花粉传授,便可以归之于“食”和“色”,甚至相当一部分微生物也具有这一自然天性,如很多微生物的吸取水份和自我复制,也可以归之为广义上的“食”和“色”。因此,上述“食色”即为人性的观点是不严谨的,也是不全面的。因为它遗漏了人性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本质的东西。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意思是人与禽兽等不同的地方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如果人仅仅只有“食色”等生理本能,便与禽兽无异了。孟子这一次倒是说对了,也算是点到了上述说法的软肋。
那么,人与禽兽等其他生物不同的“几希”之处是什么呢?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即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乃在于“有教”还是“无教”。何为“有教”?教者,教育、教养也,不论是教育、教养,还是教诲、教化,皆是后天的,何能称之为人性?故而孟子又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人性之善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这里显然有矛盾了。孟子
似乎发现了这一点,对此进行辩解,举例说:山上的树木原本是很茂盛的,可如果老是用斧子去砍伐它,还能茂盛吗?树木虽然在生长,雨露虽然在滋润,但新枝嫩芽还没长出来,又去放羊放牛,于是就变得光秃秃的了。人们看到山上光秃秃的,以为原来就没有没有树木,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有些人之所以没有仁义之心,正如斧头对待树木一样,天天去砍伐它,所以善念不能存在。“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有材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意思是人性原本是善的,与禽兽是完全不同的,之所以有些人性恶,让人看起来似乎和禽兽差不多,其实是后天的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先天的,于是又引出了为人必须要修身,而修身首先要克制各种欲望的观点,即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而孔子的“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等等,也是要求人们要克制自己欲望的意思。对此,宋人朱熹则进一步予以解释和发挥,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子语类》),要求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此外还有,儒家认为人的天性是有区别的,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几希”之处,“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等等,等等。
综合以上诸多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自相牴牾之处甚多,最主要者如:一、既说人性之善乃先天所固有,但同时却又说这种人性之善须经后天的修养和教化才能获得,二者难以自洽;二、“君子”与“小人”甚至“庶人”的人性不同,有悖人性乃人所共有的普遍性原则;三、既然人性本善,何来致人性恶的后天环境,而人性之稳定性又为何不能抵御这种环境,反而与之一拍即合?四、“食色”既是欲望,又是需求。这种欲望和需求究竟是人性抑或兽性?若为前者,为何要对其“克”之和“灭”之?若为后者,人为何却有兽性?等等。总之,上述儒家的观点,多为先验的即兴之说(孟子将“仁义礼智”比为人之“四体”,便属典型的信口开河),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逻辑链条,更有违关于人性的要求和定义,诚不足为据。
在回顾和分析了前人关于何为人性的种种说法及其失足之处后,再来寻找正确的答案,便较为容易了。我们知道,人的生理欲望不等于人性,然而生理欲望却是人性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生理欲望,乃破解人性之谜的钥匙。因此,我们寻找人性的正确答案,首先须将目光投向人的生理欲望,看一看人与禽兽在生理欲望方面都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page]
人与禽兽在生理欲望方面的共同点一目了然,那便是前文所说的“食色”之欲。“食色”之欲乃生存所必须。为了生存,第一要“食”,不论人还是禽兽都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在“食”的问题解决之后,紧接着便是“色”,所谓“饱暖思淫欲”,不论人还是禽兽也都一样,也都没有任何区别。“食”的理由很简单,无“食”即无命,但为何要有“色”呢?或曰为何要有性欲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凡生命皆有终点,为了生命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唯有繁衍和生殖,而繁衍生殖,就必须借助于“色”,就必须有性欲,这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而至于为何会有这种本能,则任何科学都无法作出令人信服、令人满意的回答。要回答它,唯有宗教(科学可以对本能的表现及其性质作出解释,但对其来源却无法作出解释,而这也就为宗教留下了充分的生存空间)。故而从现象上看起来,人与禽兽在生理欲望方面是相同的,没有区别的。不过,这种“相同”和“没有区别”只是表面上的,若深入一些进行观察,人与禽兽虽然同有“食色”之欲,但其实
现方式和内在机制却是不同的,而且这种不同还带有某种根本的性质。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禽兽的“食”,仅仅是为了饱腹,单一地执行维系生命的充饥功能;禽兽的“色”,仅仅是为了繁衍,单一地执行传递生命的生殖功能。而人的“食”和“色”,则除了为了饱腹执行维系生命的充饥功能,和为了繁衍执行传递生命的生殖功能外,还有着更多的追求幸福,享受生命的功能。而且这种追求幸福,享受生命的功能,其价值和意义有时甚超过了“食色”原本维系生命、传递生命的功能。如人对于“食”,固然是为了维系生命,但却又并不仅仅满足于维系生命,而更多和更重要的是为了享受生命,为此,人只要有条件、有可能(“饥不择食”不在此例,属另一种情况),便不仅要要求能够吃得饱,而且还要要求能够吃得好,讲究“食”的色香味形及盛食物的器皿;不仅要讲究“食”的环境、氛围和情调,而且还赋予“食”以诸多社交礼仪和表达情感的功能,开发出大量“食”的“副产品”和“附加值”,而这些对于禽兽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再如人对于“色”,最初固然也是为了传递生命,但却也同样并不仅仅满足于传递生命,也同样更多和更重要的是为了享受生命。为此,人只要有条件、有可能(“贫不择妻”也不在此例,属于另一种情况),便不仅要选择交配的对象,讲究交配对象的容貌、品行、知识、谈吐、气质、个性、年龄、家境,而且还要赋予“色”以形而上的感情因素。这种感情因素有时甚至喧宾夺主,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色”的原本繁衍、生殖、传递生命的功能。和“食”一样,人在“色”的方面,也同样开发出大量的“副产品”和“附加值”。而更为甚者的是,到了现当代,伴随着节育避孕的出现和普及,很多人对“色”的传递生命功能,干脆一刀切除,使“色”的目的,只剩下唯一的幸福快乐,享受生命的功能,而这更是禽兽们所望尘莫及的。
二、人与禽兽虽然同有“食色”之欲,但禽兽们的“食色”之欲相对来说,是孤立的、被动的、单纯的、不自觉的,缺乏发展、创造和变化的;而人的“食色”之欲,则是全面的、主动的、复杂的、自觉的,充满发展、创造和变化的。具体来说,禽兽的“食”一方面只是单一地为了维系生命,而另一方面,禽兽们的维系生命,也只有“食”这一种途径,而人的情况显然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一方面除了前者所说的,人对于“食”不仅仅是为了维系生命,而是除维系生命之外,还要享受“食”的美味,开发出大量与充饥饱腹毫不相干的“副产品”和“附加值”,而另一方面,人为了维系生命,也不仅仅局限、依赖于“食”作为唯一的途径,而是还能够借助于营养搭配、环境改善、体育锻炼、医疗卫生、养生保健等等,从而使之成为一个无比巨大的系统工程,而这些无疑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而人也正是借助于这一切,从而实现了对“食”这一原本属于动物性生理本能的升华和超越。同样,“色”也是如此。禽兽之“色”一方面只是单一地为了传递生命,而另一方面禽兽们的传递生命也仅仅只是执行本能的指令,尽管在这种执行的过程中也许不无愉悦和快感,但不论其实现方式,还是交配双方的关系,皆始终拘于固定的模式,一成不变,很少有发展和变化,而人的情形显然也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一方面人对于“色”不仅仅是为了传递生命,而是除传递生命之外,还要享受“色”的快乐,开发出大量与繁衍生殖毫不相干的“副产品”和“附加值”,而另一方面虽然迄今为止人对于传递生命除交配受精之外尚没有更多的途径和办法,但不论是过去的宗族相传、重男轻女、卖淫嫖娼、太监制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是现在的计划生育、丁克家庭、试管婴儿、同姓婚姻、成人玩具、网恋虐恋等等,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也绝非禽兽们的世界
可比,也同样反映出人之“色”要较之禽兽们之“色”更主动,更自觉,也更充满变化与活力。
三、和禽兽的本能欲望主要集中在“食”和“色”两个狭窄的范围不同,人类享受生命的欲望无疑要广阔得多,也丰富得多。这种广阔和丰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人享受生命的欲望不满足于仅仅局限在“食”的美味和“色”的快乐上,而是对身体各个器官和部位进行全方位的试验和探索,努力开发出其潜在的享受功能。这种试验和探索的覆盖范围,不仅包括眼、耳、鼻、嘴、皮肤、四肢等这些显而易见的器官和部位,而且还包括诸如头发、睫毛、指甲、双足、腰脊、臀部等这些往往容易被忽略的器官和部位,可谓无以复加,而且这种试验和探索至今仍未见止息。其次,人的享受生命的欲望,也并非仅仅停留在人的生理范围和物质层面上,而是扩展、深入到人的心理范围和精神层面,从而创造出优美隽永的文学和精彩纷呈的艺术。如同人类基于自身的进化,产生出诸多物质上的享受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从而创造出大量相应的物质产品,而这些物质产品的使用,又反过来进一步提升和强化了人在物质方面的享受能力,增加了人在物质方面新的享受需求,二者形成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一样(关于这一点,在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人化”和李泽厚关于“积淀”的分析中,有相关的论述),人的原本动物性的快感进化为人类的美感之后,也产生了精神上的享受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人也创造出了以文学艺术为代表的丰富的精神产品,而这些精神产品的享用,也同样反过来进一步提升和强化了人在精神方面的享受能力,增加了人在精神方面新的享受需求,二者也同样形成了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一步步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展。最后,人类不仅在享受生命,不断地追求这种享受的最大化和最高值,而且还为这种享受和追求能够顺利进行扫除障碍,设计创造出种种名目繁多的形式、组织、制度和理论,这便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谓“上层建筑”。而所有这一切,都无疑使得人与禽兽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以至最终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类。
总之,综上所述,人类与禽兽虽然一样都有先天的“食色”之欲,然而禽兽的“食色”之欲,始终停留在维系生命和传递生命的低级阶段,而人类则由于不满足于简单地和被动地维系生命和传递生命,而是主动地、自觉地和创造性追求享受生命,故而人类不仅将原本单纯意义上的“食色”之欲加以改造、升华,使之成为享受生命中的一部分,用享受生命的幸福功能,覆盖甚至取代“食色”之欲原本的生存功能和繁衍功能(人在衣、住、行等其他方面,也同样使之兼具实用和享受两种功能,且只要有条件、有可能后者常常要大于前者),而且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构建起无比宏伟的大厦。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享受生命,乃人类一切行为的最高律令,同时也是人所先天固有的,区别于其他所有生物的最重要的自然天性。
并未终结的思考
为了不致发生歧意,徒增纠葛,在厘清了人性的含意之后,仍然不能立即进入讨论人性善恶的环节,仍然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一、要确定善恶的标准,不确定善恶的标准,讨论人性的善恶,只能是胶柱鼓瑟,方枘圆凿;二、要了解人性的特点,不了解人性的特点,讨论人性的善恶,只能是无的放矢,郢书燕说。
我们先来看善恶的标准。众所周知,在人类早期的洪荒时代,是没有善恶概念的,有的只是和禽兽们相类似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丛林法则,从本质上说就是生存法则,即生存是压倒一切的第一要义,为了生存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食人族的故事和传说,即是这一蛮荒时代丛林法则的遗痕。然而当人类走出丛林,进入群居和社会化阶段之后,丛林法则便不适用了。人类在各自追求享受生命这一目的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地搏弈、争斗、磨合之后,终于达成了某种妥协和共识,意识到为了人类整体和长远的根本利益,必须要有约束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而善与恶,即是这一道德规范里的两个最基本的范畴。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如果要对此下一个简单而明快的定义,那便是:凡有利于他人者即为善,凡有损于他人者即为恶;不仅有利于他人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者即为大善,不仅有损于他人而且有损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者即为大恶。
下面我们再来看人性的特点。在上文关于何为人性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人的追求幸福,享受生命的天性,不论在心理取向方面还是在行为取向方面,都有着三个重要的特点。这三个特点分别是:恋生畏死、趋利避害和永不满足。人性的这三个特点如地球的引力,物质的磁场,虽不见其形,不闻其声,然而却又无处不在,随时随地都在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发出切实可据的感召和指令。
具体来说,恋生畏死,亦即人们所常说的贪生怕死(因贪生怕死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有着浓厚的贬意色彩,故此处改为恋生畏死,使之稍稍显得中性一些)。恋生畏死,是一切生命的共性,原因是生命作为个体存在,有着无可逃遁的生命终点,故而恋生畏死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不过,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的恋生畏死的特点无疑要更强烈和更执着。因为人是有思维、有理性的生物,不是像其他生物那样只有直觉、感性的条件反射。人意识到生命的本身是享受的前提和基础,生命不存,享受安在?故而人类不是像其他生物那样听天由命,日复一日地被动活着,直到生命的终结,而是积极应对,采取一切手段,想尽一切办法,为延长生命,远离死亡作不懈的努力。这种基于恋生畏死的努力,在人类的一切行为中始终是居于第一位的。
趋利避害,是人追求幸福、享受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特点。从本质上讲,恋生畏死也是一种趋利避害,而且是最重要的趋利避害,不过那是狭意上的,而这里所说的趋利避害,则是一种广义上的趋利避害。何为利?凡有助于享受生命者皆为利;何为害,凡有损于享受生命者皆为害。人为了享受生命,别无选择地趋向于“利”,千方百计地规避着“害”。这一特点不论是对于人类的心理来说还是对于人类的行为来说,都是天然的、本能的,同时也是贯穿其生命始终的。
人的缘于其享受生命天性所表现出来的第三个特点是永不满足。与前两个特点不同的是,永不满足这一特点是人类所特有的,其他生物都不具有。人类的这种对享受生命永不满足的特点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即既表现在享受数量方面的永不满足,又表现在享受质量方面的永不满足,同时还表现在对新的享受方式、享受内容和享受项目不断创新追求方面的永不满足。虽然有时候有些人,在某一特定阶段有所谓知足感或者说是满足感,但这种知足感或者说是满足感只是暂时的,是靠不住的,是在其某种欲望需求取得的初期,且尚未得到切实保障情况下产生的。一旦这种已实现的欲望需求有了切实可靠的保障,则很快就会产生不满足的念头,从而要去追求新的,更高一级的享受和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甚至将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和自我超越需求六个不同层次,从低级到高级依次递进。由于超越是无止尽,无终点的,故而人类的需求永远也不可能满足。
在扫除了外围的诸多障碍之后,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到性善性恶讨论的正题了。可是当我们将人性的特点与善恶的标准相联系,并加以对照衡量之后,却十分意外地发现,这种对照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原因是,因为人性的三大特点,不论是恋生畏死也罢,趋利避害也罢,还是永不满足也罢,虽然其过程和结果每每有着善恶的分野,但就这些特点的本身而言,却不能简单地与善恶标准划等号。如恋生畏死,其动机无疑是利己的,但它所带来的结果究竟是损人还是利人,却是不能确定的,即生活中既有为求活命而出卖残害他人者,也有虽为恋生其结果同样亦有利于他人者,更有为救他人而舍弃自身生命者,故不可下绝对性结论。趋利避害同样如此。趋利避害在利己的目的性方面是肯定的,但其所造成的结果是损人还是利人,也是不能确定的,虽然由于资源的有限、能力的差异、机会的不均等等因素,人在趋利避害方面无疑更易于为恶,而难于向善,但这并不就等于趋利避害就一定为恶,事实上,与之相反的情形也所在多多,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至于永不满足,也莫不如此。永不满足的前提是利己,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它给他人所带来的究竟是利还是害,则仍然是不能确定的。即若谓其恶,则人类却正因为这种永不满足,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辉煌成就;若谓其善,则永不满足所造成的疯狂贪欲,却又酿就了无数罪恶的苦果。善兮恶兮,委实难以评说。总之,人类追求幸福、享受生命天性及其三大特点,与善恶、利人还是损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若将其加以分类归纳,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八种不同的情况:
一、单纯的利己,既不损人也不利人;
二、利己同时也利人;
三、不利己而利人;
四、利己而损人;
五、不利己而损人;
六、损己而利人;
七、为利他人而牺牲自己;
八、为利己而危害他人,甚至危害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类。
在这八种情况中需要说明的是,第五种情况的“不利己而损人”,实际其损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达到某种心理平衡,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利己。而第六种情况的“损己而利人”和第七种情况的“为利人而牺牲自己,”实际上是缘于行为人将道义上的追求,作为最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而这种体现即为自己最大利益之所在,故而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利己”。

从以上所列的八种情况中可以看出,人类追求幸福,享受生命的天性及其三大特点虽然是一致的,但具体的实现方式和所产生的结果却是不一致,是十分复杂的。而更复杂的是,上面所说的“利”和“损”还有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之分。有时从短期来看是“利”,从长期来看却是“损”;有时从短期来看是“损”,从长期来看却是“利”,不能下简单的结论。另外还有,人的行为其动机与效果往往是不一致的,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有“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之分,善的动机和善的效果,恶的动机和恶的效果,二者之间并非是全然对称的正相关关系,而是有时会发生背离甚至逆反。这种动机与效果,意图与责任不一致的现象,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历史记载中都是不鲜见的。
总之,凡此种种,都只能表明这样一个既让人十分沮丧又令人无可奈何的无情事实,即离开具体的、复杂的、千差万别的人和事,孤立的、抽象的、先入为主的争论人性之善恶是荒诞的,也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因此,性善性恶的
争论,只能是一个徒劳无功的伪命题。
当然,如果因为性恶性善的争论是一个伪命题,就认为这场争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也是不正确的,不公正的。事实上,这场争论的过程和结果,还是引出了一些值得玩味的东西,如:一、既然追求幸福,享受生命,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为何其追求和实现的方式却大相径庭,有着善恶的不同分野?这种分野主要是来自于先天的,还是来自于后天的?若是来自于先天的,从学理上应如何解释?若是来自于后天的,又表现在哪些方面?二、性善性恶的争论,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有着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总体上应如何评价?三、性善论在逻辑上有着明显的漏洞,为何还能畅行无阻,在争论中占据上风?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和历史上的统治者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待于人们去探寻和追索。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