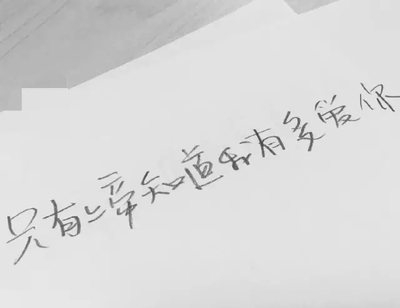故事发生在早年的“人民公社”时期。
汤河边的羊尾巴村里有个女人叫陶燕婷,丈夫进城当了干部变了心,把她给抛弃了。陶燕婷因此大病了一场,从此便在这三间土坯房子里过着孤孤零零、凄凄惨惨的日子,成了丈夫还活在世上的“寡妇”。
在农村一个孤苦无依的妇女,过日子可难可苦了,地里活儿,家里活儿,打个场,修个房的,短不了得请别人来帮忙。有时请了个不安分的,不是说几句撩人的话,就是找个机会摸一把、捏一下,犯点儿坏。碰上了这样的,陶燕婷只得忍着点儿、躲着点儿,唯恐一闹起来人家还得说她不本分,招蜂惹蝶的。
就这样陶燕婷苦苦巴巴熬到“农业学大寨”那阵子。有一天她从自留地里干活儿回来,走到半路上忽然觉得要小解,便走下大道,走进一座废弃多年不用的破窑里,她瞧瞧四处没人,赶紧蹲了下来,哪知道刚蹲下,忽然听见身后啪一声,从高处滚下了一块砖头来。吓得她哆哆嗦嗦地问道:“谁?”没人回答。她心咚咚直跳,壮着胆子又说了一句:“你再不出来,我喊……人了。”她这一招倒挺灵,从那破窑顶的小碉堡上边,露出一个人头来,低声说道:“嫂子,是我。你可千万别喊呀!”
陶燕婷定睛一看,原来是村里出名的老实主儿万东明,她这才放下心来,红着脸问:“我在这里小便,你进来干什么?”万东明颤声说:“不,嫂子……是我先进来的。”“那你看见了没有?”“这……咋说呢?”
话刚一出口,陶燕婷忍不住脸一红,嘴里扑哧一笑,心想:有这么问人家的吗?她朝万东明摆摆手说:“兄弟,你下来吧,咱俩这么楼上楼下的说话多不方便呀。”万东明支支吾吾地说:“不行,我下不去呀。”陶燕婷奇怪地问:“你咋下不来?”“我,我光着身子呢。”
陶燕婷脸上又一阵发烧问:“你穷风光什么呢?”万东明不好意思地说:“不怕嫂子笑话,我就这一身皮,脏得实在没模样儿了,刚才在水坑里涮了涮。我寻思天好,一会儿晒个半干子穿上,谁知……这么会儿工夫嫂子你进来了。”
这个万东明与陶燕婷同村,四十出头了,还是个光棍汉子,要论人吧,长得高高大大、端端正正,手里农家活儿哪样也拿得起、放得下。就因出身不好,高的攀不上,找个哑巴瘸子他不干,所以一直是个“单干户”。在羊尾巴村这么个穷地方,万东明是脱了破棉袄就穿小单褂的主儿,而且是单打一的行头没有换头,所以才闹了这么一出戏。
听万东明这么一说,陶燕婷的心里挺不是滋味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站在那儿发愣怔。正在这时,窑外又传来一阵脚步声,吓得万东明变脸变色,压低嗓门说:“嫂子,来人了,你快出去吧!”说着一猫腰,人便缩进了碉堡里。
陶燕婷也知道此地不能久留,万一让人看见她和光着身子的万东明在这儿,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于是,她赶忙一转身出了窑门,谁知一见迎面走来的人,她更加心慌。这个人尖嘴猴腮,小脸塌鼻蚕豆眼,他叫万宝昌,是村里的大会计,是个谁也不敢得罪的实权派。
论辈分,万宝昌该叫陶燕婷婶呢。可他是个见了女人比猫儿见鱼腥还馋的角色。对陶燕婷早就垂涎三尺,他倒不是真心爱她,而是欺侮她家没男人,想找个便宜。现在他见陶燕婷慌慌张张从破窑里出来,顿时两只蚕豆眼一转,嘿嘿,准是这娘儿们和哪个野汉子在这儿鼓捣什么呢,让我给冲散了?他决定进窑里看看,想看出点什么蛛丝马迹,抓住了陶燕婷的把柄,那她就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任我摆布了。
他抬脚要进窑,可把两人吓坏了,万东明吓得缩在自己垒的小窝里大气也不敢出;陶燕婷吓得连头也不敢回,飞快往家里跑去。
可是,万宝昌刚一步踏进窑门,突然连跳带蹦就逃出来,原来这小子天生胆小,见到个土鳖马蜂都会吓得脸发白。现在看见从砖堆里钻出一条二尺来长的青蛇,晃悠着身子,吐着芯子朝他凑了过来,差点儿没把这小子尿给吓出来。
当天晚上,陶燕婷睡不着觉了,破窑里的事虽没闹出来,可她却可怜起万东明来,那么能干的人一年忙到头,连身换洗的衣裳都没有。人家平日净给自己帮忙,自己怎么就不能帮帮人家?她眼望着屋顶上的房梁一个劲儿地发呆,把万东明平日的好处一点一滴全都想了起来。想着想着,浑身上下像着了火一样热了起来,她躺不住了,打开箱子把丈夫留下的衣服翻了出来。
陶燕婷挑了几件衣服用一个小包袱包好,徘徊再三才夹着包袱走出门,摸着黑,东瞅瞅,西望望,小心翼翼地来到了万东明家门前。万东明家穷得连个大门都没有,她直接进了院子,看看两间小土房黑洞洞的,一点灯火也不见,一点儿声儿也没有。她又犹豫了,进不进去呢?就在这当儿,忽听咔的一声,屋里火光一亮,接着又见一个红火头一闪一闪的。陶燕婷知道万东明是在家一个人闷头抽烟呢,心里一慌,脚下一绊。
这一下惊动了万东明,他问了一声:“谁?”说着趿着鞋走出来。“我。”陶燕婷小声应道。尽管声不大,可万东明听出来了,激动地叫了一声:“嫂子!”
万东明家一年到头难得有个串门的,今儿晚上来了陶燕婷,他不由得喜出望外,声音都有点儿发颤了:“嫂子,屋里坐吧!”“不,让别人看见,那……”陶燕婷说着把包袱递给万东明说:“这几件衣服给你,往后做个什么针线活儿的就来找我。”“行……”“可有一样,千万别让人看见。”没等他回答,她仿佛觉得四周都是眼睛在盯着她,一刻也不敢再停留,又说了声“我走了”,转身就走。万东明抱着那衣服包袱站在院子里,老半天也没动地方。
这天夜晚,月亮圆圆地挂在空中,万东明想着自打穿了陶燕婷送的衣服,心里暖烘烘的,一闲下来脑子里就出现陶燕婷。他想平时叫她喊她,她不睬,可她总是朝着自己甜甜的笑,笑得他浑身麻酥酥的。他见今儿晚上月亮天明的,觉着陶燕婷家的猪圈该起圈了,于是就扛着铁锨,也不打招呼,跳进猪圈吭哧吭哧就干了起来。
在屋里油灯底下做针线活儿的陶燕婷,听见院里有动静,赶紧出来,见是万东明正在起圈,就不声不响回进屋,在一个破了口的瓦罐里掏出两个鸡蛋用水煮了,剥了蛋壳,放在一个盘子里。
万东明只花了半个来小时就将圈起完,又推来新土垫在圈里,这才拍拍手心满意足地刚要离开。忽然听到一声:“等等,”陶燕婷过来叫住了他,“兄弟,你累了半天,到屋里歇会儿吧!”万东明立在院里,没动脚。“快进屋去!”听见陶燕婷催促,万东明便老老实实地跟在她身后进了屋。
陶燕婷让万东明坐在炕上,把那盘鸡蛋端了上来,说:“兄弟,你辛苦了半天,嫂子也没有什么招待你的,这两个鸡蛋将就着吃吧。”万东明接过盘来,对着鸡蛋左看右看,不知该从哪儿下嘴,大嘴一咧,傻乎乎地看着陶燕婷。
“是不认识我,还是没吃过鸡蛋?”陶燕婷说着微微一笑,她觉得自己好多年没这样高兴过了,就好像一场大梦昏昏噩噩地做了许多年,今儿个才从梦中醒来。万东明也觉得今儿晚上可痛快了,他恨不得天天都来给她帮忙,不是为了吃鸡蛋,而是想多看她两眼。跟她一个村住了这么多年了,好像这几天才看出她这么漂亮。“吃呀!”陶燕婷见他净望着自己出神,脸上有点儿发烧,又一次催他快吃。“哎。”万东明答应一声,抓起鸡蛋一口一个塞到嘴里,鼓了鼓腮帮子咽了下去,噎得他直翻白眼,吓得陶燕婷顾不上什么回避不回避的,伸出右拳轻轻地给他捶着,嗔怪道:“看你,倒是慢着点儿呀!”万东明只觉得气往下一顺,鸡蛋全到了肚子里,他顺势拉着陶燕婷的手说:“嫂子,咱俩也跟……”“跟什么?”万东明结结巴巴地说:“跟刘备和孙尚香似的吧!”“胡扯什么?”“嫂子,其实我也知道你挺喜欢我的。”“你别自作多情了。”“那你为什么给我送衣裳?”“那是我看你可怜。”“你还偷着量我的脚印给我做鞋。”“胡说,在哪儿呢?”万东明说着从炕上拿起一只鞋底子在鞋上比了比说:“嘿,正好,我一进来就看见它了。”陶燕婷没话说了,低头不语。万东明又凑过来问:“嫂子,我刚才说的那个事你倒是表个态呀!”见陶燕婷还不回答,他急了,气呼呼地问:“那你也嫌我的出身?”“不,不,”陶燕婷连连摇头,“绝对不是。”“那你倒是说呀!”陶燕婷想了想说:“今儿太晚了,过两天我一定给你准信儿。”说完便把他推出门外。
等万东明一走,陶燕婷可静不下来了,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说实在的,她是既盼着万东明说出那话来,又怕他说。说了一时接受不了,不说又从心里着急。可现在人家说了,怎么办?就在这时,又听门“吧嗒”一声,她以为是万东明又来了,就装作生气地说:“让你等几天,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可要生气了!”
“婶子,你认错人了,是我!”一听这声音把陶燕婷吓了一跳,她听出是万宝昌来了,这可真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她连忙说:“我睡了,你有事明天来吧!”“谁说的,我从窗户眼儿里看见了,你还在地上溜达呢。”万宝昌说着人已进入屋里,满脸奸笑盯着陶燕婷,吓得她往后退了两步问:“你来干、干……什么?”“听说婶子煮鸡蛋了,我也想弄两个吃吃。”万宝昌此话一出,可把陶燕婷吓得一时出不了声。
万宝昌见陶燕婷默不作声,又往前凑了一步,拉着她的手说:“哟!婶子的手好白嫩呀!”“你要干什么?”陶燕婷猛地把手往回一抽。“哟,这会儿正经了,刚才你们俩可是背也捶了,手也摸了,还说什么刘备孙尚香的,咱俩就不兴亲热亲热了?”万宝昌皮笑肉不笑地说。陶燕婷气得浑身直哆嗦:“别忘了,我是你婶子!”万宝昌嘿嘿一笑:“又不是亲的,再说那是封建残余,只要咱俩看着顺眼……”陶燕婷呸了一声:“谁看着你顺眼!”“你看不上我,看着万东明顺溜,可你别忘了,他是黑五类、臭大粪。我把你们的事一抖落,明天他挂着牌子,你挂着破鞋三乡五里转一转,你就美了。”万宝昌说着转身要走。
几句话把陶燕婷吓得魂飞魄散,她紧拉住他的手说:“好侄子,千万别……”万宝昌顺势把陶燕婷揽在怀里说:“好婶子,不,燕婷,我想你可不是一天半天了,你就答应我一回吧!”边说边把陶燕婷按在炕上。陶燕婷到了这种地步,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得像死人一样任其摆布……
等万宝昌满足了兽欲,看着直擦眼泪的陶燕婷说:“燕婷,你也别太那个了,人和人就是那么回事,哪个皇帝没点儿风流事,何况咱们一个平民百姓呢?我手里有点儿权力,也不亏你,往后你的工分按满工记,分口粮时,我称秆一抬,算盘一响,你知我知就行了。”陶燕婷把头扭向土墙,再也不理他了。
真是偷腥猫儿性不改,万宝昌自从那天晚上尝到了甜头,他是每晚必来,花言巧语,软硬兼施地欺侮陶燕婷。
这天晚上,万宝昌把小脸洗了洗又来了,陶燕婷一点儿也没反抗就让他得了手。就在这小子美着时,突然哗啦一声门响,接着咚咚咚地闯进一个人来,一挑门帘进了里屋,来人正是万东明,一下子吓得陶燕婷和万宝昌瘫了。
原来万东明那天向陶燕婷表明心迹后,见陶燕婷并没拒绝,只是让他等几天,他知道事有八成了,乐得天天夜里做好梦。耐着性子等了四天不见回音,沉不住气了,刚才一时心血上涌来找陶燕婷,想锣对锣、鼓对鼓当面问问。快到门口时,正好看见万宝昌进去,他就躲在一边想等万宝昌走了再进去。哪知万宝昌一进去就拉灭了灯,凑到窗根儿一听,顿时怒火冒三丈,不顾一切地冲进屋里。
万宝昌乍着胆子问:“你小子夜入民宅,干……干什么来了?”“还是问问你自己吧!”万东明说着双手握拳,两眼冒火,一步一步逼过来,吓得万宝昌不住地讨饶:“东……明叔,高抬贵手吧!”万东明哪理这一套,他一伸手像抓猫似的把万宝昌提了进来,怒骂了一声:“去你妈的!”就把万宝昌从敞开的窗户里扔了出去,摔得那小子直学鬼叫,然后夹着尾巴逃跑了。
心魂稍定的陶燕婷刚要开口想把原委说清楚,哪知万东明一挥手制止住了。他双唇紧闭,鼻孔里出着粗气,胸脯一起一伏地说:“难怪你让我等几天,原来是为了和他说清楚!”“兄弟,我……”“什么也别说了,谁让我是黑五类崽子呢,还想高攀,瞎了眼了!”说着在自己身上猛捶几拳,一跺脚走了。陶燕婷眼前一黑,倒在炕上……
自从万东明摔了万宝昌以后,就做好挨斗的准备,可一连几天不见动静,他也不知道万宝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等着人家什么时候找来就认倒霉。他也暗暗骂了陶燕婷无数次,可每次骂过之后,又觉得她不是坏女人,这里头准有事儿,可气一上来又大骂一阵。从此他再也没登过陶燕婷的门,但一空闲下来,就远远呆望着陶燕婷那三间土坯屋,好半天儿脚不动窝。
这样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他一个本家侄子万长山来找他,说公社让一个村出两个民工去修水库,村里决定让他俩去。肚里正窝火烦闷的万东明二话没说就痛快地答应了。就在万长山转身要走的时候,万东明突然叫住万长山说:“今儿个吃了晚饭扛着大镐上我这儿来。”“干啥?”万东明瞪了他一眼说:“刚才我出去兜了一圈儿,谁家的自留地都种上麦子了,只是你婶子……”“我婶子?”万长山翻了半天白眼,想不起从哪儿又蹦出一个婶子来。“我说的是陶……”“陶”字一出口,万长山明白了,他咧嘴冲万东明一笑,答应一声走了。
当天夜里,天上只有大半个月亮,可刨地种麦还是够亮的,万东明就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样干个不停,连年轻力壮的万长山都赶他不赢。爷儿俩忙了大半夜,总算把陶燕婷的二分自留地种上了麦子。万东明蹲下来用手轻轻抚摸着整得平如镜面的土地,喃喃道:“小雨下过好几天了,不知麦子还能出来吗?”
第二天一大早,爷儿俩扛着铺盖卷上路了,当二人走到村西那座旧窑前时,万东明不禁停下脚步,望着窑门发起呆来。那天在这儿碰见陶燕婷的情景又出现在脑里。他怎么也没想到陶燕婷怎么会和万宝昌乱搞,但不知为什么,对陶燕婷他既恨不起来,也忘不了。他正在这儿发愣,忽然万长山推了他一把说:“叔,你看!”万东明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村口站着一个人正朝这儿望着,尽管距离较远,可万东明一看就认出是陶燕婷。万长山一见他俩都像石雕木刻似的一动不动,就把嘴凑到叔叔耳根上说:“叔,回去说几句话吧!”“不,咱们走!”万东明像旱天里打了一个响雷似的吼了一声,然后转过身来头也不回地走了。
工地上的生活挺简单,干活儿、吃饭、睡觉就这么三件事,唯一解闷的方法就是胡聊。清一色的男性农民到了一块儿,三句话离不开女人,凡是见到的、听到的,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每逢这种闲聊,万东明便离得远远地一个人抽闷烟。
这天晚上,万长山一觉睡醒,见万东明还坐在地铺上抽烟,就催促着:“叔,睡吧,明儿还得上工呢。”万东明还是一声不吭,万长山关切地坐了起来问:“叔,你想什么呢?”“哎……”万东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婶子自留地里的麦子长得出来吗?”万长山一听放心了:“睡吧,叔,一定长得出来。”
第二天,水库工地上人来人往,锤声、哨声、石头滚动声、人的喊叫声,响成一片。万东明、万长山和几个民工在一个陡坡上打了一组炮眼,装上火药,点上火后全退到安全处。一会儿只听“轰、轰、轰”响了三响,炮声便停了。万东明皱着眉头焦急地说:“哎,怎么少了一响?”他们正想再等一会儿。谁知一个戴着红袖章的领班走过来,朝着万东明他们吼道:“谁点的捻儿,上去看看。”“再等会儿,现在上去响了怎么办?”那个领班皮笑肉不笑地说:“咱们可是有任务数的,哪个组任务完不成,我就不给补助,扣发口粮。”那时候,哪个民工不是为了一天那几毛钱补助和那点儿口粮才离家来卖力气的,听领班这么一说,有几个人沉不住气了,朝着万长山努努嘴,示意他上去。万长山看了看万东明,慢腾腾地朝工地走去。“等一下,”万东明一把拉住了侄子,轻蔑地朝领班一笑,然后紧了紧裤带说,“我去!”“叔,我去!”万长山一步跨到叔叔身前。“你小子听着,你老的给你说门亲事不容易,年根儿就结婚了,出点儿事我可担当不起,没法向你爹妈交待,我去吧!”“叔叔,陶……婶子等着你呢。”“滚开,再不滚开,我一脚踢你到山旮旯里去!”
见叔叔发了怒,万长山退到一边,万东明迈着大步朝炮眼走去,一步,一步,他每迈一步,万长山就觉得肠子拧一个弯,在场的人全屏住了呼吸,就连那个领班的也瞪大了眼睛死盯着前方。
万东明仔仔细细地查看着,突然他发现脚下冒着浓烟,他想躲开,已来不及了,只听轰一声,那高大的身躯晃了几晃,倒下了。
“叔!”万长山呼喊着跑了过来,抱起血肉模糊的叔叔,在大伙帮助下,把他送到了工地的临时医院,经过抢救,直到下午三点多钟,万东明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吃力地睁开双眼,看见守候在身边的侄子,嘴巴嚅动了几下,硬是没有发出声来。尽管万长山怎么问,他只是呆呆地看着侄子。又过了一会儿,万东明的嘴又动了起来,万长山把耳朵凑了过来使劲儿听着、听着,他终于从那微弱的、吐字不清、断断续续发音中听清楚了,万东明说的还是那句话:“你……婶子地里的麦……子,能、能长出来……吗?”“能,叔,你放心吧……”万长山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晚上,万长山伺候叔叔喝了点儿水,吃了几块桃罐头,就靠在窗台上,不知不觉睡着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阵冷风把他从梦中惊醒,他往叔叔床上一看,啊,人不见了。万长山惊得赶紧出门去找,可找遍了工地也不见万东明的影子。最后,他从一个护士口中打听到万东明朝家乡羊尾巴村的方向走了。这可把他急出了一身冷汗,他想叔叔身负重伤哪走得了这五十多里路啊,他赶紧迈开大步朝前追去。
万长山连奔带跑,跑得大汗淋漓,腿肚子发软。这时,他借着月光看见前边不远的山路上有一个身影,正踉踉跄跄地往前走着。“叔——”万长山一下惊叫起来。他一下忘了疲劳,迈开大步边喊边追了过去。
可是任凭万长山怎么喊,万东明却根本不理,头也不回,一个劲儿地朝前走,而且越走越快,简直像飞起来一样。不管万长山怎么加速,也追不上他。追到后半夜,已来到羊尾巴村西的那座旧窑前。只见万东明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朝前走,万长山望着万东明奔到陶燕婷的自留地里“咕咚”一下摔倒了。万长山终于追上他,月光下,只见碧绿的麦苗密密匝匝、整整齐齐地钻出了地面,万东明手里攥着麦苗,一动不动。万长山哈下腰说:“叔,你放心了吧,麦苗多齐整。”
万东明没有回答,万长山突然觉得身后有人,扭头一看,啊,是陶燕婷!
陶燕婷怎么半夜三更到自留地来的呢?说来真神奇,她从昨晚上就开始心惊肉跳,说什么也镇定不下来,一夜没合上眼。躺到后半夜,不知怎的就出了家门到村西张望,见自留地里有人影,便走了过来。陶燕婷问道:“长山,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叔老是惦记着你地里的麦子。他受了伤……”万长山一五一十把前前后后的经过一说,陶燕婷听了止不住热泪盈眶,赶紧俯下身去,深情地叫着万东明:“兄弟,起来吧……东明,到家里歇歇儿。”万长山也伸出手去拉万东明,可是万东明一动不动。万长山拉了一把没拉动。陶燕婷连忙伸手摸万东明的身体,这一摸,顿时惊得大叫一声:“啊!”万长山忙用力把万东明翻了个身,陶燕婷不顾一切地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用心听着,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月光下,他的脸白得瘆人。她明白了,万东明死了。她跪在地上,双手拚命摇晃着万东明,边摇边放声大哭:“兄弟,你醒醒呀,嫂子我答应你了!你从工地上回来咱就结婚,不,结了婚再走,你说呀!”万长山也哭喊着:“叔,你睁眼看看呀,麦子长……长出来了。”可是任凭他俩哭得天崩地裂也无济于事了,万东明死了,真的死了。
忠厚老实的万东明,他惦着陶燕婷,惦着她那自留地里的麦子。他凭着最后一口气,硬是神奇般地走回村来,亲眼看见麦苗真的长出来了,他才安心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赵宇航/荐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