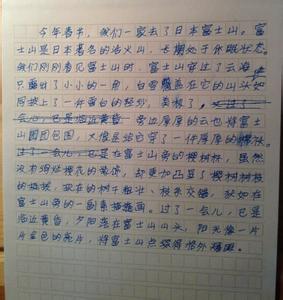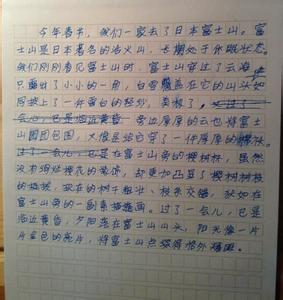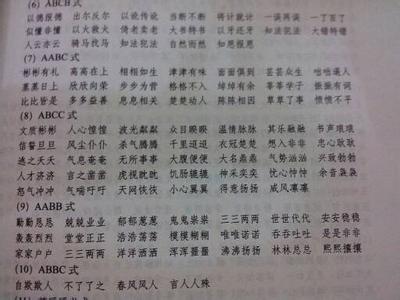(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23页)
好风:但见:扬尘播土,倒树摧林。海浪如山耸,浑波万迭侵。乾坤昏荡荡,日月暗沉沉。一阵摇松如虎啸,忽然入竹似龙吟。万窍怒号天噫气,飞砂走石乱伤人。
(吴承思:《西游记》第356页)
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驰,象惊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的乱卷,象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电线......
(老合:《骆驼祥子》第73页)
易于刮风的北平的天气,在空中,又充满着野兽哮吼的声音了。天是灰黄的,暗暗的,混沌而且航滞。所有的尘土,沙粒,以及人的和兽的干粪,都飞了起来,在没有太阳光彩的空间弥漫着。许多纸片,许多枯叶,许多积雪,许多秽坑里的小物件,彼此混合着象各种鸟类模样,飞来飞去,在各家的瓦檐上打圈。那亦裸裸的,至多只挂着一些残叶的树枝,使藤鞭似的飞舞了,又象是鞭着空气中的什么似的,在马路上一切行人都低着头,掩着脸,上身向前屁股向后地弯着腰,困难的走路。拉着人的洋车,虽然车子轮子是转动的,却好象不曾前进的样子。一切卖馒头烙饼的布篷子都不见了,只刹那些长方形的木板子和板凳歪倒在地上。并且连一只野狗也没有。汽车喇叭的声音也少极了。似乎这时并不是人类的世界。一切都是狂风的权威和尘灰的武力。
(胡也频:《到莫斯科去》 《胡也频选集》笫49—50页)
十一月初头,北风从长城外吹来,河北大平原卷起旋转的黄尘,这是结冰的季节了。夏秋两季,辽阔的田野遍是怒绿的庄稼和草木,密丛丛地遮蔽着远近的村庄。现在,庄稼倒了,草木凋零了,每个村庄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风变成没遮拦的小霸王,打着响亮的唿哨,狂放地到处奔跑,跑过荒寒无边的野地,跑过空虚的村街,无理地摇撼着人家闭紧的窗门,时时还扬起大把的沙土,撒向谁家的纸窗。风驱逐开人类,暂时霸占了这个世界。
(杨朔:《风暴》 《月黑夜》笫77页)
台风一来,秋高气爽的南国就变成一个阴阴沉沉的愁惨世界。鲜明艳丽的太阳叫横暴的雨点淋湿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风象一种恐怖的音乐,整天不停地娄着。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揪着,扭着,骂着,吵嚷不休。满天的黑云象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唤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他们慢慢去远了,把广州的光明和温暖都带定了,但从白云山后面,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追赶上来。
(欧阳山:《三家巷》第293页)
突然西北大山头上一阵怪啸的咆哮。大家一齐惊骇地向啸声望去,只见山顶上一排大树摇摇晃晃,树枝格格地截断,接着便是一股狂风卷腾起来的雪雾,象一条无比大的雪龙,狂舞在林间。它腾腾落落,右翻左展,绞头摔尾,朝小分队扑来。林缝里狂喷着雪粉,打在脸上,象石子一样……
小分队冒着象飞砂一样硬的狂风暴雪,在摔了无数的跟头以后,爬上山顶。这股穿山风,已经掠山而过。……小分队刚才路过的地带,地形已完全改变了,没了山背,也没了山沟。山沟全被雪填平了,和山背一样高,成了一片平平雪修的大广场。山沟里的树,连梢也不见了……
(曲波:《林海雪原》第292页)
这时候,暴风雪愈来愈猛,刺骨的寒风带来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寒风摇撼着树枝,狂啸怒号,发狂似地吹开整个雪堆,把它卷入空中,寒风不住呼啸,方向变化无定,几乎掀翻了雪橇和马匹,好象尖石子似的刮着骑马人的脸,叫他们透不过气来,说不出话来。缚在雪橇辕杆上的铃子全然听不见声音了,在这旋风的怒号和呼啸声中,只听得一阵阵凄苦的声音,象狼嚎,又象远处的马嘶,有时又象人们在大难之小的呼救声。
([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371—372页)
十二月的寒风,在烟筒里呼啸,放荡而狂悖,听起来象灵魂在黑友的草原里,在狂。风暴雨中,在漂泊中呼吁。
(【德】托马斯·曼:《沉重的时刻》 《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254页)
风呼啸着,在草原上奔跑,滴溜溜地乱转,刮得青草发出一片响声,闹得雷声和车轮的吱嘎声反而听不见丁。这风从黑色的雨云里刮过来,卷起滚滚的灰尘,带来雨和潮湿土地的气味。月光昏暗,仿佛变得肮脏多了似的,星星越发黯淡,可以看见滚滚的烟尘眼它的阴影顺着大道的边沿急忙跑到后面什么地方去。这时候旋风盘旋着,从地面尘土里卷走枯草和羽毛,大概升上了天空,野蓟多半在黑色的雨云旁边飞翔,它们一定多么害怕呀!可是透过迷眼的灰土,除了闪电的亮)艺以外甚么也看不见。
(【俄】契诃夫:《草原》 《契诃夫小说选》第239—240页)
……这种猛烈的热风已经刮了两天了。灰粉的尘雾,笼罩着城市,遮蔽了阳光。一团团浓密的飞沙,打街头一阵阵卷过,每次吹来,街上那疏落的行人便都背过身去。尘沙钻进所有的隙缝,穿过宙格,在窗槛上积起厚厚的一层,连人们的牙缝里,电都在沙沙作响。窗户被风吹得直摇晃,屋顶上的炔片也发出嘎嘎的响声。加以这风又热又闷,即使在屋子里,也有一股街上的味道。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姊妹》第107页)
风暴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它不但可怕,而且可惜可怖。大海的翻腾一直达到了天穹。密云到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它似乎为所欲为,它施加压力,使波涛暴怒,它自身却保持不祥的镇静。下面是发狂,上面是发怒。满天都在吹气,整个大海成了泡沫,这就是风的权力。飓风是司命的神,他被自己的凶恶弄沉醉了、糊涂了,它变成了旋风。这是盲目的在制造黑夜。有的风暴发了狂,疯疯(癫癫爬上了天穹的脑顶。天穹也张皇失措,只好暗暗的用雷鸣来回答。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这真是最凶恶的时刻。
(【法】雨果:《海上劳工》第328页)
风呢——不是在路上迎面吹过来,或者从背后吹过来——固然这已经够坏的了——却是一直横着吹过马路,把雨吹成斜的,就象人们在学校里用尺画在抄本上让孩子们照着写字的斜线似的。有的时候它会停一阵子,旅行的人不免自骗自地以为它是因为被早先的猛劲儿弄得累了,所以是安安静静地躺着去休息了,谁知道“呼”的一声,远远地”自哮着,唿哨着,冲过山冈的顶上,在平原上扫过来了,越近,劲儿和声音就越大,然后一股脑儿扑在马和人身上,把刺人的雨吹进他们的耳朵,把冷冰冰的湿气吹进他们的骨头,它由他们身边刮过去老老远了,还发着使人发昏的吼叫,象是讥笑他们的软弱,得意自己的威力。
(【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215页)
风一整天都从南方猛烈地刮来,然而,并没有带来一滴雨。随着夜晚的来临,风非但没减弱,反而刮得更猛,咆哮得更厉害:树一个劲儿地给往一边吹倒,根本不扭过来,一个小时里几乎一次也没把树枝转回过来,这股猛劲儿持续不断,把它们多枝的头按向北方——云被从这一极吹向那一极,一大块迅速地紧接着一大块,在那—七月的一天,连一点蓝色的天空都看不见。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361页)
风的音调,有一部分,十分特别,只能在这儿听到,不能在任何别的地方上听到。连串无数的狂飚,一阵一阵从西北方一个跟着一个吹来,它们之中的每一阵在飞奔而过的时候,都在进行的过程中把声音分化成了三种。低音、中音和最高音都能在里面听出来。全体的风势,掠过坑谷,扑过冈峦,就是和鸣的众钟里那个最沉浊的声音。第二种能听出来的,是冬青树飒飒作响的半低音。还有一种,比这两种力量小而调门高,听起来象是老年人变细变弱了的嗓子而却强作粗音哑音的情形,刚才说过的那种本地特殊的声音,就是这一种。它比超前而那两种来,虽然更细弱,虽然更难以立刻就找到它的来源,但是它给人的印象却更强烈。
(【英】哈代:《还乡》笫71页)
忽然狂风大作,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丫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23页)
好风:但见:扬尘播土,倒树摧林。海浪如山耸,浑波万迭侵。乾坤昏荡荡,日月暗沉沉。一阵摇松如虎啸,忽然入竹似龙吟。万窍怒号天噫气,飞砂走石乱伤人。
(吴承思:《西游记》第356页)
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驰,象惊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的乱卷,象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电线......
(老合:《骆驼祥子》第73页)
易于刮风的北平的天气,在空中,又充满着野兽哮吼的声音了。天是灰黄的,暗暗的,混沌而且航滞。所有的尘土,沙粒,以及人的和兽的干粪,都飞了起来,在没有太阳光彩的空间弥漫着。许多纸片,许多枯叶,许多积雪,许多秽坑里的小物件,彼此混合着象各种鸟类模样,飞来飞去,在各家的瓦檐上打圈。那亦裸裸的,至多只挂着一些残叶的树枝,使藤鞭似的飞舞了,又象是鞭着空气中的什么似的,在马路上一切行人都低着头,掩着脸,上身向前屁股向后地弯着腰,困难的走路。拉着人的洋车,虽然车子轮子是转动的,却好象不曾前进的样子。一切卖馒头烙饼的布篷子都不见了,只刹那些长方形的木板子和板凳歪倒在地上。并且连一只野狗也没有。汽车喇叭的声音也少极了。似乎这时并不是人类的世界。一切都是狂风的权威和尘灰的武力。

(胡也频:《到莫斯科去》 《胡也频选集》笫49—50页)
十一月初头,北风从长城外吹来,河北大平原卷起旋转的黄尘,这是结冰的季节了。夏秋两季,辽阔的田野遍是怒绿的庄稼和草木,密丛丛地遮蔽着远近的村庄。现在,庄稼倒了,草木凋零了,每个村庄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风变成没遮拦的小霸王,打着响亮的唿哨,狂放地到处奔跑,跑过荒寒无边的野地,跑过空虚的村街,无理地摇撼着人家闭紧的窗门,时时还扬起大把的沙土,撒向谁家的纸窗。风驱逐开人类,暂时霸占了这个世界。
(杨朔:《风暴》 《月黑夜》笫77页)
台风一来,秋高气爽的南国就变成一个阴阴沉沉的愁惨世界。鲜明艳丽的太阳叫横暴的雨点淋湿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风象一种恐怖的音乐,整天不停地娄着。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揪着,扭着,骂着,吵嚷不休。满天的黑云象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唤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他们慢慢去远了,把广州的光明和温暖都带定了,但从白云山后面,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追赶上来。
(欧阳山:《三家巷》第293页)
突然西北大山头上一阵怪啸的咆哮。大家一齐惊骇地向啸声望去,只见山顶上一排大树摇摇晃晃,树枝格格地截断,接着便是一股狂风卷腾起来的雪雾,象一条无比大的雪龙,狂舞在林间。它腾腾落落,右翻左展,绞头摔尾,朝小分队扑来。林缝里狂喷着雪粉,打在脸上,象石子一样……
小分队冒着象飞砂一样硬的狂风暴雪,在摔了无数的跟头以后,爬上山顶。这股穿山风,已经掠山而过。……小分队刚才路过的地带,地形已完全改变了,没了山背,也没了山沟。山沟全被雪填平了,和山背一样高,成了一片平平雪修的大广场。山沟里的树,连梢也不见了…… (曲波:《林海雪原》第292页)
这时候,暴风雪愈来愈猛,刺骨的寒风带来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寒风摇撼着树枝,狂啸怒号,发狂似地吹开整个雪堆,把它卷入空中,寒风不住呼啸,方向变化无定,几乎掀翻了雪橇和马匹,好象尖石子似的刮着骑马人的脸,叫他们透不过气来,说不出话来。缚在雪橇辕杆上的铃子全然听不见声音了,在这旋风的怒号和呼啸声中,只听得一阵阵凄苦的声音,象狼嚎,又象远处的马嘶,有时又象人们在大难之小的呼救声。
(【波】显克微支:《十字军骑士》第371—372页)
十二月的寒风,在烟筒里呼啸,放荡而狂悖,听起来象灵魂在黑友的草原里,在狂。风暴雨中,在漂泊中呼吁。
([德)托马斯·曼:《沉重的时刻》 《外国短篇小说》上册第254页)
风呼啸着,在草原上奔跑,滴溜溜地乱转,刮得青草发出一片响声,闹得雷声和车轮的吱嘎声反而听不见丁。这风从黑色的雨云里刮过来,卷起滚滚的灰尘,带来雨和潮湿土地的气味。月光昏暗,仿佛变得肮脏多了似的,星星越发黯淡,可以看见滚滚的烟尘眼它的阴影顺着大道的边沿急忙跑到后面什么地方去。这时候旋风盘旋着,从地面尘土里卷走枯草和羽毛,大概升上了天空,野蓟多半在黑色的雨云旁边飞翔,它们一定多么害怕呀!可是透过迷眼的灰土,除了闪电的亮)艺以外甚么也看不见。
(【俄】契诃夫:《草原》 《契诃夫小说选》第239—240页)
……这种猛烈的热风已经刮了两天了。灰粉的尘雾,笼罩着城市,遮蔽了阳光。一团团浓密的飞沙,打街头一阵阵卷过,每次吹来,街上那疏落的行人便都背过身去。尘沙钻进所有的隙缝,穿过宙格,在窗槛上积起厚厚的一层,连人们的牙缝里,电都在沙沙作响。窗户被风吹得直摇晃,屋顶上的炔片也发出嘎嘎的响声。加以这风又热又闷,即使在屋子里,也有一股街上的味道。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姊妹》第107页)
风暴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它不但可怕,而且可惜可怖。大海的翻腾一直达到了天穹。密云到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它似乎为所欲为,它施加压力,使波涛暴怒,它自身却保持不祥的镇静。下面是发狂,上面是发怒。满天都在吹气,整个大海成了泡沫,这就是风的权力。飓风是司命的神,他被自己的凶恶弄沉醉了、糊涂了,它变成了旋风。这是盲目的在制造黑夜。有的风暴发了狂,疯疯(癫癫爬上了天穹的脑顶。天穹也张皇失措,只好暗暗的用雷鸣来回答。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了。这真是最凶恶的时刻。
(【法】雨果:《海上劳工》第328页)
风呢——不是在路上迎面吹过来,或者从背后吹过来——固然这已经够坏的了——却是一直横着吹过马路,把雨吹成斜的,就象人们在学校里用尺画在抄本上让孩子们照着写字的斜线似的。有的时候它会停一阵子,旅行的人不免自骗自地以为它是因为被早先的猛劲儿弄得累了,所以是安安静静地躺着去休息了,谁知道“呼”的一声,远远地”自哮着,唿哨着,冲过山冈的顶上,在平原上扫过来了,越近,劲儿和声音就越大,然后一股脑儿扑在马和人身上,把刺人的雨吹进他们的耳朵,把冷冰冰的湿气吹进他们的骨头,它由他们身边刮过去老老远了,还发着使人发昏的吼叫,象是讥笑他们的软弱,得意自己的威力。
(【英】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第215页)
风一整天都从南方猛烈地刮来,然而,并没有带来一滴雨。随着夜晚的来临,风非但没减弱,反而刮得更猛,咆哮得更厉害:树一个劲儿地给往一边吹倒,根本不扭过来,一个小时里几乎一次也没把树枝转回过来,这股猛劲儿持续不断,把它们多枝的头按向北方——云被从这一极吹向那一极,一大块迅速地紧接着一大块,在那—七月的一天,连一点蓝色的天空都看不见。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第361页)
风的音调,有一部分,十分特别,只能在这儿听到,不能在任何别的地方上听到。连串无数的狂飚,一阵一阵从西北方一个跟着一个吹来,它们之中的每一阵在飞奔而过的时候,都在进行的过程中把声音分化成了三种。低音、中音和最高音都能在里面听出来。全体的风势,掠过坑谷,扑过冈峦,就是和鸣的众钟里那个最沉浊的声音。第二种能听出来的,是冬青树飒飒作响的半低音。还有一种,比这两种力量小而调门高,听起来象是老年人变细变弱了的嗓子而却强作粗音哑音的情形,刚才说过的那种本地特殊的声音,就是这一种。它比超前而那两种来,虽然更细弱,虽然更难以立刻就找到它的来源,但是它给人的印象却更强烈。
(【英】哈代:《还乡》笫71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