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城里跌了一跤,他不得不回家来了。
他跌跤的原因是有人骗他说,他妻子跟人跑了。他追赶这个说谎的人时翻越楼梯扶手,不小心把脚给崴了,幸好他跑得不快,否则可能终身残疾。这是五月初的事。事发当日,他就被人送回来了。
到镇医院拍片子,医生说一切正常,可他不信,脚在自己身上长着呢,一入夜就钻心地疼。他把这感受如实说了,医生摆摆手,说过几天就没事,还要他“相信科学”。这真是瞎扯淡,他当时就生气了,扯着嗓子吼:“你他妈的,讲什么科学?”吼完就再不理人了。是他的妻子替他圆的场:“他从小就这样,脾气暴。您多见谅。”医生来了个西式耸肩:“没什么,没什么。他为什么脚疼,片子上确实反映不出来。”碰上这么个谦虚的医生,活该他倒霉。
第二天,他的脚开始浮肿,很快,连地也没法下了,这时全家人都急起来。妻子劝他再去别的医院看看,他眯起眼睛,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母亲也来数落他,说他前几年走的路太多,天南海北地跑,成年累月不回家,这是报应来了;他觉得母亲老糊涂了,因为他确实是她的儿子呀。
这个夏天,他一直在堂屋里躺着。屋前有两棵壶瓶枣树,还是父亲在世的时候种的。那时他的年龄太小了,根本没有父亲种树的记忆。关于这件事,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现在,浓阴遮挡了烈日,他的头顶上,像贴满了薄荷叶似的。除了脚疼,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他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说:“你干脆住在外面算了。”他可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不但母亲误解,妻子偶尔也埋怨:“你走了,留下我们俩,在家里受苦。”母亲的嗓门大,但妻子说话的声音异常轻微,如果不仔细听,根本不知道她在说话。他相信她的话出自真心。
父亲死了以后,只留下了这么几孔破窑洞。他结婚那年,本来还想着翻修一下,可一时凑不起钱来,只好作罢。就这么一拖,又是三年过去了。有时在屋子里坐着,会看到白色的灰尘无声无息地落下,时间久了,地上能积薄薄的一层。他问过妻子,得到的答案是,那是你父亲的灵魂。每逢这时,母亲就在旁边大声说:“他已经走远了。你们别再把他招回来。”
他突然想问问父亲是怎么走的,可屋子里很静,母亲出去喂鸡了。
妻子说:“你应该把这几年赚的钱拿出来,这房子再这么住下去,会出事的。”
这话初听很不入耳,后来,却觉得她说得对。他示意她扶他起来。
“还疼吗?”
“有一点点。”
“按说,肿该消了。我照医书采的草药,应该不会错。”
“感觉确实好多了。我以前不知道你还会这一手。”
“你别忘了,我是从崖上来的。再说了,我家祖辈行医,打小我耳濡目染,自然懂点儿。”
“看来,你比镇上那个医生强。”
母亲睡着以后,屋子里静极了。妻子去邻居家串门回来,一进屋就说:“吓死我了。”他已经在黑暗里待了一个多小时,此刻依然没有出声。刚才,屋子里的钟表“嘀答”响着,他点点滴滴地想起往事。可她一出现,不只钟表的响动停止了,就是他的回想,也迅速地短了路。她拉开灯以后,奇怪地看着他。他眯缝着眼睛,像是昏睡未醒。她蹑手蹑脚地洗脸、洗脚、刷牙,他突然开腔,又吓了她一跳。
“我不在家的时候,你想我了吗?”“什么,你说什么?”
“你走神了吧?我刚才又没有捏着鼻子说话。”她默默地上了炕,默默地脱衣服。这阵子钟表的“嘀答”声又响起来了。
“这些天,我在炕上躺着,想了很多事。”
“你不用想,什么事都没有。”
不一会儿,他的耳边,就响起了轻微的鼾声。这声音细如发丝,可还是把他吵着了。他动了一下身子。
“又疼了吗?”
“没有。”
“那赶紧睡吧,天已经很晚了。”
“我睡不着。你同我说说吧,我离开的时候,你会不会想我?”
她翻身坐起,看了他一眼,然后伸手摸他的额头。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抓得很紧。都说她的手很白,皮肤很细,他觉得这话对极了。她的手果真像绸缎似的。他的动作,加上他眼睛中的焦灼,使她很快出汗了。她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如果你非要我说,我也没办法,可是,你为什么总在问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这不是无关紧要,它关系大着呢。”
“可是,你回来都这么多天了。”
三年前,她刚嫁过来的时候,才十九岁。如果不是父亲突然病故,她本来准备读大学的,可是老天的安排大异于她的想象。起初她想跟命运对着干,可紧接着母亲也舍她而去,她被吓怕了,于是干脆利落地向生活缴了械。她的选择马上赢得了一片赞誉。原因很简单,他那时刚当上村长。
可结婚不到半年,他就在一次海选中落了马。她一直记得那天晚上。
“我被他们抛弃了……以前我觉得蛮有把握呢,一直以来,我们相处得都很好。他们有没有和你谈论我?”
“没有,从来没有。”
“说谎。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事实确如他的想象,但她必须这样说。
“那一夜,他缩在我的怀里,像个婴儿,我能感觉到他冷得发抖。我全身的热量都没有办法使他恢复过来。就在这时,婆婆推开了我们的门,她是来安慰他的。可是月光下,他的脸色突然变白。后来,我们就像掉进泥浆里,两个人都湿漉漉的……我想退回原地,可怎么都不行。他的精力也大不如前,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岁。”
她再一次顺从了命运。
他离开得很仓促,只带了副被褥就走了。事后她收拾家里的细软,发现他竟然没拿走一分钱。这似乎也不可能,但至少她看到的事实是这样的。
他走了的第二天,婆婆从东屋来到他们住的屋子。
“你做错了一件事。”
她睁大茫然的眼睛看着她。
“以前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离开的。没想到,他的儿子又走了他的老路。”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
“你怎么这样同我说话?是不是觉得他一走,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没这么想。”
“媳妇,你别心口不一。”
“妈,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心口堵得厉害。后来,她就离开了屋子,站到了院子里的壶瓶枣树下。阳光渗漏似的从树叶间射下来。她闭紧双眼,似有微风拂过,她觉得脸颊上有了一阵阵凉意。
“我早已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现在,又来到了这里,受这种罪。”
“父母活着的时候,我整天无忧无虑,可人死如灯灭……我连他们的面容也快忘记了。”
“都说他们不是短寿的人,可为什么像一阵风似的,转眼就不见了?”
这一整天,她都没有回屋,没有做饭,也没有吃饭。婆婆像是跟她赌气似的,再也没有跟她说一句话。天色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暗下来的,很快,夜幕就把大地罩得严严实实。她又在院子里站了半天。进屋的时候,她翻来覆去地想着这句话:
“总之,她不是我亲妈妈。”
晚上她自己煮面条吃了。临睡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一天里,有好多事她都没做。
夜里她睡得很不踏实。
后半夜又下起雨来。闪电照亮了窗口,她有些害怕了。她试着喊了两声“妈”,过了十几秒钟,传来一声咆哮:“喊魂哪!”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抖动起来,屋子里也有些凉了。
“我就这样一直盯着窗口。雷声和雨点都很大。可就在这种时候,我发现一个人影透过天光进了屋子,开始时以为是你回来了,过了很久才知道是幻觉;可明明知道是幻觉,却不由得去看、去想。那个人影在屋子里徘徊了很长时间,一会儿在四面墙上,一会儿又跑到屋顶,最让我难以忍受的一次,他居然跑到我的床上来了。我拿笤帚使劲赶他,又大声喊叫才把他吓跑。妈在东屋听到了我的声音,她过来了,一进门就问:‘你是在成心扰我吧?’但她还是在这边睡下了。过了不到五分钟,她就打起鼾来。雨一直下到天亮才停。雨一停,妈就走了。”
她醒过来的时候是正午,院子里的鸡在“咯咯”叫着,婆婆正在喂食。看见她站在门口,大声喊她过去帮忙:“别像个傻子似的站着,我手上还有其他活儿呢。”有一只鸡看见她手上的玉米,就跳起来啄食。她在地上轻轻撒开,然后动手把那只恃强凌弱的鸡赶走。鸡被她赶上了枣树,树枝颤了一下,紧跟着就“噼里啪啦”滚下一阵雨珠。
婆婆说:“又没事做了吧?去把掉到地上的枣子捡起来吧。”
“你离开好多天后,家里终于有人来了。他们是来探听消息的,全身上下都长满了好奇心。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说是你在外面搞上了女人。这话说的次数多了,我就将信将疑起来。但妈说:‘不用担心我的儿子,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我一想,她准是对我不满意了。妈还说:‘这些嚼舌根的人,既管不住自己的嘴,又管不住自己的身子,你不要理他们。’”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好像睡着了,这真是件怪事,因为是他首先提到了这个茬。于是,她穿衣服起来,在地上走了走。然后她突然动念,想翻一翻他带回来的东西,但又怕他突然醒来。正在犹豫的时候,她听到外面的公鸡叫了。她侧耳听了一会儿,直到外面复归寂静。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婆婆的房门开了。她试着推了推丈夫。
“你听。”
他半睁着眼睛看了她半天,像是奇怪她为什么会站在地上。
“我夜里肚子疼,出去上厕所。”
“你不要骗我了。”
“你没有睡着?”
“每天夜里,我只睡两三个小时。”
“这样下去可不行,你身体会垮掉的。”
“先不说这件事。我回来这些天,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
“你就是有秘密对不对?老实说,你心里还装着什么人?”
“你不用胡思乱想,这根本不可能。”
说了一会儿话,他气咻咻地起床了。费了半天劲,终于把上衣穿上身。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对妻子说:
“我从外面寄回来的那些钱,现在还剩多少?”她愣了一下,头也不抬,“我不知道,钱都在妈手里,说是给孙子攒着。”
“哼,还提孙子,八字都没一撇呢。”
她没有接腔,端着吃剩的饭菜走了出去。
他不可能向母亲追问那些钱的下落。自从父亲去世后,母子俩的生活一度难以为继,母亲想尽各种办法,使他不仅没有饿死,而且很好地活了下来;但父亲离开的日子太久了,所以其实这些事,早已充斥了他的全部记忆。
一群麻雀飞上了枣树,“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他看着外面妻子的背影,忽然涌上来一种不明所以的情感。他把盖在腿上的毛毯掀开来,发现脚上的浮肿开始消退了。
“妈,你过这边来一下。”
母亲很快过来了。
“妈,我的脚好多了,再过几天,就和她把事情挑明了吧?”
“胡说。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家了?”
“这样拖着,总不是个办法。”
“儿子,你太年轻了,等到了妈这个岁数,再说这种话吧。”
他抬起头来,透过窗口,看见空中一大片浮云远远地飘来。可阳光亮得刺眼,他忙把头低了下来。
“你刚才和妈在说我吗?”
“没有。我脚上的肿散开了。”
“看来是药物起作用了。这样的话,再过些日子,你就能出门了。”
他懒懒地靠在被褥上,她坐在炕沿上做针线。直到黑暗再度降临,村子里的灯一盏盏地亮起来。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有人来找过你吗?”
“我过去的几个老同学来了。她们最近都嫁人了。”
说到“嫁人”这件事的时候,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轻轻地叹了口气。
“你怎么了?”
“你该给我手里留点钱。要不你一走,我连人情往来的事都该免了。”
“放心,我以后不走了。”
她木呆呆地坐着,看不出她在想什么。大约沉默了半小时后,她站起身来,出了屋。他听着她的脚步声慢慢走远了,不知道她去做什么了。他奇怪自己为什么不问一问她。
十分钟后,她端着一只装满了绿豆的塑料碗进了门。他发现她的身上有一种母牛的气息。
“吓死我了。”她喘着粗气说。
“村里最近来了几个外地人,一到黑夜就打着手电筒四处疯跑。刚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站在老槐树下,学鬼叫吓人。”
“那你黑天半夜出去干什么?天亮的时间那么长,有多少要紧的事非得夜里去干?”她闻到了他话里的火药味。
“可天不是刚黑吗?牛首崖下种地的人,这会儿刚进村。”
“那是因为路远。你又不用种地。”
“你的意思是,光坐在家里,就可以把日子过下去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她忽然意识到什么似的,闭口不言。可他还在喋喋不休。
“这么说,你开始嫌弃我了?你是不是早想说这句话了?其实,我这样在家里躺着有什么好?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连个女人都比不上?”
“我可没这么说。”
“那你这样想了。”
她不说话,开始拣绿豆里的沙子,可她的脑子却没有片刻停顿。她不仅想起了他们刚结婚时的情景,而且想了他回来后的这段日子。想到后来,她的头就疼起来。她在凳子上坐了会儿,然后把绿豆洗干净了,倒到锅里,又放上水和米,开始做晚饭。
村子里突然喧闹起来。有人放鞭炮和焰火,暗夜里升起一片片红光。
“最近有什么喜事吗?”
“我也说不清楚。你不在的那些日子,隔三差五的,总会放放鞭炮。这段时间已经少多了。”
“就没人管一管吗?”
“我很少出门。你问问妈,妈常出去,兴许知道点情况。”
“我不知道,你不要背后瞎说,我出门做什么?家里这么大,还不够我生活吗?”
她忽然有些气馁,放下手里的活,就到院里去了。天上有流星划过,村子里早睡的人家,灯光已经灭了。进屋的时候,她听到婆婆还在嘀咕。
“你出去了一趟,心早都野了,哪知道你这个媳妇多难伺候。”
“在不知情的人看来,倒像是我在欺负她。”
“我不是责怪你,可你总得为妈想想。妈已经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这顿饭吃得没滋没味。放下碗筷的时候,她决定上牛首崖去看看。
她是从牛首崖上嫁过来的。父母没了,差不多就等于娘家人都没了,这三年来,她几乎没有回去过。但到了这一天,她竟然鬼使神差地跑回来了。
好在路程并不远,往返一趟,也就是打个盹的工夫。
牛首崖是很古的时候就形成的一处断崖。崖上是一座绵延数百里的大山,山上长满了中草药。从爷爷那一辈往前数,足足有几十代人,都在崖上采药为生。后来有一部分人因迷恋崖下的耕地,才渐渐分流出去。等到崖下的村子渐渐成了规模,崖上的人烟就愈见稀少。到她父亲那辈时,往常住民密集的牛首崖上,就只剩了二十来户人家。这些人零零落落地占据着面积数倍于崖下的大村子,人口却不及崖下的五分之一。
再往后,牛首崖就成了一道分界线。两个盘根错节鸡犬相闻的村子,却住着活法不同的两类人。崖下的人慢慢都走出去了,崖上的人还固守着以前的日子,仍以采药为生。
一开始的时候,她确实想的是回去看看就离开,娘家的房子虽然还留着,可是人去房空,院子里早都杂草丛生,房门也破败了;谁料想,她却住了那么长时间。直到夏季快结束的时候,接她的人都没有来。
她把院子里的杂草一点一点清除,有一些草根已经扎得很深了,她双手使劲都拔不出来,有一天,就来了几个帮忙的人。他们不仅把草除掉了,还把残破的院墙修补了一番。院里有间耳房,也被拆掉了,匀出来的砖就铺到了院子里。有个人还帮她卖了部分旧砖,换了些石头运来。
月光如水的夜晚,她站在屋檐下,能听到许多人在外面走来走去。
刚回来那几天,她确实累坏了,一到夜晚倒头就睡;那几天睡眠质量也高。从第二周开始,情况变了。她常常睡至半夜醒来,有时看到父亲在屋子里,有时是母亲,还有的时候,是他们俩都回来了。他们看起来对她的生活了若指掌,可是,他们现在什么都管不了。她可不想让他们再操什么心了。
在家里住了半个月的时候,院子里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好几年不见的邻居都跑来了。他们惊奇地看着这所院子的变化,争着向她说起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当然,这其中有一些人,更加关心她的个人私事。有些话,他们当面会说;还有些话,则是私下议论的,再经由别人的口反馈给她。
“听人说,你家男人出事了?”
她含义不明地瞅了说话的人一眼,这个人也正在看着她,像是猜测她心里在想什么。
她没有回答,而是沿着刚砌好的砖石路走出了院子。这一来,那些还在原地逗留的人只好尴尬地散去了。
后来,就只有帮工的几个人定时来家。她十分过意不去,一直在想着该怎么报答他们。
父母倒是留了点家底给她,但几年下来,早被她用光了。现在,除了这所院子,她差不多是个一无所有的人了。
可这一天,这些人仿佛约好了似的跟她说:
“你不用发愁,我们帮你,也不图几个钱。”
她看见他们中某个人的脸上泛出希望的光来。这是个阴沉沉的下午,有几只长着红色羽毛的鸟儿落在了院子里的香椿树上,她的心被它们叫得乱起来。送走了这些人,天边的最后一线光也被夜色吞没了。空气中泛滥着驴马归圈前长长的嘶鸣。
到了夜深的时分,她开始发起烧来。
她就睡在父母曾经睡过的那张炕上,他们在这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都苏醒过来,仿佛是,他们携手到地下走了一遭儿,而阎王却把他们再度遣送到人间去。她感觉到母亲冰凉的手在摸她的额头,而父亲充满善意的眼神却若即若离地看着她。
她不只觉得自己躺在他们睡过的炕上,她还觉得他们都在她的身边躺着。好像有灯光,但太晃眼了。父亲坐起身来,替她挡着那光线。
“你离开那男人时间太久了,孩子。”
她使劲推了父亲一把。父亲像影子一般离开了。
父亲不是没来得及参加自己的婚礼吗?
她的头又开始疼起来,眼前有金星闪烁。
她在床上躺了一上午。那些帮工的人走进来,看见她病怏怏的样子,十分意外。他们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就都走了。临出门的时候,那个人还恋恋不舍地看了她半天。
“要不要我帮你做点吃的?”
她很感激地看了这个人一眼,笑着摇了摇头。
“我就是发烧,再睡会儿就好了。”
“你如果感到难受,躺着是舒服点儿。”
这个细声细气的男人最后也走了。
宁静的上午确实使人昏昏欲睡,整个世界,连一丝风都没有。是狗叫声把她吵醒了。她从炕上爬起来的时候,浑身软绵绵的,但身上的烧已经退了。
有个年老的女人带着暖洋洋的阳光进了门。这人衣服的下摆处亮晶晶的。
“我常年就说合这事,其实也就是搭伙过日子,你只要点个头,随你过去或他过来都行。”
她没有请来人坐的意思,这个人很识趣地站着。
“这不可能,我男人还等着我呢。”
“闺女,我明白你的心思,我也是从你这个岁数过来的。不过,听我一句劝,你就别傻等了。你男人的底细,我调查清楚了,他可不是个老实人。”
她站在地上整了整衣襟,然后抓起笤帚,想把地上的灰尘扫一扫。
“这个人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她好像已经看透了我的一生。我可不能在这种人面前服软。”
“你说你整年就做这种事?没人会找你的霉头吗?”
“怎么会?我一辈子都在积德行善。你可能还不知道,你的父母就是我撮合的。你母亲的前半生,也像你现在这么不幸,后来通过我,才认识了你父亲。可惜你母亲不守妇道,把你父亲气死了,结果自己也没落个好。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你怎么能胡说八道?我父母的亡魂都看着你呢。要不是看你年龄大了,我真该拿笤帚把你打出去。”
她忽然觉得心慌意乱,白天的阳光似乎全部消散;紧接着,是有些东西越来越轻,直至最后,它们都和空气一样,悄悄地溜掉了。
那个人提着东西进门的时候,她刚刚吃过了晚饭。
“我来的时候,一直想你在做什么,我猜得没错,你连碗都没来得及洗呢。我来帮你干活吧。”
“夜里来家,邻居会说闲话的。”
“我以后一定注意。”
坐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听他们说他的腿已经废了。”
她忽然生起气来。
“不管你的事。”
“怎么不管我的事?说起来,我等你都整三年了,可你一点儿也没有体察到我的心思。”
“你这个人太奇怪了,三年前我就嫁人了……”
“是啊,我正是你出嫁那天认识你的,当时我就预感你跟他的婚姻不长久。”
“你别在这儿胡扯。”
“我不是胡扯,我打听过你们的生辰八字,还找人算过了,你跟他根本不合适。跟我才是天生的一对。”
“一派胡言。”
“看来你确实年轻。但是那个男人到底爱不爱你,你早该知道了吧?”
“这与你又有什么关系?”
“哎,我本来不想打击你的,但现在还是说实话吧,你男人早都有相好的了……”
“你这样说,会遭报应的。”
“如不信,明天你就回家看看。”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你是不是早都盘算这件事了?”
“当然。”
“那些做工的人,也是你找来的?”
“是的。”
接着是一片寂静。
“如果我的父母还活着,这个人不敢这么无礼。可他们为什么早早儿都走了,留下我孤零零地待在这个世界上,受这个人的欺侮。”
“如果你心里不乐意,我不会强迫你的,反正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
“你别做白日梦了。”
“不,我相信我的诚意会打动你的。三年来,我学会了木工和泥水活,跟了我,保你一辈子衣食无忧。”“你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走吧。”
“我还会来的。”
这个细声细气的男人刚刚离开,她就嚎啕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她忽然觉得自己的哭声会招来更大的不幸,然后就硬生生地停止了。
睡到后半夜的时候,她开始有窒息感,像是有人掐住了她的脖子。她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失败,最后干脆放弃了反抗。她已经喘不过气来。
似乎有人在使劲扇另外一个人的脸,有人在旁边“噼里啪啦”地拍巴掌。她想看看这些恶毒的人是谁,可就是睁不开眼。她的双眼也被蒙上了。
她想喊,可嘴里发不出声,腮帮子鼓得老高,窒息感又加重了。
她觉得自己身上不着寸缕,而且有尖利的锋刃抵着自己的咽喉。恐惧一丝丝地袭来,转眼间就覆盖了她的全部身心。然后,就有一股尿意喷薄而出。她的身子慢慢酥软下来。
她从梦魇中惊醒的时候,摸了摸冷汗淋漓的额头。
她浑身上下,早被汗水浸透了。
曙光初降,门外传来敲门声。
男人进门的时候一直在嘀咕:
“你的反应太慢了,怎么会睡那么沉?”
好长时间未见,男人的脚看起来已无大碍。可她忽然醒悟过来,就转身去推他。男人猝不及防,被她推了个趔趄。他被她的举动搞糊涂了。
“你怎么了?”
“那个人是谁?”
“你说什么?”
她又不想说话了,脑子里生出一个好大的结。他尾随着她往里走,脚步一高一低。
“你准备在这里长住吗?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拿起一根木棍,挥手朝远处一扔。有几只停在墙头的鸽子被惊起,它们扇动翅膀的时候带起一缕尘土。
走到屋檐下时,他忽然惊奇地回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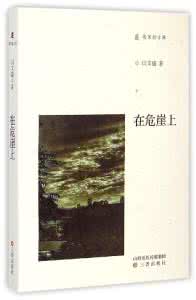
“我早都感觉不对了,原来根子在这里。”
“你还想说什么,都一古脑儿说出来吧。”
“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到你从崖上摔下去了。”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你就是来告诉我这些吗?”
“不,妈生病了。”
她这才看到他的眼睛里满是哀伤。
“你怎么到现在才说?”
他没有吭声,而是惊奇地看着她的眼睛。
“有人欺负你吗?”
她开始惊觉,转身,动作之迅捷,有如脱兔。
“原来我的眼睑上留了一道细细的疤痕,这一定是昨晚那场搏斗的痕迹。可整个黑夜都像一场梦,梦醒了,一切阴翳都该消散了,它怎么就留下了这么一道疤痕?”
她仔细地在上面涂抹了半天,然后回头问他:“这下好了吧?”
“好了。现在你该告诉我事情的原委了吧。”
“没什么,我最近总是噩梦缠身。”
“我来得太晚了。妈病了好些日子,我脱不开身。”
“这几天好些了?”
“不,情况恶化了。”
锁门的时候,她突然看见街角有个人影一闪。她浑若无事地走过街头,她的男人一瘸一瘸地跟在身后。见许多人都在看,他有些愤怒起来。
“真他妈一群蠢货。”
“你不要回头,不要理他们。”
“人走霉运,喝凉水都倒牙。我他妈的,真是丢尽了脸。”
“别想那么多了。”
“唉,我真是废了。”
他一路啰嗦着,走一会儿就累了。他们共歇了三回,都是她在等他。可他总想走到前头去。
“他希望我慢点儿,可我总注意不到这点。”
快到家的时候,她终于让他抢了先,因为她有点害怕起来。路上,她一直在回忆着;她总是听不到他的抱怨,也不排除这个因素。
“这就是我选择的日子,它似乎长得没有尽头。”
进屋的时候,她听到婆婆的叹气声。
“你如果累了,就先过去睡会儿。”
“不,我不累。”
她再次看到了婆婆的面孔。也就是半个夏天的光景,她突然衰老了许多。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你家里好像有很多事?”“也没什么要紧的。”
“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说错了话,或者做错了什么事?”
“不,妈。是因为父母走的时间长了,院子太旧了,我把它修整了一下。”
“我这次生病,可能是大限到了。现在,只有一件事让我放心不下。”
“妈,你没事的。”
“你太年轻,什么都不懂。但在这件事上,你一定要听我的。”
“……”
“你不同意?”
“妈,你说吧。”
“媳妇,你别装傻,你应该明明白白。”
她有些难堪地站着。
“这件事不能怨我,但她总爱把责任归结到我的头上。这三年来,在同样的问题上,我已经受够了她的冷嘲热讽。”
“妈说什么,你答应下来就是。她这次的情况确实不太好,已经连续一个星期了,每天只喝一点稀粥。我真害怕……”
“尽管一切都是假的,但我似乎无路可走。”
“好吧,以后我就顺着她的性子。”
“我对不起你,你又该怪我了。”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一直是你多心。”
她的目光一直在搜寻,他追赶着她的脚步。院子里像是起了浓雾。
“你在找什么?”
“我看看家里是不是被你弄脏了。”
“你发现了什么?”
“时间真快,枣子熟了。”
他每天都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她看得烦了,说他几句,他就停一会儿。但过不了十分钟,他又坐不住了。
“再不锻炼锻炼,我就彻底完蛋了。”
“你这样做,跟自我折磨差不多。你能不能多消停会儿?”
“好吧,我不走了。”
他和她都在壶瓶枣树下坐着。枣子被打下来后,树上的叶子也一天天地往下掉,很快,整个院子都显出了一片萧索。他的面部经常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却翻江倒海。
“他总是忘不了过去的事,这对我们将来的生活,一点儿好处都没有。”
“你能不能说几句话,每天这样,都快把我憋死了。”
“好吧,我刚才想问问你,除了这儿,你是不是还有地方可去?我的意思是……”
“这句话,你不是刚想起的吧?它在你的肚子里,一定藏了好久。”
“你不要打岔。”
“你的心眼太小了,跟你妈一样。”
“这跟我妈可没什么关系。再说,她的日子不好过,你不要背后说她。”
“我觉得婆婆的病不妨事了,你没有注意到她的饭量已经恢复了吗?她的脸色也不错。”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妈说话的底气又足了。这些日子全亏了你。”
两个人身前不远处,突然掉下一堆鸟屎。浓烈的光线渐渐淡下去了。
“跟你商量件事。”
“说吧。”
“我想把父母留下的房子卖掉,反正,以后我也不准备回去了。”
“前些日子,你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不,父母已经离我而去,他们保佑不了我,留着一所空院子,还有什么意义?”
“可是……”
“你有什么顾虑吗?”
“我其实在想,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了跟我过一辈子?”
她不再说话,而是把目光落在了眼前的空地上。秋风萧瑟,从枝叶间“飕飕”地刮过去了。
“回去吧,天冷了。”
她躺下来了。天上的星星好亮。
“不过半年光景,他像是变了个人。”
整夜无梦。一切似乎都消逝了,她的生命空空。第二天,她就着手卖房子。
“妈还在床上躺着,你不要太着急。”
“我说过,妈的病不要紧了。”
“我在外面赚到的钱,还够咱们活两年,要不你再等等。”
“不等了,房子越来越旧,再放就不值钱了。”
“可城里的房子不这样,房价一直在涨。”
“那些事我看不到。这三年,我的视线超不出牛首崖,我都好长时间没下山了。”
“等妈的病好了,我们就去城里看看。”
“再说吧。”
“我决定了,也就是百八十里的路。”
可婆婆的病突然恶化了。他们手忙脚乱了一些日子,临近年关的时候,老人家却撒手人寰。临终的时候,婆婆拉着她的手说:
“那些钱我都留着……咱们家几代都是一脉单传……”
婆婆走了,但她的声音还活着。
“实在不行,就抱一个吧……你答应妈,妈才去得安心……”
“好的,妈妈,我答应你。”
“我们做了错事,怪我……老天爷也惩罚我……”
“妈,没人会怪你。”
“你们好好过吧……我不来扰你们……”
处理完丧事,他的脚又开始疼起来。这次复发,像是久备而来,她精心照顾了一个正月,最剧烈的疼痛才算过去了。
二月二,那个细声细气的男人走进他家的院子。
“我是来买房子的。”
他神采奕奕的样子,像个暴发户似的盘踞在炕上说话。
“我早都相中了,只是以前没听说要卖。你开个价吧。”
“不,你听错了,这房子我要一直留着它。”
她的话让在场的两个男人都吃了一惊。
“是这么回事,因为是老人们留下的念想,我们确实得合计合计。”
“可大街上连告示都贴出来了,落款时间是上个月。”
“那一定是你眼花了,我们正月里连大门都没有出。”
“这可真是活见鬼。”
这个人走后,·她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盯了她半天。
“你真的后悔了吗?”
“我梦到爸爸妈妈了……”她哽咽得说不下去。这天夜里,他钻到她的被窝里来了。
“他们有时会想到回家看看,我不能让陌生的人住进去,他们会迷路的。”
“我早都知道你舍不得。”
“我真的害怕了,以前我不该说出那样的话。”
“你是从今天开始想明白的吗?”
“是的,就是那个人走进门的那一刻。”
“那人十分讨厌,就是真的要卖,也不会卖给他。不过,看起来,他愿意出高价钱。”
“现在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他心里突然想得厉害,可她很快发出轻微的鼾声。后来,他借着月光研究她的手。
“他们说,她是狐狸变的,可我看不出来。”
“以前,她总是说,我的欲望消退得太快了。但她哪里知道,连我自己都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妈是对的。要不我真是什么都没有了。”
他滚烫的身体渐渐降了温。往事一幕一幕地在眼前闪过,可他理不出丝毫头绪。
“再过几个小时,天就大亮了。”
他贪婪地闻了闻她身上的气息,她一点儿知觉都没有。等到他终于睡过去的那一刹那,他荒唐地想:他们这一夜可能永没有止境。
他在睡梦中把疼痛的脚一点点收回来,放到她的小腹上,她轻轻地动了一下。
窗台下的蛐蛐叫起来,一声接着一声地叫着,时间仿佛不复存在了。满世界都是蛐蛐声。
责任编辑:段玉芝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