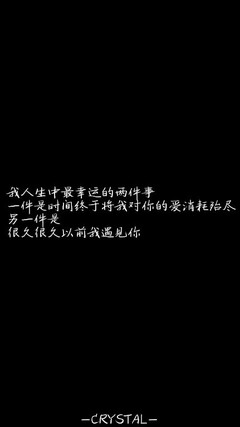爱 的 牵 挂(26) 编辑制作:林夕梦
二十六只蝴蝶 孙道荣
在欢快的婚礼进行曲中,一对新人,互相挽着手臂,向餐厅中央的舞台,缓缓走去。新娘是我的同事,我们有节奏地拍着手,给他们祝福。
这是一场普通的婚礼,按照既定的程序,往下进行。司仪请双方的父母,从席位上站起来,接受新人的叩拜。一对中年夫妇微笑地站了起来,他们是新郎的父母。“请新娘的父母亲也站起来,好吗?”司仪又喊了一声。人们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主桌。没有人站起来。司仪尴尬地和新娘耳语着什么。
新娘的脸腾红。犹豫了一下,她从司仪手里拿过话筒,说,我的家乡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大山里,我的,我的父、父母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没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新娘进我们单位,已经三年多了,从来没有见到过她的家人,也没有听她自己谈起过老家的父母,倒是从其他同事口中,偶尔听到过一点关于她家的事情。她的父亲在她小时候就因病早逝,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母亲,靠在集镇上摆修鞋摊熬日子,苦苦地将她拉扯大。十八岁那年,她考取了大学,这是她们家,也是全村考取的第一名大学生。就在她上大学后不久,却传来了一个让她无比震惊的消息,妈妈要和隔壁修自行车的老王头结婚了。老王头她是认识的,也是一个残疾人,对妈妈和她都很好,这些年给了她们很多照顾。她并不讨厌他,甚至还有一点点喜欢她,可是,让妈妈改嫁给他,这却是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她不明白,妈妈拉扯着她,这么多年都熬下来了,为什么就不能再熬几年,等她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就将妈妈接到城里,一起过好日子?因此,她激烈地反对。一向温顺的母亲,第一次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坚决地和老王头生活到了一起。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她和母亲彻底决裂。她再也没有喊过她一声妈妈。每学期放假的时候,她不是留在学校勤工俭学,就是回到爷爷奶奶家去。
大家都明白,新娘的父母之所以没来参加婚礼,多半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打算让他们来。
这时候,新郎忽然从新娘手中拿过话筒。他注视着新娘,转身对大家说,我的岳父母没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但他们送来了一件珍贵的礼物,以及他们的祝福。
新娘惊诧地看着新郎。新郎笑笑,接着说,前几天,我一个人开车去你家了。请你原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新郎接着说,我的岳父母最近身体都不太好,经受不了长途奔波,所以,他们无法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不过,在我临走前,他们送给了我一件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
有人托着一个竹篓一样的东西,走上舞台。竹篓外面,裹着一层鲜艳的红布。新郎轻轻地打开竹篓上的小门,忽然,从里面飞出一只彩色蝴蝶,在竹篓边盘旋了一圈,扇动着翅膀,向空中飞去。紧接着,又一只蝴蝶,飞了出来。第三只,第四只……
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惊呼声,太美了,太漂亮了!姑娘们尖叫着,几个调皮的小孩子跳起来,试图捉住空中的蝴蝶,蝴蝶振动翅膀,向更高的空中飞去。
新郎面对着新娘,说,这是我的岳父,一只只从村后的山坡上捉来的,每一只都有着不同的颜色。在我去之前,岳父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些蝴蝶,一共26只,每一只代表我妻子的一岁。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回去,所以,他们原准备在我们结婚这天,在家里放飞的。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是我的岳母告诉我的,我的妻子,她的小名就叫蝴蝶。她是群山里,最美丽的一只蝴蝶。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以及玻璃酒杯碰撞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新娘的脸上,挂满泪花。新郎用手绢,帮新娘轻轻擦拭。我还有一个请求,新郎说,我们将蜜月旅行取消掉。新娘不解地看着新郎。新郎继续说,去你家度蜜月,大山里的空气特别好,而且,我想和你一起去看看大山里的蝴蝶。新娘含着眼泪,点点头。
再次爆发热烈的掌声。司仪拿过话筒,请新人叩拜新郎的父母,还有远方新娘的父母……
有人打开酒店的窗户,蝴蝶一只接一只,向窗外飞去。
《南方日报》2011年6月21日
迟到的牵手 清扬婉兮风来了。城市的风,从各条巷道各个角落匆匆奔至,厮绕纠缠,拥挤一如街道上的车和人。

母亲在看。看马路对面那家“大自在佛具店”,那是她想去的地方;看眼前的车水马龙,那是她必须穿越的一个阵。这条马路,北端斜斜伸向一条河,南头最近的十字路口也得走上一刻钟。所以,母亲别无选择。
母亲来自伏牛山,那里满眼是绿树青山和各色庄稼,没有这么多的车和人。母亲说,车真多,这人咋都在街上哩?山村的路多是土路,坑坑洼洼,歪歪扭扭,近些年修得像模像样了,但也没有这么漂亮。母亲说,路真宽,真平,能照出车影儿了吧?
但这美丽的路,母亲显然不敢过。她站了许久,左右张望,没有一辆车肯为她停一停脚步。我就在母亲身边,我想牵上她的手,亲亲热热走过马路去,像别的母女那样。可是,母亲不看我,只看着马路,脸上有淡漠,还有倔强,如我幼时看惯的样子。而我,也一如幼时,只能看着她的手而已。牵手,于我们母女,生疏至旁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在故乡那个小盆地里,多的是大山小山沟沟坎坎,多的是黄土地乱石滩,独独缺乏温情。那里的孩子与田野上的花花草草,与满地跑的小猫小狗没有两样,都是望天收的自然生命。大人们忙大人的事,孩子们玩自己的,即使有时被指使干点儿大人的活,也没有手把手教这回事。也有被母亲拉了手扯回家的,但大抵是挨打的前奏,与牵手的柔情毫不相干。
在那些母亲中,我的母亲又是个性最刚的一个。她幼年失父,战乱年代携一弟一妹颠沛流离,稍稍大些就开始帮我的外婆撑起家门。在长辈之命、媒妁之言下,她嫁的是连看也不愿多看一眼的人,只能忍受着外人的嘲谑勉强度日。国家提倡婚姻自主后,她顶着依然保守的乡民们的诋毁,冒着族中长辈们的谩骂,毅然决然与我的父亲重组家庭。父亲长年在外,她独自应付生产队的活儿,抚养我们姐弟五个,还得照应外婆一家人。白天干强壮男劳力的工作,晚上在油灯下纺棉、织布、缝衣服、做鞋子……再苦再难也要让家人体体面面地立于人前。长期的生活磨砺,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母亲有了刚强的性格,也有了自己的一套处世方式。她克己,律己,做事力求完满,绝对不给人挑出错来。对自家孩子要求尤其严格,甚至于苛刻的地步,只要与人发生争端,千错万错都是自家孩子的错,不问缘由先打骂一番。所以,我们都很怕她。
我是老小,据说挨打最少。尽管如此,即便是跟了母亲去谁家吃酒席,我也是小心地跟在她后面,亦步亦趋,诚惶诚恐,生怕一不小心出了差错。对于母亲的手,我只能远远观望,暗暗揣想;牵手,那是梦里也不敢企及的,不招来一顿责打就已经很是满足了。
那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切似乎理该如此。今天我却有些伤感了。母亲已经七十,我也不再是那个跟在母亲身后的小女孩了,岁月把一切掩埋在一个叫做七里坪的地方。
也许有些事已经改变了,在我所看不见的地方?譬如,父亲去世后,母亲偶尔流露的脆弱?譬如,这两年母亲渐渐显出的温情?老一辈的感情表达是典型中国式的,花落不闻,水流不动,深潭一般波澜不惊。
母亲的手就在眼前,青筋暴露,皴皱瘦削,老人斑星星点点或隐或现地昭示着苍老。这样的手,今生我还能再牵几次啊?还迟疑什么呢?我伸手过去,两寸,一寸……将要触到时,我的女儿喊了她外婆一声,母亲回过头来看向人行道。我的手偏离了方向,便就势搀住母亲的胳膊,心里同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咋了?咋了?母亲一边问我的女儿,一边使劲甩开我的手,用惯有的语气说:咳呀,干啥哩?冇事儿,我冇事儿!
母亲还是那个刚强的母亲,我怅然若失。
想起朋友介绍我看的一篇文章来,题目好像就叫“牵手”,大概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写的吧!也是过马路,也是牵手,原本是自幼与母亲牵手走惯了的,这一天却突然不肯再那样,因为孩子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母亲的失落溢于言表,孩子尽收眼底,回顾十几年在爱中成长的点点滴滴,经过一番中国孩子常用的思想斗争后,孩子重与母亲牵手过马路,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
溪流永远急着奔向大海,浪潮却总想重回陆地。那个不知珍惜的孩子呵,那个柔情无限的母亲呵,那个可爱得令人神往的故事呵……想着这些,我笑了,笑自己已过而立却突然作小儿女状,矫情了些呵。
再注意母亲时,我看见她终于要过了。她小心地探出一只脚,像春汛时过村前那条翻水桥先试深浅一样,保持重心靠后,以便随时撤回。过了许久,没有发现什么危险,母亲便试着伸出另一只脚……一辆雪铁龙正好疾驶而过,那刺耳的尖叫声明显带着警告,把母亲吓得连连后退。我被母亲的神态吓得紧赶过去,忙乱中不觉伸出了双手,母亲一把抓住,立定身体,大大地喘了几口气。女儿在一边笑起来,大约是笑外婆会被汽车吓着。母亲也笑了,脸上讪讪的,还强自镇静着,但并没有松开我的手。
现在,母亲的手就在我手中了,并没有文学作品里描述过无数次的那种柔滑——母亲老了——那手只是一味的干燥粗糙,刺剌剌的,但是很温暖,是血肉相连的那种暖,一直暖到心底最深处。
现在,我要过马路了,牵着我的母亲的手走我们的路了。真希望这马路再宽些再远些,让我牵着母亲长长久久地走下去,走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走出她艰辛粗砺的人生,走出段细腻温情的晚年。
现在,我的右手牵着年迈的母亲,她的身体半倚着我,脚下亦步亦趋,正如一个需要扶持的孩子一般。我的左手牵着年幼的女儿,那是母亲和我血脉流向的又一个,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牵手的幸福却已满满的了。
现在,现在……我说不下去了!秋日暖阳里,我突然想流泪:可是……母亲呵,我情愿你不牵我的手,情愿依旧随在你身后,只要你依旧是那个倔强有力从容前行决不后顾的年轻的母亲!
来自天堂的回信
【美】鲍勃?格林
伯尼?迈耶斯身患癌症,他10岁的孙女萨拉?迈耶斯对于他的死感到十分突然,说她还没来得及向爷爷说几句告别的话呢。有好几个礼拜,萨拉对此都很少流露自己的感情,可是有一天,她参加完朋友的生日聚会,手里拿着一只鲜红的氢气球回来了。
母亲回忆道:“她默默地回到自己屋里,出来时又拿着那个气球,还有一只信封,上面写着‘天堂 伯尼爷爷收’。”
信封里装着萨拉写给祖父的信,她说她爱他,希望他能够听到她所说的话。她又在信封上面写上回信地址——伊利诺斯州威尔梅蒂,然后就把它系在气球上放了。
母亲还记得:“那气球看上去那么容易破,我以为它连三棵树都飞不过去,可它竟飞走了。”
两个月过去了。一天,邮差送来了一封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约克的信:
“亲爱的萨拉及你的家人和朋友:
“ 你给伯尼?迈耶斯爷爷的信看来已经到过目的地,他读到了。我知道,天堂那儿不能收有形的东西,所以它又飘回到地上了。他们只把思想、记忆、爱心等留下了。萨拉,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起了爷爷,他都会知道,并满怀慈爱地来到你的身边。
“诚挚地
“唐?考普(也是一个爷爷)”
考普是一位63岁的退休职员。他在离威尔梅蒂将近600英里的宾州东北部的一次狩猎中发现了这封信和几乎瘪掉的气球。气球落到了一片乌饭树上,在此之前,它至少飘过了三个州和北美五大湖中的一个湖。
“尽管考虑怎么说花了我好几天时间,”考普说,“可给萨拉回信对我来说却十分重要。”
萨拉说:“我就想收到爷爷的回信,现在看来,我已经收到了。”
母亲的潜能 孙道荣 同事小陈刚刚做妈妈不久,脸上洋溢着遏止不住的幸福神情。每隔几天,她就会往自己的空间里,上传几张宝宝的照片。宝宝长得虎头虎脑,煞是可爱。每张照片,还都起了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如有张照片,标题是《宝宝的白日梦》,宝宝趴在枕头上,睡着了,印花枕头上的碎花,像是满天的星星。还有一张,取名《手指的滋味》,宝宝斜躺在沙发上,一只手含在嘴里,正有滋有味地吮吸着呢,大大的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很陶醉的样子。照片构图巧妙,灯光恰到好处,最关键的是,捕捉到了宝宝最可爱的瞬间,一看就是专业水准。然而,让我们绝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照片竟然是出自小陈之手。这怎么可能?从来没听说过她会拍照片啊。记得以前单位集体旅游,她是从来不带相机的,她说自己对机械的东西很笨拙。
小陈脸红红地说,真的都是自己拍的。宝宝出生后,为了记录下宝宝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从来没有拍过照片的小陈,开始学起了照相,为了拍好照片,她还特地让丈夫买回了专业的单反相机。与我们平时用的傻瓜相机比,这可是真的机械的家伙。对照着书本,几天下来,小陈就基本摸清了照相机的门路。很快,什么用光啊,对焦啊,构图啊,这些摄影的基本问题,也都一个个迎刃而解。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也是越来越好。开始的时候,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些照片出自自己之手。几个月拍下来,小陈已经很有些摄影师的范了。
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是难以相信,你怎么就能捕捉得那么精准的瞬间,那么生动传神的表情呢?小陈笑着反问我们,还有谁比她更了解自己的宝宝?每位妈妈的眼睛,其实就是最好的快门,如果妈妈们都拿起照相机的话,每个妈妈都一定是孩子最好的摄影师。
妈妈的眼睛,就是最好的快门。她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是的,还有谁比妈妈更了解自己的孩子?而在伴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妈妈的潜能,也是慢慢挖掘、升华起来的。
上个月,接到一位老乡的电话,说他的妻子要到杭州来,陪孩子参加艺考,他的女儿报考了一家高校的艺术专业,专业课要提前考。老乡的妻子我们也是认识的,典型的一个家庭妇女。接到老乡的妻女后,将她们安顿好。第二天,孩子去考试了,我和妻子陪她在考场外等待,闲聊起来。她告诉我们,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喜欢写写画画,他们就有意培养她学习绘画,开始是在少年宫学,每周两节课,都是她陪同接送的。后来,孩子的绘画有了提高,他们又花大价钱,给孩子请了家教,直接到老师的画室上课。她说,这些年,她都是陪着孩子在画室度过的,为了给孩子开阔眼界,她还到处陪孩子看美展,参加各种各样的美术比赛。讲到孩子和绘画,老乡的妻子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她朝考场里幽幽地望了一眼,叹口气说,孩子特别喜欢克里姆特和莫奈的画。她的绘画基础不错,就是色调处理得不大好,特别是明暗对比,比较欠缺,老是会出现处理不当的色块。还有个就是笔法也常常处理不好,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刮”法和“砌”法,因为不到位,缺乏立体感和纵深感,三度空间不明晰……说实话,听她讲这些的时候,我简直如坠云雾。以前在老家时,我们常到她家蹭饭,她烧得一手好菜,话题也是围着厨房转,没想到,几年不见,在伴随孩子学习的过程中,她自己也几乎成了半个行内人,那些生僻、孤傲的专业名词,如白菜萝卜一样,顺手拈来。
这几年,常有外地的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领着孩子来杭州参加艺考,有的报考的是主持人,有的报考的是音乐专业,有的报考的是书画方向……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曾经对主持、音乐、书画统统一窍不通的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如今,张嘴都是专业术语,都各自的圈子,耳熟能详。有个学音乐的孩子的妈妈,以前看简谱都像看天书一样,现在不但熟谙五线谱,还会弹钢琴,拉二胡,奏古筝,她自嘲地说,自己的这些潜能,都是在孩子的激发下,伴随孩子的成长,迸裂出来的。
她说的没错,母亲身上的潜能,很多是为了子女的成长,而萌芽爆发的。那也是爱的潜能,爱的释放。
《山东商报》2011年7月17日
林夕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