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中华》(一)
<?xml:namespace prefix = o />
【猜测黄帝】
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司马迁的《史记》是从黄帝开始的,皇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黄帝,是华夏民族实现第一次文明腾跃的首领。黄帝有一个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历来有不少人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
炎帝的主要业绩比较明确,那就是农业。黄帝要比炎帝进步一点,所谓“轩辕之时,神农世衰”。
炎黄之战,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入场口,具有宏大的哲学意义,“血流漂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大多各有庄严的持守。
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部落,逐渐被跨地域的部落联盟所取代,出现了“华夏大族”的概念。华,荣也,夏的本意是大。华夏也就是指繁荣的中原大族。
黄帝之后,便是著名的尧舜禹时代。大禹的儿子建立了第一个君位世袭的王朝——夏,夏朝的建立是华夏文明的一个新开端,从此“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传说时代结束了。
【古道西风】
老子否认自己有伟大的学说,他觉得最伟大的学说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说清楚了又不自然了。“大”,在老子看来就是“道”。
老子的道止于流沙黄尘,孔子的道,止于宫邑红尘。
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路上的孔子,一只承担着一个矛盾:一方面,觉得凡是君子都应该让世间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觉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间充分接受。用现在的话说:一头是广泛的社会责任,一头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对立,水火不容,却在互补中仍然互斥,虽互斥又仍然互补,难分彼此,永远旋动。
这便是大器之门,这便是大匠之门。
【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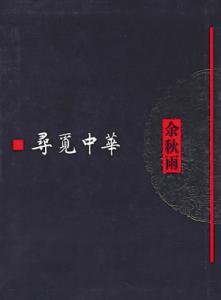
稷下学宫原址,是曾经与无限智慧有光的角落。即便只是一站,也会立即困惑,人类在几千年间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稷下学宫创办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齐国朝廷一开始是把它当作“智库”来办的,是当时的一所最高学府,诸子百家中几乎所有当时的代表人物都来过,丰富、多元、互融。
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成为名垂百世的文化大手笔。
保持思维对于官场的独立性,是稷下学宫的生命。不参政,却问政。
柏拉图创建雅典学园的时间,比稷下学宫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应该算是同时。孔子可能只比释迦牟尼小十几岁,孔子去世后十年左右,苏格拉底出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一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二岁,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五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七岁。。。
人类历史大么长,怎么会让这么多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涌现于一时?为什么后来几千年的文化创造,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后尘?
天意从来高难问。几个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时出现在世界上,从此,人来也就从根本上告别荒昧,开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贵。
【诗人是什么】
我们远祖的精神起点很高。在低级的生产力还没来得及一一推进的时候,就已经“以诗为经”了。
《诗经》里有一种来自乡野大地的人间情味。这是一种悠久的合唱,群体的美声,是一种广泛的协调,辽阔的共鸣。它所标志的,是一个缺少个体诗人的诗歌时代。
《诗经》首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那么,屈原则首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体形象出现的伟大诗人。《诗经》把诗写在万家炊烟,屈原把诗写在自己的身心上。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内心基调改变了,有了更多的个人话语。这种自我,非常强大又非常脆弱。一个多愁善感的孤独生命发出的声音似乎无力改易国计民生,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低头思考自己的生命,他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被嫉受诬,将成为一个横贯两千多年的主题,所有的高贵和美好,也都将从这个主题中产生。于是也就掀开了中国的贬官文化史。
屈原的高贵由内至外无所不在,但他的起点却是承担了使命之后的痛苦。由痛苦酿造高贵似乎不可思议,屈原提供了最早的范本。
这位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屈原,两千多年来依然寂寞。他所开创的自我形态、分裂形态、挣扎形态、高贵形态和询问形态,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半失落。
【历史的母本】
在中国文化史上,让我佩服的人很多,让我感动的人很少。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让我感动的人物。
司马迁让所有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史记》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态一鸣惊人,成为今后两千多年历代编史者自觉效仿的通例。是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前后一贯的历史兴趣、历史使命和历史规范,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始终有史可寻、以史立身的文明群体。
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副有关正义的目光,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家谱”。
司马迁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写历史,开启了一部“以人为本”的中国史。在他看来,所有的时间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恶、气度、性格,永远可以被一代代后人体验。他描写的那些著名人物,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种精神模式和行为模式,衍生久远,最重组成中国人集体人格的重要部件。
这种轻事重人的选择,使司马迁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选择使早已应该冷却的中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人的体温和呼吸。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
《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更是中国文学的母本。
【丛林边的那一家】
文化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间,是“恶之花”。再也没有比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丛林地带,更能体现这种文化魅力的了。
三国对垒,曹操张罗的是一种权术组合,刘备张罗的是一种性情组合,孙权张罗的是一种意气组合。
曹操的那几首诗,已经足可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曹操在文学上高于诸葛亮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生命格局。诸葛亮在文学上表现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学上表达的是天地生命。
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会在琐碎装饰上沉陷。真正自信的人,总能够简单得铿锵有力。
曹操父子三人拢在一起,占去了当时华夏一大半文化。真可谓“天下三分月色,两份尽在曹家”。我想不起,在历史的高爽地带,哪一个名门望族在文化聚集的浓密和高度上赶得上曹家。
父子三人,权位悬殊、生态各异、性格不一,却不约而同地感悟到了人世险峻、人生无常。这些感悟,最集中的体现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归宿——墓葬上,我敢肯定,曹氏父子确实是薄葬了。
【千古绝响】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当英雄们逝去之后,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
魏晋,就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无论在世纪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
文化名人成批被杀,一种特殊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魏晋时期的一大好处,是生态和心态的多元。
阮籍似乎执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闹出一番新气象。干脆扯断了一根根陈旧的世俗经纬直取人生本义。人们都说他怪异,但在他眼里,明明生就了一个大活人却像虱子一样活着,才叫真正的怪异,做了虱子还洋洋自得的冷眼瞧人,那是怪异中的怪异。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可爱人物。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他完全不理会种种教条礼法,彻底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的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
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密土。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重山间的田园】
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因此,深刻意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正是这种不一样,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素质。
一般来说,在我们中国,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文化人格。最感到陌生的,是游戏反叛型文化人格。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文化人格,中国民众处在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的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
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正是高远的情怀,有可能主动对自己做边缘化处理。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大化其间,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一旦确认,我们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田园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桃花源记》表现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冷然。陶渊明告诉一切过于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理想的蓝图是不可以随脚出入的。在信仰的层面,它永远在;在实用的层面,它不可逆。历来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对此岸理想和彼岸理想都不认真,陶渊明对他们而言,只是失意之后的一种临时精神填补。
静静的他,使乱世获得了文化定力。
 爱华网
爱华网


